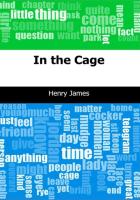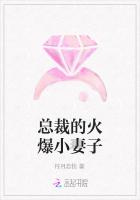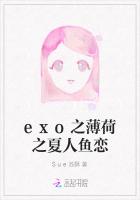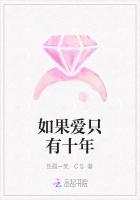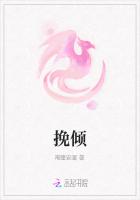他若不是当今圣上的本生父,尚且要夹着尾巴做人,何况盛名在顶,能不戒惧?
西太后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牢牢捏住了老七的软骨。所以世铎不过是个过渡,真正的首席军机大臣恰恰是这个第二天补宣的“商办人员”。这就是政治的微妙。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西太后也是一位一贯的对外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呢。
所以李鸿章才说他们是“乳臭陋儒”,并敏感的预感到了醇老七的悲剧结局。
但大清国里,终究不是人人都能看透这一切。
对慈禧而言,这是蓄谋已久。但对于朝野而论,实在是一声霹雳。其中最震惊的莫过于盛昱,而又惊又愧的,又莫过于张佩纶。
说起来张佩纶虽然是清流派的健将,却是一个比较支持洋务的清流,而且他的父亲与李鸿章是故交。想当年李鸿章受任于临危之际,远赴上海孤岛。此后苏南浙北,三千里转战,真是万苦千难。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时任安徽按察使,对李鸿章帮助颇多,两人可谓生死之交。这些往事,李鸿章永远不会忘记。
在张佩纶看来,北宁的失败源于徐延旭的无能,徐延旭的被误用又源于自己的误信人言与轻率举荐。说起来,自己才是罪魁祸首。结果呢?自恭亲王以下,枢辅重臣纷纷落马,自己却置身风暴之外。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所以他才写信给李鸿章,自承:“误荐晓山,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
但在太后眼中,问题就完全不同了。若是北宁失败的责任问题真说清楚了,她又如何借机实现多年的夙愿?就算张佩纶想负这个责,也不能让他来付。
可是太后有意放张佩纶一马,言路却不愿放他。弹劾奏章越积越高。而言路之所以敢如此猖狂,原因无他,因为张佩纶往日弹劾人太多,冤家遍地,现在终于轮到这些人四处使银子买通言官狠批张佩纶了,也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关键的,太后一手提拔的主政大臣醇亲王,素来讨厌清流人物,早就说过: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大言无实,我在位一日,决计不用此三人。
京师,张佩纶是不好再待了。那就出去转一圈吧。
毕竟,从慈禧的角度讲,她最需打压的绝非清流,而是醇亲王。她好不容易赶走了恭亲王,又岂容新对手出现?更何况这个“对手”还是当今圣上的本生父!所以太后有必要保留清流,因为既可以制衡李鸿章,还可以制衡醇亲王。这也是权力制衡术,只可惜是权谋制衡术,最终服务的不是国家、人民,而是坐在最上位的那一个孤家寡人(眼下是孤家寡妇)。
于是便有了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1884年5月8日)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其中,张佩纶被授三品衔。
对朝野而言,这无疑又是一声霹雳。
在局外人看来,文人典兵,多无善终。只怕这一次也不会例外。不知道这仨人哪里得罪了太后,竟逼出这出“借刀杀人”的戏来。又或者,也许是太后已厌倦了言官们的大言不惭,要杀鸡儆猴,给言官些颜色看看,这也不好说啊。总之天威难测,但还要测,不测哪来饭后茶余的谈资?
可在局内人的心中,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正如张佩纶给李鸿章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恭(亲王)、李(鸿藻)黜,徐(延旭)、唐(炯)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棉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丹老来述慈圣(慈禧太后——笔者注)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恩。”
后人读史于此,可不免纳闷了。被杀的人反而感激借法国刀杀他的人,这叫什么世道?
事实证明,这绝非张佩纶的幼稚,更非一厢情愿。
从表面上看,让张佩纶一介书生又督办福建海防,确实不无“借刀杀人”之嫌。可若是“刀”都没了,又如何去“借”?
注意,让张佩纶去福建的上谕发于光绪十年的四月十四日(1884年的5月8日)。这道“上谕”若是早发两个月,或晚发两个月,“借刀杀人”之说都能成立,偏偏这时不能成立。为什么?
就因为和谈已经开启,李鸿章和福禄诺的谈判已基本达成共识。到阳历6月中旬三大清流(张佩纶、吴大澂和张之洞)联抉出京之时,和约业已达成。
就等三个月后双方互派全权大臣商订细节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十年的十月初十,就是太后的五十大寿之日。激进派想打,太后可还想安安稳稳的过个生日呢。
所以五月初一的上谕中才说:“前因福建海疆紧要,谕令张佩纶前往会办,以资整顿。所有该省濒海各处,张佩纶抵闽后,自当周历巡查,会商该将军督抚妥筹布置,期于周密。”
整顿,巡查,布置。这就是他的任务。
影响所及,三大清流的旅程也是不慌不忙的。
离京之际,群贤聚于陶然亭送行,清流健将宝廷还满怀浓情地赋诗一首:
友朋久聚处,淡泊如常情。偶然当离别,百感从此生。
人生各有事,安得同止行?各了百年身,甘苦难均平。
古今几豪贤,畴弗有友朋。离别亦习见,别泪例一零。
今日天气佳,有酒且共倾,勿作祖帐观,联辔游江亭。
俯视大地阔,仰视高天青,余生尚几何,愿醉不愿醒。
清流式的浪漫情怀,跃然纸上。
出京之后,他们先到天津拜会了李鸿章。后者给他们安排了精彩的水师演练,并把他们一路拉到旅顺,视察工事,会见老友,共论国是。真是快何如哉。
反正横竖没仗打,张佩纶懂不懂军事就无所谓了。关键是借这个机会,让他出京避避风头。只要不出错,就有功劳。中法彻底和好如初之时,就是张幼樵再回京师之日。那个时候,不仅旧错可以不提,而且要论他的新功。想当年,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天下读书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现在张之洞都是以山西巡抚署理两广总督的钦差大臣了,张幼樵也不能过于落后。李鸿章越来越老,大清国的日子却还长久。接班人总还是要培养的。所以当李鸿章听说这个任命时,才说了这样一句话:“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
在这个磨练使命下,张佩纶岂能不感激涕零?
但若仅仅是感激涕零,那他就不是张佩纶了。
张佩纶的特点是勇于任事而耻于逃避责任。这一点很像李鸿章,所以才赢得后者的激赏。作为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张佩纶不会轻易放过这次任命,但作为一次逃避责任的升迁,他也绝不会完全去领太后的好意。正如他在写给李鸿藻的信中所计划的那样:“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总之,横竖都要装病,绝对不去搞无功受禄的事情。
从事后的发展看,事情若果能如此收场,反而幸运了。可惜历史恰恰不愿作此收场。
变起观音桥
问题出在撤军问题上。
如前所述,山西、北宁虽然失守,但谅山等北越重镇仍在清军手中。根据李福协议,这些清军都将撤回中国境内。福禄诺在5月17日(四月二十三)正式向李鸿章划出了两道进军线:法军将于6月5日进据高平、谅山,7月1日进据保胜。反之,限东线清军于20天内,既西历6月6日前全部撤回境内;西线清军于40天内,即西历6月26日前全部撤回。以免发生摩擦。
这可让老李为难了。
自醇王上台之后,主战之声再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李鸿章更是成为众矢之的。而西太后在撤军问题上恰恰也是倾向于缓撤。李鸿章只好另动脑筋,希望边军指挥官能够先斩后奏,造成撤军事实,和约落地,自然皆大欢喜。
李鸿章之所以敢采取这个行动,原因在于当时驻扎谅山的新任署理广西巡抚潘鼎新是他的老部下。
可惜潘鼎新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先请示中央,万一法军来犯,边军如何处置?这下麻烦了。此时京师中的主战派已占了上风,他们一致认为《天津条约》丧权辱国,无论最终细则如何制定,中国都不可能先撤军,以免法国人得寸进尺。在这种环境下,太后只能指示:“准稍退示弱!”果法军来犯,还要“之决战,力遏凶锋”。
这一来,就等于是下了命令。潘鼎新再想制造既成事实,就要冒抗命的罪名。到时候只怕太后也只有丢卒保车了。于是,潘鼎新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与此同时,法国军方也早已按捺不住。
米乐令陆军中校杜森尼于6月中旬率先遣队北上接收谅山防区。这支先遣队共八百余人,包括一个海军步兵营(310人),一个山炮连(90人,6门40毫米山炮),两个东京土着步兵连(约300人),及少量骑兵、工兵和医疗人员。
临行前,米乐一再叮嘱,这是一次和平进驻,而非军事行动。如果遇上土匪与强盗,杜森尼可以自行解决。但若遇上清军,如果对方拒绝将防区移交,一定要先请示自己,再依令行事,万不可造次。
应当说,米乐的态度是比较持重的。但正如街亭之役武侯的误用马谡,这次米乐同样犯了大错。一如一名法国作家所言,杜森尼中校“毫无外交手腕,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被破坏的危险。”最明显的一点,杜森尼北上接收谅山,居然连个像样的汉语翻译都没带,他所依赖的那位越南翻译,居然只能听懂粤语,汉语书面阅读能力也极差,稍复杂的公文就挠头。而杜森尼所面对的,却是正急于雪愤的“黄桂兰旧部”——而且同样没有一个像样的法语翻译。
易怒而马虎的杜森尼,注定要引发新的灾难。
6月22日(五月二十九日),九百名法军在杜森尼的率领下,行抵北黎(今北丽),接近了清军的阵地。第二天,杜森尼照会清军,要求后者于三日内退出谅山,不然后果自负。
在已经接到明确的谕旨的情况下,潘鼎新当然不敢把谅山让给杜森尼。按理说,此时杜森尼应该立即请示米乐,可是,冲动的杜森尼却选择了靠实力解决问题。
这真是一个不长脑子的决定,法军固然在武器装备与组织训练上具有优势,但这个优势可不是个无限扩大器。当杜森尼在6月25日于观音桥地面悍然对一万余名清军开火后,结果可想而知,清军群起还击,杜森尼一伙狼狈逃窜。
此战清军以伤亡三百余人的代价,毙伤法军数十人,并将后者逐退三十余里。清军不仅守住了阵地,并在追击中缴获了一些法军物品。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冲突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不幸。但真正造成不幸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事后双方一线官员的汇报。
为了推卸责任,杜森尼在汇报中把这起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一方不说,他甚至把一直驻扎在谅山的清军说成是从别处调来,专门伏击接收分队的。他还把双方的冲突描述成中方精心策划的伏击战。结果,在巴黎的茹费理看来,中方此次伏击不仅是预谋性的,而且手段非常卑劣。
反之,潘鼎新则在汇报中把法军的规模由不足千人夸张到一万余人,法军的伤亡数字也被翻了好几倍。这样一来,在北京中枢看来,这无疑不是接收,而是借和约履行的幌子,妄图袭击全歼驻谅山的清军。这是蓄意挑衅!而对激进派而言,既然万余法军的进攻都被打退了,大清国还怕法兰西吗?一时间“谅山大捷”传遍京师,北京城内的主战声浪也再度高涨。
一方过于急躁的愤怒,一方文不对题的亢奋。战火的重起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法国海军中的激进派主张立即将战火烧向东南沿海,至少要拿下福州与南京,再直捣渤海,攻旅顺,克威海,直逼京师,订城下之盟。孤拔在6月底甚至主张在预定的时刻同时进攻旅顺、威海、南京、吴淞、福州和厦门。并已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但返回巴黎汇报工作的福禄诺反对这些狂热的计划。他认为这次和平来之不易,法国应该珍惜。李鸿章深明大势,是法国长久的朋友,我们最好不要去他的防区挑衅。双方意见差距太大,茹费理折中了一下,于7月9日(闰五月十七)通知中国临时驻法公使李凤苞:若中方不能迅速从北越撤军,并为“北黎伏击”
赔款,法国“将有必要直接地获取担保与应得的赔偿”。
曾巴会谈有始无终
这就形成了法国的新战略:踞地为质。
既是“踞地为质”,就像黑社会绑票一样,总要绑个富家公子、豪门千金。
若绑个贫家子弟,法律风险一样,收入可就大不相同了。除非此君家里有什么自己都不知道的祖传宝贝。其次,绑国家领导人更有赚头,但有那本事吗?风险过高,收益下降,游戏结束。法军现在不绑“人质”绑“地质”,同样要遵循这两大原则,要寻求风险与投入,成本与回收之间的平衡。
闰五月初八(6月30日),利士比派其副官日格密赴津面见李鸿章,恫吓说,若中国不赔款,孤拔将军就要进北京城,与中国执政面议。李故意装傻,问:孤拔何时晋京?日格密只好进一步挑明:“所谓的面议者,系以兵戎相见。”李鸿章笑着说:“孤拔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
李鸿章这样说当然是有自信的。
自“李德谈判”以来,李鸿章一直在忙着加强京津守备。他“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