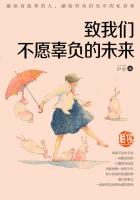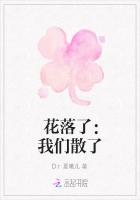可是,他的苦苦哀求丝毫也不能让遭受遗弃的妻子回心转意。“你有什么脸来见我,”她愤恨地说,“我是被你遗弃的人,去吧,还是去找年轻美貌的海伦吧,求她救治你。你的眼泪和哭诉决不能换取我的同情!”说着,她将帕里斯送出门外,她没有想到她的命运跟她丈夫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帕里斯由仆人们搀扶着走开,他们将他抬下山。在半路上,他因箭毒发作而咽下最后一口气。
俄诺涅独自待在家里,心里感到深深的后悔。她想起年轻时的帕里斯和他们往日的情意。她感到心痛欲裂,止不住泪流满面。她从床上跃起,奔了出去,经过一座座山岩,穿过山谷和溪流,整整地奔跑了一夜。月亮女神塞勒涅在暗蓝的天上同情地看着她,用月光照着她的路。最后她来到了她的丈夫的火葬堆那里。牧人们对他们的朋友和王子表示了最后的敬意。俄诺涅看到丈夫的遗体,悲痛得说不出话来,她用衣袖蒙着美丽的脸,飞快地跳进熊熊燃烧的柴堆里。站在一旁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拉她,她已经被火焰吞噬,和她的丈夫一起烧为灰烬。
2006年4月1日
Apollo in curse
阿芙洛狄忒这位基本上跟所有男神都有一腿的风流美人,唯独跟花花公子阿波罗井水不犯河水。渊菽大约还得从《变形记》所记载的上古开始,阿波罗撞破阿芙洛狄忒与阿瑞斯的私情,因着不愿阿瑞斯独享专美的嫉妒,向赫淮斯托司告密。戴绿帽子的丈夫便精心织就看不见的大网,捉知了似的把这对儿情人展览给众神取乐。阿芙洛狄忒因此恼羞成怒,诅咒阿波罗的子女,世代得不到真爱。慢说是阿波罗的子女,就是无所不能的太阳神本身,其爱情也没有一回是甜蜜的。达芙尼变成月桂,究其底细也就是胖屁股的小厄洛斯拿阿波罗开心,让阿波罗几乎要溺死在自己的爱情里。厄洛斯替母亲报仇,基本上等同了春药的功能。再有无数的王女、公主、河仙、宁芙们,不过就是春风一度,或是天河牛女,被阿波罗始乱终弃。唯一一次,太阳神认真了,爱的小心翼翼,不厌其烦地玩起小儿女的把戏,甘愿陪伴左右,亲自执辔牵弓。能令神低下高贵头颅的只有斯巴达王子雅辛托斯。可是西风仄斐厄司嫉妒雅辛托斯成为太阳神的禁脔,设计让太阳神亲手误害少年。
“Ay,” the sigh of pain that rose from Apollo’s breast.
唉!——阿波罗发出痛苦的悲鸣。可怜阿波罗,白享生命之神的名头,却只能抱着心爱之人悲痛,眼睁睁地看着鲜活的色彩从少年身上剥离。他把他萎蔫的娇躯点化成风信子,让人们从任何一片花瓣上都能看到他的叹息。
神的子女继承了父亲受到的诅咒。科尔喀斯公主美狄娅被妒妇赫拉弄到神志不清,为了伊阿宋,抛父去国,杀弟投敌,结果伊阿宋逆起二心,迎娶新妇。更早些的,米诺斯的王后疯疯癫癫爱上公牛,诞下牛头怪米诺陶在迷宫里吃童男女,雅典英雄忒修斯冒冒失失去杀牛,要不是米诺斯公主阿里阿德涅给了他线团,英雄只怕也早做牛腹美餐。然而忒修斯空口许约,得了便宜卖乖,抛弃眼泪淌干的公主,驾黑帆回雅典,也合该他老父跌进海里。阿里阿德涅的妹妹费德拉,非但没有吸取教训,还是义无反顾下嫁忒修斯给他当续弦。阿芙洛狄忒更加捉弄她,让她爱上丈夫与前妻的儿子希波吕托斯,苦不堪言。到得襄助特洛伊,神祇分帮别派,阿波罗、阿耳忒弥斯、勒托、阿芙洛狄忒、阿瑞斯力挺特洛伊城,也并不是缔结同盟,本是各有心思。阿波罗怀念工作旧地,而且宠爱帕里斯,即便卡珊德拉胆敢拒绝他,也是还有念情,因此阿耳忒弥斯和勒托,妹妹母亲齐齐上阵,为可怜的哥哥出一臂之力。阿芙洛狄忒盖因老情人兼儿子都在特城,况且帕里斯把苹果大方判给她,自然要袒护特洛伊。阿瑞斯初时只怕跟着阿芙洛狄忒裙子转,到后来见自己嫡传阿玛宗女皇牺牲,才真真愤怒起来,跑去城下杀红眼。
阿波罗名下的嫡子只有三人,诗歌与音乐之神俄耳甫斯、医神阿斯克勒毗俄斯、流落民间的利诺斯。传说中的法厄同和伊翁,大概都是后来的补充。比如法厄同常说是早期日神赫利俄斯的儿子,在射手跟日神合而为一的时候,这个倒霉的孩子就顺理成章过继给阿波罗了。那时候阿波罗喜爱用自己的号——光明的福玻斯。
美狄娅的祖先也被说成是早期的日神。崇拜太阳在希腊北部居多,也有说阿波罗是从亚洲跑去欧洲的,理由就是《伊利亚特》里他偏袒特洛伊。
2006年5月12日
施季里茨退休了
读《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恰读到此——
二十三年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他最后一次见到萨申卡;当时他(施季里茨)正动身先去上海;然后再前往巴黎执行捷尔仁斯基交给的一项与白俄侨民有关的任务。那是刮着大风,很可怕、很遥远的一天。就从那天起,萨申卡的音容笑貌就深深铭刻在他的心上,她成了他“自我”的一部分,和他融成了一体……
施季里茨又想起了在一个深秋季节他和儿子在克拉科夫偶然相遇的情景。他记起了有一次儿子是怎样化名“戈里尚奇科夫”到旅馆来找他,他们又是怎样开着收音机低声细语;以及他与儿子(由于命运的安排儿子选择了父亲的道路)分手时的痛楚心情。施季里茨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布拉格,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这座城市,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维赫利少校保护了克拉科夫一样。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柏林到布拉格乘车只需六个小时,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施季里茨伤愈后,驱车到卡尔斯霍尔斯传城郊罗什克的遗孀家里去了一趟。房间里没有生火,罗什克的妻子正躺在床上说胡话。罗什克的儿子亨利才一岁半,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气无力地哭着:孩子的喉咙哭哑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施季里茨急忙请来医生。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哮吼性肺炎。施季里茨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善良的老太婆,给孩子洗了个澡,饱饱地喂了一顿热牛奶,正准备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
“请在我的卧室给他铺好被褥,”施季里茨对她说,“让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里孩子吵得可厉害啦。”
“或许这正是我的喜好,”施季里茨轻声回答说,“也许我很想听听娃娃在夜里是怎么哭的。”
老太婆笑了,说:“孩子哭有什么好听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没敢和主人争辩。夜里两点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卧室里的那个男孩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啼哭。老太婆穿上暖和的长袍,匆忙梳了梳头就走下楼来。她看见卧室里还点着灯。施季里茨把裹着羊毛毯的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低声地给孩子哼着歌曲。老太婆从来没见过施季里茨现在这样的面容,这面容变得真是让人难以辨认,起初老太婆甚至还怀疑:“这是他吗?”平时施季里茨的面部表情十分严厉而又显得年轻,现在却很苍老,但颇为温柔。
当适时,电脑里放满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弓弦似乎就在心室上拉扯。而后鼓足勇气看《白比姆黑耳朵》。
他有过幸福的家庭,可是四年前儿子死在山上,妻子悲痛过度也随之撒手尘寰;他有过卫国战争的经历,他在战场上的伤痛郁结成文字,他靠写作打发退休生活;他养了条塞特种小猎犬,和它相依为命,它不幸是个病变的白化狗,他不幸顽强地活着;它有一对黑耳朵,他叫它比姆,告诉它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一条像它这样的好孩子;他带它去打猎,远远的树林子,春天时深深浅浅的蓊郁,秋天有美丽的斑斓,他们其乐融融,不介意打不到任何猎物;他放它独个儿散步,它自己撒欢,看街景,然后用爪子挠门,乖乖地回到他身边。
可是有一天,心瓣上的弹片又在折磨他,他被送到医院抢救,送到莫斯科做手术,它呜咽着,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他的身影。它沿着铁路飞奔,盼望得到他的爱抚;他对医生说他唯一的亲人就是比姆,拜托邻居拍来它的照片。它被好心人收养,被狠心人虐待,它想回到家,等待他做完手术轻轻地呼唤它:比姆卡,我们去打猎!他攥着一把老骨头回到家乡小镇,却只能在捉狗队的卡车车厢里,看它冰冷的小身体最后一眼。他对那些一路追寻来的关爱着它的孩子们说:它不在那里……
坐在碧绿的林子里,他看男孩跟小狗嬉戏,“比姆——”,他又产生了幻觉。
也许是冥冥中谁在眷顾,吉洪诺夫主演的《白比姆黑耳朵》两张碟,被盗版商做颠倒了。我先看到吉洪诺夫抽空的眼神,后看到他去领养狗狗,就像是看完正片看前传。这样也好,如果情绪积累下来,最后还不知要怎样难过。俄国人,即便在苏联时期,拍的电影也地道的悲哀到骨子里。
比姆是个异数,它有优秀的血统,却因为毛色不正拿不到认证资格,可它无疑是漂亮的,聪明的,善感的,人性化的,它的乖巧伶俐是它成为悲剧角色的重要砝码;老伊万是个常数,他像卫国战争幸存下来的大多数战士一样,即便饱尝孤独,却仍旧对生命充满感恩。他懂得阳光雨露都是自然造化至美的体现。他在狭长的空间内活着,对缄言的伙伴倾注全部爱心。他把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却保留不住属于自己的一点。比姆伤痕累累吗?比比姆更伤痕累累的,就是主人伊万的内心。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四日,这一年还没有过完,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就逝去。太突然。周日中午,突然得知噩耗,我沉默半晌,转告远方的朋友本来老六,并且说,“你会为吉爷爷写点文字吧?”老六允了。今天,另一位朋友戏作三昧也发短信来,“天,才看到吉洪诺夫死了啊,居然八十一岁了,我觉得他还很年轻”……
对于我辈喜爱苏俄文艺的,吉洪诺夫的《战争与和平》《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白比姆黑耳朵》又怎能遗漏?我很想得瑟地说,我还看过他在《红天鹅》里扮演基洛夫的艺术指导古雪夫,《敌后前线三部曲》里的红军军官,《银翼上的红星》里的航校团支书,还有一直压箱底的《他们为祖国而战》《青年近卫军》……
但是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大前天的日子里,施季里茨同志,永远退休了。
2009年12月4日
停不了的红舞鞋
大梦谁先觉
幼年时,很喜欢舞蹈,常常闻乐起舞,没有定式没有师承,每个动作都是很稚拙很简幼,但乐此不疲。那个时候,曾经梦想着今后过一辈子穿着红舞鞋的生活,在追光下,在掌声里,像风,似有若无;像蝶,飘飘若仙;像魅,来去无踪。
也莫名其妙对西域感兴趣,沙丘、绿洲、面纱、罗裤、手鼓……在那个名曰“长春”的城市中,从电视和画片上捕捉着阻隔时空的诱惑。幻想着某个清晨,脚铃像天然的装饰一样附属在细幼的踝上。
爱的莫名,想法诡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部舞剧《丝路花雨》,相当出名,相当唯美,相当向往。从得知到有机会看,盼了一年多。家里搞到几张招待票,马上所有的憧憬都化为一饱眼福了,我心里却坚定地说:不去。
父母都知道我曾经多么渴望,更奇怪我不去观赏的执拗。我一个人待在家中,想象着,激动着,不能自己。
有一首歌说“相见不如怀念”,而我更喜欢“怀念不如期待”。相见是既成事实,怀念是追忆似水年华,期待是可望而不可即。
可望而不可即,会调动全身心在临渊的巅峰状态。脑袋里一些超现实的、匪夷所思的、惊鸿一瞥的构想碎片,一旦化作真实的舞台、幕布、道具,来来去去跳跃着的演员,似乎是一件恐怖至极的事。想象被阻隔在真实的门口,犹疑不决,而那不是我想看到的。
那时候,我才四岁,是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的年纪。
那时候,文化活动还不发达,也鲜有电视转播。
当然,大人们回来说舞剧太棒了。
当然,我的不动声色下泛起一丝后悔。
当然,我也没能正规地学习舞蹈,做舞蹈演员,成名成家。
丝路花雨,大漠敦煌,却终于蝶破庄周梦般,进驻我的心田。
十四岁上,有缘沿当年的丝绸之路,拜谒敦煌。敦煌在我心中的圣地角色,已从舞蹈转向了绘画,长袖善舞的飞天们不再啼唱迦陵频加的歌声,而是用绚烂到糜烂的色彩将我窒息。
佛说,我看到的越多,即是我的业力太重,有太多的东西还割舍不下。
世纪之交,又有一部舞剧《大梦敦煌》,也是当年《丝路花雨》的歌舞院推出的作品。我不能再次错过这难得之机了。
有了经历,便懂得包容。眼睛里充满着渴望,经历等于空白,手中仍空空如也。
坐在剧院里,感受人为营造的时空差。一世纪前看守莫高窟的万恶的王道士,将千年前浓墨重彩的凄美绝唱展现给众人——丝绸之路上,两个地位悬殊的年轻人,分别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之旅。
月牙儿,镇守边关的将军之女。任性,冲动。女孩儿中的英姿飒爽。
莫高,奔赴敦煌的江南画师。忧郁,孤苦。男子中的纤弱敏感。
就在濒死的沙漠中,漫天飞舞的墨色的天女,月牙儿像一泓清泉跌落进莫高干裂的心叶。爱情的种子萌生在救命的水壶里,茁壮在邂逅的惊喜里,缠绵在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艰涩里,荼靡在以我死换你生的决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