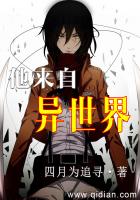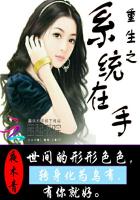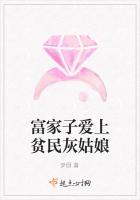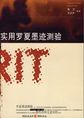夏目漱石有个小说,名字叫《哥儿》,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哥儿喝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价值一钱五厘。之后有人在哥儿面前挑拨,说那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哥儿马上想到了那杯冰水,第二天,就把一钱五厘扔到了那朋友的桌子上。他认为,虽然只是一杯冰水,接受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的恩情,实在有损自己的面子。虽然只是破费他一钱五厘,但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死了也于心不安。受别人的恩惠,默不作声,就表明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自己喝的那杯冰水,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但他却硬要争着付,弄得自己心里总感到内疚,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自己虽然无权无势,却有独立的人格。要自己低下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简直是一百万元的回敬。
这一钱五厘让他想得如此多,如此有涉原则,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曾经,我们也有卫生工因为被冤枉偷了十元钱而自杀,舆论想到的是:她为十元自杀,不值。没有人想到那已经不是十元钱,而是关乎人格。
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里,说了一个极端的事例:有一个商人,出于好意提醒一个武士,说他背上有只跳蚤,竟被那武士劈成两半,理由是:“因为跳蚤是寄身于畜生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生等同看待,是不能容忍的侮辱。”
但问题在于,你身上到底有没有跳蚤?
6
我手头上写的长篇小说《移民》,里面有个日本人叫渡边的,是白领,是我在日本期间再熟悉不过的典型的日本人。其实在当时,我就在随身带的笔记本里给他画了速写,其中心词就是“精致”。
精致,并不只是“小”,把日本人的趣味理解成“小”是片面的。与其说日本人喜欢“小”,毋宁说日本人讲的是“精”,精到极致,不达完美绝不罢休,也就是“洁癖”。
中国人喜欢嘲笑日本人,谓之“小日本”,得意于自己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日本虽然地不大,但能够极其有效而且科学地利用;本土的物产不多,但却物质极度富足,而且全是优质的,不像中国那样,几乎没有一样食品让人放心。即使是军队,他们只有自卫队,但从武器到人员素质,都是极精良的。至于人,众所周知,日本人是世界上国民素质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的精致,是着重于实质上的,不像中国人那样重排场,说是大而化之,其实是粗疏。
我说日本人重实质,一定会有许多人出来反对。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平江不肖生。在他的《留东外史》中,恰就写到了相反的例子。他引用中国武林高手郭子兰对日本剑道的批评:“日本射法流仪太多,闹不清楚,其实没有什么道理,拈弓搭箭,手法微有些不同,又是一个流派。”另一个叫黄文汉的,说得更刻骨一些:“大凡一样技艺,习得一多,就不因不由地分出流派来,其实不过形式罢了,精神上哪有什么区别?都是些见识少的人,故意标新取异地立门户。”哪里是重实质?分明是地道的形式主义嘛!
不仅中国人,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法国人罗兰·巴特在他的《符号帝国》中,就用“套盒”来比喻日本文化特征。日本文化的本质就像日本传统工艺品——漆器套盒,从大到小,一个盒子套进另一个盒子,尽管里面空洞无物,但是盒子却很精美。他称说,这是“一种极端的艺术创作”,也就是包装的艺术。他说:“人们精心地运用那种制作技巧,运用卡纸板、木头、纸张、丝带的相互作用,一丝不苟地在上面画出几何图形……由于制作非常完美,这种外皮往往重复制作,你可以没完没了地拆开包装。这种外皮推迟了人们对里面物品的发现,里面的东西通常是无关紧要的,这恰恰是日本包装的一个特点,即里面的东西微不足道,它与外皮的那种豪华不成比例;一块糖,一块小豆糕,一件普普通通的纪念品,像一件珍宝那样显赫耀眼地包装在里面。这样一来,礼品似乎就是那个盒子,而不是里面装着的物品。”
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很多都有类似的经历:接受日本人的礼品,看着掂着挺有分量,打开,是一层包装;打开包装,又是一层包装;再打开包装,仍是一层包装;最后终于看到礼品了,却是一把小扇子,或者一双筷子,或者一条手绢。确实是包装重于礼品,形式大于内容,正如罗兰·巴特说的,礼品是盒子。但是且慢,那扇子或筷子也并非不精美,也包括罗兰·巴特所说的糕点,日本的产品没有不精美的。罗兰·巴特所以感觉普通,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原先的期待太高了,他觉得既然是礼物,就应该稍微贵重一些。但是日本人是不送贵重礼物的,不关日本人小气,也不关巴特贪心,如果要归咎,只能归咎于巴特所说的文化了。
顺便说一下,罗兰·巴特所说的漆器套盒,并非是日本专有,中国也有,而且日本的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西方人不知道,就好像他们一想到东方绘画,就想到浮士绘一样。我的家乡就有很多脱胎漆器,当年去日本,也带了几个去,送日本人。结果到了日本,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同样的东西,人家做得精美得多。这就是日本人的产品。罗兰·巴特所见到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产品吧,即使只是作为包装。一个能够把包装盒做得如此精美的民族,内里的礼品,能做得不精致吗?
但是仍然有人不认可,那就是我所写的渡边先生。作为日本人,他最有发言权。他深陷在这样的精致之中,那是铺天盖地的网,那是沁入毛孔的风。是的,它是内容,也因此更令他欲罢不能。它成了深入骨髓的法则,不能越雷池半步。“水至清则无鱼”,我们可以想象,渡边在这种环境中如何奄奄一息。他努力突围,晚上去泡吧,去胡闹,但日本是个井然有序的国家,他的突围,只能是虚拟的,他被控制在这种法则中。疯狂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得照样去接受那种法则,尽管内心大不以为然。
于是我们看到,形式又确实大于内容了。虽然渡边们都不认可这种束缚,但是他们又都遵守了,并且遵守得很好。于是我们看到整个日本社会对规则的绝对顺从,不这样,就被罢黜于日本社会。当形式大到能够吞噬内容了,其景象是多么的可怕。于是我们看到,即使有异端,也很快式微了,被阉割了,被同化了,被清洁化了。即使有人坚守着内心的独立,但又能坚守几何?心是会游移的,心靠不住,这点上,当代企图守住“底线”、“底线”却在步步调低的中国人,一定深有同感。哪怕是信仰,也是集体共同意识的产物,如果被共识为“异端”,没几个内心不打鼓、能够坦然的。而法则是明确的,也是容易把握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指标,甚至只是合格的程序,就可以被认可,就可以心安理得。哪怕是杀人放火,但只要语言干净,就可以被文明化。哪怕是强奸敌国妇女,只要有崇高的理由,就可以坦然行之(我的《移民》里就写到了这么一场日本军人对被占中国的妇女的轮奸:列队,排到了,向长官立正、敬礼,然后钻进帐篷,脱裤子。完事后,出来,再敬礼,俨然是执行了庄严的任务)。只要厘清“从西方人手里夺回亚洲”的逻辑,就可以越界侵占他国。
哪怕是被确认为犯罪了,也可以通过仪式来洗罪。其实,日本人除“晨浴”外,还有一种洗罪的仪式,那就是沐浴戒斋,然后去神社举行禳祓仪式。经过这种仪式,犯了罪的人就清白了。对日本人来说,犯了罪,只要经过一次或多次的“晨浴”,就可以清白了。
于是,无所谓清白,无所谓罪恶,所谓日本人的“洁”,某种意义上只是“空洞”。空洞是极其可怕的东西,不问内容,只知形式,任何内容都可以装进这个形式里,包括暴力。
其实,清洁本身就是滋长法西斯的温床。希特勒当年就是以清洁的名义施行屠杀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不也是一种“洁癖”吗?一切以清洁的名义,这是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理由啊!清洁,有多少罪恶假你之名!在追求清洁之下,潜藏着多少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