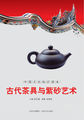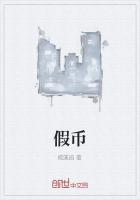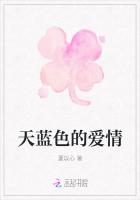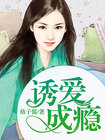傅秋芳家的婆子来到荣府,本意是想高攀一门亲的,但派了两个婆子来明察暗访后,好长时间就没了音信,多半是黄了。只是在高鹗先生的续书里,又约略地提到了,竟然还是“痴心”不改。莫不是那傅秋芳慧眼识真人,知道宝玉那一番呆症正是世间少有的多情?
两个婆子来时,宝玉正哄着玉钏喝了一口小莲蓬汤。玉钏手里端着汤,忙着听两个婆子说话,宝玉伸手要汤,谁也没太在意,两下里接差了,将碗碰翻,汤洒出来,烫了宝玉的手。宝玉忙问玉钏,烫了哪里了?疼不疼?宝玉一心只想讨玉钏的好,那婆子见了便认定这宝玉真是呆气,又想起宝玉下雨时自己淋得水鸡儿似的,还在那里喊别人避雨,更是呆气。估计回去汇报时,肯定会把这些当笑话讲给傅家人听,除非傅家老大对贾家的门第看得太重,不然傅家怎么肯把那么聪明美丽的傅秋芳的终身托付给这样一个人?
别说傅家的婆子没见识,宝玉在自己家的名声多半也是这样的,那些笑话可都是贾家人自己说出去的。他的父亲贾政看他不合自己脾胃不说,连拿他当命根子的母亲也只是别无选择才疼爱他,若是珠儿活着,王夫人还会不会这么拿他当命根子地护着可就真难说了。黛玉一进贾府,王夫人便把宝玉的毛病告诉了黛玉,一点也不知道替自己儿子隐瞒着点。
宝玉是不肖子孙,在赖嬷嬷的眼里看来却不是天生的,原因就在于老太太一贯护在头里。谁没有过花朵般的少年,只是没有宝玉这般绽放的。回忆起贾政小时候:“你爷爷那个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象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赖嬷嬷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只恨宝玉挨揍少。但贾母就不这么看,贾政正要培养一个棍棒下的孝子,贾母急忙拦住了,并且很生气地质问贾政:当初你老子是怎么教训你的!显然,如果和贾政教育宝玉的方法一致,那就跟贾政小时候的待遇一致,教育方法一脉相传,老太太也就用不着生气了。若不一致,赖嬷嬷的话就有问题。不过,赖嬷嬷与贾母都老了,记忆出现偏差在所难免。
宝玉独得贾母欢心,这欢心首先是看着这孙子长得可人意儿,而这可人意儿竟然也还有贾母说不出的理由,那就是与当年的国公爷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贾母怀念过去,而孙子相仿的相貌和蓬勃的朝气恰好弥补了岁月的缺憾。不过,这当然不是全部,重要的还包括宝玉出生时嘴里便含着的玉。古代不平凡的人出生都有些异兆,不是红光满室,就是天星坠怀,但多如幻景一般,没人能证实确有其事。宝玉就不同了,人家口里衔着物证,让人反驳不得。这就非常人可比。贾雨村一听冷子兴说到这,便说果然奇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冷子兴说,都这么说,试他将来志向,政老爷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两个为此还辩论了一番。但都这么说,还是说明这一个物件是很能打动人心的。贾母为说服众人自己不是无理由地宠爱这个孙子,还说这孙子懂事,知道孝敬,折枝花都想着插老太太、太太屋里。只这一件,老太太、太太都高了兴,爱屋及乌,把压箱子底的旧衣裳赏给了宝玉屋里的秋纹,让秋纹兴冲冲很是得意了一会儿。
其实要说起来,宝玉不肖其父,却肖其祖母。老太太喜欢乐事,下雪天见姑娘们赏雪作诗,她也乘了一顶小轿跑了来添麻烦,李纨只好赶紧把狼皮褥子铺在地上。老太太又撕了一点子鹌鹑腿子肉吃了,下一道作诗不如做灯谜的命令就赶紧跑屋里暖和着去了,还说是要看惜春的画画得怎么样了,年底前是否能交工。老太太走了,那只是因为年龄的缘故,受不得寒冷,但那一份热心,却是尽人皆知的。宝玉也是这么“无事忙”着,事事掺和,人人关心,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不寂寞,为了享受那点世间的生活。有那么段时间,宝玉心情不爽,诸事不顺,遇谁与谁闹别扭,后来就读了庄子文,写了篇字发泄心里的怨气。黛玉她们读了宝玉的文章,以为他要出家,赶紧劝谏,结果只简单问了他几句话,就打消了他出家当和尚的心思。其实哪是黛玉她们的功劳,只是宝玉借坡下驴而已。人生乐事还没过够,哪里肯先放弃。这一点也是传承了老太太的基因,贾母听到甄家被抄家了的事,心里自然不快。但她只让不快停留了一会儿,立即转移了关注点: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别人家的事未必不牵连自己家,贾家盖园子时,贾蔷学办事,到江南采购,用的就是存放在甄家的五万两银子。老太太经多见广,怎么会连这点都不理解?但老太太若是因此一筹莫展,家下人大概就要惶惶不安了。老太太以自己的举重若轻轻描淡写,把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消弭于无形,不仅是处变不惊,也与得乐且乐的心理有关。
若说宝玉完全是老太太一般的行径,那就错了。二人还有截然不同之处。老太太年轻时可是比凤姐还说得做得,不然就没有这般的道行了。宝玉却不理俗务,完全超然物外,却花费大量心思、精力关心世人都不关心的事物,自哭自笑,与鱼燕对话,对星月兴叹;爱惜起东西来,连个线头都是好的,糟蹋起来,值千值万都不管了;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不读书求进,不喜与当官的交往,只喜欢在女孩群里混;没上没下,没有等级观念,种种不为世人理解的怪癖,却是死不改悔,全然不理世人的非议。若在今天看来,宝玉的行径实在是超前,具有众生平等的意识,重情不重礼,不屑于做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之流,关爱世间万物,又是情痴情种。
世人的非议多是因为不理解,每个人的观念不同,看世界的目光不同,所理解的世界也就不同,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来。书中说傅家的两个婆子是“极无知识的”,以她们的阅历来看,自然是俗之又俗之人的看法。但宝玉与现实脱节,与环境抵触的思想与行为,使他在世上的知己却不多,甚至可以说只有黛玉一人,曲高和寡,宝玉的境界多数人还是难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