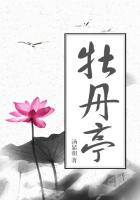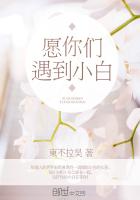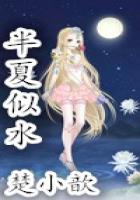她坐在我的面前,朴素的衣着,常见的剪发,显出中年妇女特有的稳重与端庄。交谈时,她红红的脸庞上总是漾着平和的微笑。
这微笑,引起我对她往昔生活的回顾——
十一年前,她的公爹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去世了,撇下了一个近六十岁的老伴和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娘。
抹去眼角的泪水,她站起来,对丈夫说:“把咱娘和咱奶接来,我侍候两位老人。”
那时,她只有三十二岁。
她用微笑,消除了丈夫的忧愁。
两位老人接来了。
在失去亲人的沉重打击下,她们神志恍惚。当她们惴惴不安地来到这间不足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时,心里疑惑了:这,能行么?
她微笑着迎上去:“奶奶、娘,咱家地方小,让二老受委屈了!”
贴心的话语、亲昵的微笑驱散了老人心头不安的疑云,驱散了失去亲人的悲凉。
安排好二老,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又走了。
她默默地挑起赡养老人的重担。
她上班去,再三叮嘱老人:“奶奶、娘,我走了。你们上街干啥的可要小心,别跌着碰着。冷了就加件衣裳。”
下班回来,一进门就满含歉意地说:“奶奶、娘,饿了吧?我这就做饭!”
晚上,她从不串门儿,总是坐在两位老人身边,一边做活,一边微笑着和老人拉家常。她用自己的微笑唤起老人对生活的希望。
她和她的丈夫都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工人。微薄的收入用到一家六口身上,日子的艰难是可想而知!可她家里总是不断有肉食和水果,那是专供两位老人享用的。老人受了一辈子苦,再穷也得让她们吃好点。
苦吗?苦。可她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她终于病了。可她还是拖着病恹恹的身子侍候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婆婆实在过意不去了,含着眼泪,悄悄地收拾好行李,到她二儿子那里去了。
婆婆离家三天。这三天,她心里空落落的。一早起来,她总是照例到小厨房,推开门,为婆婆准备一份早点;晚上,她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想那不辞而别的婆婆,在老二家过得下去么……第三天晚上,她再躺不住了,半夜起来准备干粮,打算天一亮就去接婆婆回来……
门开了,婆婆顶着茫茫风雪,苦着脸回来了。
她扑上前去,抱住婆婆,哽咽着说:“娘呀,从今往后,你老哪儿也别去了。咱娘几个苦,苦到一块;甜,甜到一块。我侍候您和奶奶一辈子。儿媳有啥不好,您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只求您老别走了啊……”
病床上的奶奶哭了,两个孩子也嘤嘤而泣……
十一年过去了。
她微笑着告诉我们:这几年,她们家好过多了:她和丈夫都相继升了两级工资;厂里照顾他们,给分了一套宽绰的房屋……
她笑得那么亲昵,那么娴静,像一泓碧水,映出她那纯净透明的心灵……
后记:参加全国工人作家讲习班,结业时,将一篇报告文学的素材缩写成此文在《工人日报》发表。文中隐去主人公的名字,是想讴歌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