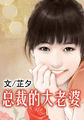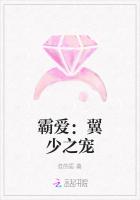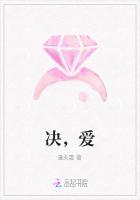皇甫东照回到家中,见只有母亲在家。他问后得知:小妹上学了;父亲的身体尚健,每月从“五·七”干校回家一、两次;母亲的疾病略减轻,已不点滴、喝汤药,但没有停药,--每天还在用口服药溜着、维持着。皇甫东照听后松了口气,将悬着的心放了下去。
母亲问东照,借的什么缘由返家。因不愿意让母亲伤心、劳神,东照隐瞒了选送工农兵大学生这件事情,只说自己不小心患了痢疾,鲁村的领导让他趁着麦收后的空闲时间回家养病。随后,他自我解嘲说这是寨翁失马,并扮了个笑脸来宽慰母心。母亲看着儿子瘦弱的身体、黄色的面容,眉头蹙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谈到父亲的工作时,母亲说:父亲去“五·七”干校后,家的门前冷落车马稀,“三结合”那阵子的热闹劲没有了,连那几位常客都不登门了。看现在的人情冷暖样子,政治的大气侯短时间内改变不了,近期内没有起用父亲的可能。
说到这,母亲笑了一下说:“这些年的政治风云变幻,潮起潮落的事情看得多了,对这些虚应景致的场面东西也就看淡了。好在你爸爸上次回来时的气色好了,饭量也见长,身子骨也好象硬朗了许多。听说,他多年的老病--神经官能症好了,这才叫因祸得福呢!你爸现在是吃得香、睡得着,越活越硬实。他还想站好最后一班岗,发挥余热,为革命再作点贡献呢!”
东照听到此处笑了,“呵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
母亲说:“我的心里,倒不在乎你爸是否出山重新主持工作。看见他精力旺盛、身体健康、心精好,我确实挺高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
当皇甫东照说,他要去干校看望父亲。母亲不同意,让东照在家休息几天,养好身体后再去干校。但东照心念多年没见面的父亲--着急,想当即就去‘五·七’干校。经母子的磋商决定:东照吃完饭、午睡后,下午去“五·七”干校看望父亲。
下午皇甫东照乘坐的汽车出城后,放眼看去,虽无黑龙江的万亩良田一望无垠的豁旷,却也有稻菽金黄、果红菜绿、‘牛衣古柳卖黄瓜’的乡趣。
东照下车后走了不长时间,便看到掩映在绿色林带后面的红砖房舍,--“五·七”干校。
皇甫东照走到干校后经寻问得知:父亲他们今天分组学习,--父亲所在的小组在食堂里面学习。东照找到食堂后,恰巧从里面出来个人,连忙上前说明了情况。那人回转身进食堂后不长时间,就将东照的父亲找出来了。东照见了父亲,连忙迎向前去弯腰朝父亲行了一礼。那人见了后,向父亲打趣说:“皇甫书记,你儿子还是过去的老礼、老令啊!”东照的父亲听了笑:“诗书传家、封建礼教,这些都是孔家店的东西呀。哈哈,批了多少回啦,家里的余毒还没有肃清啊!”然后,父亲与那个人分手,领着东照回了寝室。
刚一进寝室,父亲就问东照:“你是什么时侯回来的?”
东照说:“我今天刚到家。”
父亲说:“那么,你真不应该马上就来看我。你的妈妈天天想你,就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唱的那样:‘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她盼来盼去,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怎么不在家多陪陪她呢?让她奢侈、奢侈,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她太想你啦!”
父亲问:“家里邮的毛裤,你收到没有?”
东照说:“收到了。”
父亲说:“我回家的时侯看见你妈给你织毛裤,劝她不要织了,小心累坏了身体。她说黑龙江那个地方冷,怕她的宝贝儿子挨冻。--不听我的话,还织。她说自家织的毛裤密实、暖和。织完了毛裤,她还要为你打毛衣呢,--被我拦住了。”
父亲看着东照说:“你应该理解你妈妈对你的一片殷殷母子情。”东照点头。
父亲问东照在黑龙江鲁村的情况时,东照谈了选送工农兵大学生及自己患痢疾之事。
父亲听后说:“这么点考验你都承受不住,很让我不放心。
“现在确实有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的情况,按照等价交换的商品法则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报纸批判这是滋生特权阶层、新生资产阶级的土壤。”
东照插话说:“现在社会上编了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秤杆子、掌实权。当前这些人最热门。”
父亲说:“现在这屋里没有外人,咱们父子俩说点体己话。这些话你知、我知便可,不必让外人知道。”
皇甫东照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父亲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生活在物品繁杂、瞬息万变的当今社会,每个人都随时有不同的思想变化,有不同的七情六欲。我能没有父子情么?对我儿子的问题,我能不加以考虑么?老牛尚且有舔犊之爱,何况人啦?”
“呵”,父亲看着东照说:“你之所以跑回来,是因为心里不托底,所以促动我来啦。”
东照忙说:“老爸,这话您言重了。--我那敢促动您啊?!”
父亲摆摆手,说:“你不用解释。就算你患痢疾与工农兵学员这件事无关。你回家养病,总该与此事有关吧?你不顾旅途劳累,急匆匆的跑回来,能与此事无关吗?况且,你是需要将养的带病之身呀。”
东照欲言又止。
“小伙子,你着急啦!沉不住气啦!呵呵。”父亲笑后,又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形势如此,不怪你着急呀。春风没到黑龙江以前,早就又绿江南岸了。许多老同志已经辗转找关系往回办子女了。孩子,也是考验革命者的一关嘛。这道感情关难过呀!但是,我没有象老同志那样:为你铺路、打前站。你的心里埋怨我吗?”
东照摇头:“没有。我理解你,我还没到让私心催得使父亲为难的程度。”
父亲点了点头,说:“你别听方才那位还朝我叫皇甫书记。他们当面还叫我皇甫书记、皇甫主任,背后早就称我为老皇甫了。老皇甫(黄浦)?呵,听着怎么象蒋光头--蒋委员长的嫡系呢?
“没什么,人不在其位了嘛,怎么称呼都无所谓。
东照说:“回来后听我妈讲,咱们家现在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人都势利眼。”
父亲说:“我不在意这些过眼的烟云。”
父亲从暖瓶中倒了杯水递给东照,说:“我对你讲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想要告诉你,我现在不在位置上,没有能力啦。--请你不要难为我。哈哈,如果舍得脸皮,老同志、老部下们还是能卖给我面子的。
“我的意思是说:要谨慎、向远看,不能近视眼。”
东照听后点了点头,似有所悟。
父亲喝了口水后说:“当年,毛主席把儿子岸英送去学农,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为了革命,主席的家人吃了许多苦。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用意是很深的,看得是很远的。在思想、理论界有研究意义。
“我对主席‘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这个指示的体会是:知识分子经过农村、工厂的劳动锻炼,才能真正了解劳动人民,心里才能想着劳动人民;说话办事、处理问题时,心里才能有谱,才能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这是解决立场的问题。心系劳动人民,才不容易摔跟斗。只有种了牛痘后,才能对天花有免疫力。
“过去的那些名门望族、历朝历代的皇帝,如果能想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不至于家败国亡时才捶胸顿足。呵呵,我这话不符合阶级斗争学说。--不足以与外人道。”
东照听后理解、点头、笑。
父亲压低了声音说:“现在要求知识分子又红又专,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人家外国都电子工业、信息化了,我们的知识青年却在学习抡镐头。当年的理想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许多地方还在镰刀、锄头。”
东照点头,“是这样。黑龙江的许多地方连电灯都没有,甚至有的农家连铺炕的席子都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