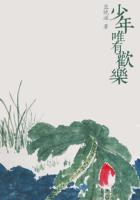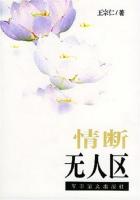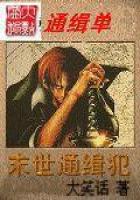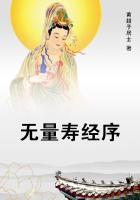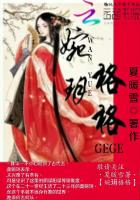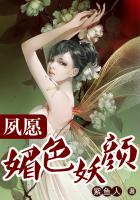清明节、过年时,给玉容烧纸钱,随着优优年纪的增长,她越来越不在意这些事,后来国盛都不提醒她,瓣瓣总是在遥远的其他地方,她也把奶奶忘了吧。他想:孩子们忘了也没办法。每年清明前后,国盛无论如何都要回乡下去扫墓,主要是给玉容的坟墓上上香、敬几个从德华酒楼买的包子,父亲和母亲的墓和其他人的墓集体迁过一次,墓碑没有了,村里人只是向他大致指了一下埋尸骸的地方,就在玉容墓的旁边,国盛想给他俩立个碑,但是一想到要花钱,就把打算搁下了。看到埋亲人的那座小丘,国盛就记起了父亲,忍不住自嘲说:“你们的老爹爹是个剥皮赌,有一点钱就赌,弄得我们全家全是些赌棍。”大小孩子们就在一边笑,说是哟。
早几年,每次去上坟,是用老二的车,至少两辆,可以坐下全家人,老二垮了台,就用老七老公刘武战开的公车,家里日益衰落后,国盛也不好向刘武战借车了,总是说他忙,不要找他。有时老七不管这些,一定要刘武战抽个时间把公司的车开出来,国盛给钱他,刘武战只能开一辆车出来,只能坐几个人,通常是国盛、优优是一定要去的,有一年就是坐刘武战公司的车,结果刘武战的车与别人的车撞了一上,把车灯撞坏了,还刮了漆,老七一个劲说:“这可怎么办?回去怎么跟他老板交待?”国盛只有说:“修车的钱我出。”这样修车的钱都花去了两、三千。
有一年是国盛租出租车和老四一起去的,儿子没收入,租车的钱是国盛出的。
国盛生前最后一次去时,老五带了照相机,国盛和老七在墓碑前照了相,有一张还是国盛的单人照,他穿着他唯一一件夹克上衣,这件深蓝色上衣是他在汉正街买的,夹层的,保暖,便宜,是他买给自己过年穿的,优优说他穿这件衣服很好看,国盛自己也觉得穿上去很精神,听到孙女这样说,自己就呵呵地笑。瓣瓣每次说要给他买衣服,他总是不让她买。他其他所有的外套都是中山装,薄的,厚的;腿上一条他在菜场附近的小摊上买的看不清是黑色还是深棕色的裤子,料子不好,不透气,国盛主要看中它便宜,在这个小摊上,他还给优优买过一件高领深棕色秋衣,优优不爱穿,嫌老气,气得国盛说:“还要有人给你买哟!”因为天气还有些凉,国盛的头上照旧戴着一顶深蓝色有檐帽,有一顶他戴了十几年,里面衬的人造革都被磨破了,国盛用报纸垫在里面,优优看到了说他怎么戴这样一顶帽子,她说要给爷爷再买一顶新的,反正也不贵。但是到盛锡福去一看,却不知道爷爷的码子,一搁就搁下来。盛锡福一楼的门面已经租出去了,卖十几岁的小姑娘喜欢的小玩意,旁边有个楼梯可以上楼至盛锡福,楼上的营业员比顾客还多,又过了几年,那一条街上的房子全拆光了,建了沃尔玛超市、大洋百货商店,盛锡福也不见了。
国盛自己在小摊上买了一顶帽子,原先那顶是毛料的,摸上去很舒服,市面上的东西越来越便宜,但是质量也越来越差了,新买的那顶又轻又薄,像纸糊的,不过样子一样就行了,国盛买过毛线织的帽子,戴上去人显老,所以他只戴有檐帽,样子就像八十年代初,他又开始做生意时流行的那种八角军帽。
国盛每天都看《新闻联播》,有时他说:“真要感谢******,没得******,哪有我们这样的个体户?”大多数的国内新闻他都不喜欢,觉得假,但仍然看。瓣瓣上大学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来对国盛说了,国盛说好。他觉得瓣瓣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既然瓣瓣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中国共产党肯定有正确的地方。但是瓣瓣从来不对他说,他也不问。
国盛越来越苍老了,但是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慈祥了,而且他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加爱说话了,比在282号还爱说,说的永远是7个子女的事,个个都不孝顺、不听话、败家子,他不光在家里人面前说,对来看他的郑果说,对弟弟说,甚至对每一个能坐在他身边不叫他闭嘴的陌生人说,他们都说是他将家里的丑事全宣扬了出去的,他却不能忍住不说。
国盛先还说人心坏了,解放前是人愿意帮助人,武汉天气热,经常有人在路上中暑,马上会有路人扶中暑人起来,自愿去药店买十滴水给中暑人用,或者帮助刮痧,连玉容都会刮痧。过年前,从腊月24到三十,可以在总理铜像前“啄”米票,穷人家的女人们坐成一排,头上插根稻草,腿间夹个火盆,周围做生意的有钱人悄悄塞米票,一升米票可以吃2天,有的可以一次接十几张,国盛有钱时也送过,在他们家极穷时,玉容也等在那里拿过米票。佛教协会门口常为赈灾施粥,每天早上,都有叫花子来“赶斋”。所有药店到热天,门口都发水喝,用金银花、薄荷泡的水,一大桶,用瓢舀,过路人都可以免费喝,药店还给河边扛包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送去,谁都可以喝。后来他都不说了,就这样。
瓣瓣在上海读大学时还成了佛教徒,有一次回来将一颗小丸子给爷爷要他吞下,国盛想都没多想就吞下了,然后问她是什么,瓣瓣说是她的佛教上师给她的,吃下去有好处。国盛呵呵笑着,只是提醒她不要乱花钱。国盛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她的太奶奶是虔诚的佛教徒。
有时孩子们用话刺父亲,国盛要么不动声色,要么干脆摇着头,面带微笑说:“耳朵不行了,耳朵不行了。”他有时是真的听不见,右耳最先听不清的,听什么都像耳朵被蒙着了一样,儿女们都嫌他话多,优优最不爱听他说家常,只有他提起家里的哪个人哪件事,她就噘起嘴巴,不是说“听过了听过了”就是说“你以后再莫在别个背后说别个了”,他只是很想讲,太多事情他没法解决,只有跟别人讲一讲,他才觉得舒服一点。搬家以后,他就渐渐习惯了自言自语,耳朵好像就是从习惯自言自语后有时有点失灵的样子的,他想自己还终于是老了,这很正常,他不担心,也不害怕。优优搬出去住了,晚上284号常常只有他一个人,他熄了灯,倒头就睡,很早就起床出门到江边走一圈。
孩子们现在给他的买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他觉得孩子们给他买东西是在浪费自己的钱。他们有钱时,给他花钱,对他而言,是种应得的享受:老六年轻时给他买的那块“海鸥”表,早就走不动了,他锁在唯一一个上锁的抽屉里;老六有钱时给他的羊毛衣服,他每件都留着,一样背心有三件。甚至老二很久以前为了让父亲别管他们家事时给他的收音机,他都留着。
老二和江白闹离婚的时候,江白几次神情恍惚地来赵家诉苦,国盛曾经对江白说:“你去跟我家老二说,看在伢的份上,不要轻易离婚,那个女人,我是不准她进我赵家门的。”老二知道后,拿了个新的收音机来,对父亲说:“您以后在家里听听收音机就行了,莫管儿女们的事。”把国盛气得变色,但是说不出任何话来,那是老二气焰最盛的时候,也是他最得势的时候。那个他一拍桌子,孩子们就没人再敢说话的时候过去了,在他不经意间,在孩子们过上了比他好得多的生活的时候,在玉容去世以后家里不再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后(父亲,总是赌博,是个文盲,爱打人,只有母亲,勤劳,善良,勇敢,清白,无私,真正的无私,从来没为自己的生活着想过,永远只是为了孩子们和丈夫,糖尿病,风湿,都是因为长年在家里裸露的地上操持家务沾上湿气引起的)。
当他放任孩子们去糟蹋他们的生活(他们赌博、嫖女人)以后,他们却暗地里怪他是个自私的父亲,只顾自己享福。
国盛的觉是睡得越来越少了,优优则保持着她从小养成的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在她小时候,赵家人睡懒觉都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会让人感到羞愧的事情。老六完全失去生活来源以后,曾经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家里睡觉,他的新习性也影响了一同住在282号的优优,她学会了睡懒觉,学校和前途都让她感到没有希望。
起初,国盛是不能原谅优优这样做的,想到她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姑娘,她早早起床做什么呢?家里不用她做任何事情,这样一切就都可以原谅了。接着国盛也能够在大白天里睡觉了,毫无愧意。
优优对国盛晚睡早起、白天时不时睡一觉的习惯很纳闷,她会问爷爷:“爷,你怎么起得那么早啊?”或者,“爷,你怎么又睡了啊?”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能对国盛称“你”,必须用尊称“你俩”,优优素来没有纪律观念,我行我素,她可以大大咧咧地称国盛“你”,国盛也不生气。听到她那样的问题,国盛会对她说:“爷老了,不像你们年轻人。”
国盛喜欢清晨起床后到龙王庙边转转,那里修葺一新,依稀又有了解放前的风采,人来人往,只是行人已不是当年的装束。不过无论怎么变化,流过它脚下的仍然是长江和汉江,汉江的水依然那么清澈,绿色的,是从家乡汉川流淌过来的,即使现在回去,仍然可以在路上看到它,少年时代,过汉江,是要乘划子的。
回到家里,就是一天漫长的无聊日子,真正的无所事事。
那只母猫从282号抱过来以后,生了两胎,生完第二胎就不见了,她先是常常窜到楼上去玩,最多两天就会回来,有一次出去了一个星期都没有回来,国盛知道她是不会回来了,很有可能是楼上的把她关起来了,但他不敢去楼上找他的猫,他觉得自己卖了282号,住在284号已经非常没有脸了,他不想去楼上找那些曾经被他看不起的没有钱、也没有子女孝敬的老人要他的猫。
第二胎里唯一剩下一只小黄猫取代了母亲的位置,他其他的兄弟姐妹早死的死,送人的送人。这只猫养了一、两年,是个成年的大猫了,常常跟着他,每次出去两天就回,国盛说:“它聪明,别人抓不住它。”尤其在优优不在的时候,这只猫更占据了他每日所关心的重点,他弄东西给它吃,它需要他,被需要是多好的感觉。
后来他把它扔在外面,它又回来了,他坐了几站公汽把它扔了,它再也没有回来。他扔它的原因是章鸣说要照顾它的,结果他不在的时候,没人管它,就像没人再管优优一样,即使他在家里,连省下一点饭给它吃的都没有,国盛干脆把它丢了。他不想,他不想成为任何一个人的负担。
优优回来时责怪他怎么把猫扔了,他说:“养着烦心。自己都养不活了还养它。”
养猫是从玉容开始的,她爱猫,不是那种常常把它们抱在怀里的爱,她是照顾它们,把它们当成一家人一样,她有时看人不说话,眼睛发着光,就像猫的眼睛一样,大而有神,似乎无比单纯,又似乎充满秘密。
猫,没有了。
282号,虽然对外说是给了国盛的侄儿子,但是国盛知道老街坊们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以前,他会和路过的老街坊开玩笑,到了284号,他就不怎么和老街坊们说话了,其实许多老街坊都已经消失的消失、死的死,和他同辈的只剩小珍了,她老了,一头白发,但是五官还像年轻时那样精致,皮肤也没有什么皱纹,只是觉得人干瘦了一些,她很少在街上走动,她是唯一一个活的岁数赶得上国盛的人。国盛知道她的孩子们都没出息,比赵家的还不如。
隔几家的楼底下的走道里有个裁缝,解放前也是个妓女,她认识凤,从80年代到90年代,她作了将近10年的裁缝,直到后来有一天再也见不到她。国盛看到她还会想起凤,只是他从来不提起这个名字了,而且这个名字似乎在他心里再也激不起任何一点波澜了,好像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有时他想凤如果去了香港应该是很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