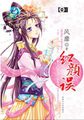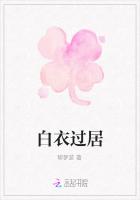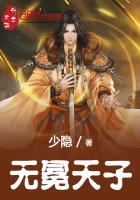那么也就是说,在庄子还活着的时代,“性命”作为一个合成词,已经出现了。只是在《庄子》内篇里,只有“性”和“命”,而没有“性命”,只有“道”和“德”,而没有“道德”。这可能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这一材料对于以此认定《庄子》内篇为庄子所作,而外篇和杂篇不是庄子所作这样一种观点是非常不利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持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庄子》的内、外、杂篇三编,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而内篇不是庄子本人所作,是庄子后学所作。
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他的理论依据在于内、外、杂篇体制的不同。古人写书有一个基本的体例:古代文章本来是没有标题的,一篇文章写出来,原本就没有标题,但是后来怎样流传呢?这篇文章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后人要给它安一个标题,怎样安一个标题呢?这个标题,往往是以第一句话中关键的两个字来命名的。
比如说《论语》,《论语》的第一篇,题名《学而》,第一句话是“子曰:学而时习之”,所以叫做《学而》篇。《为政》篇的第一句是“子曰:为政以德”,所以叫做《为政》篇。这种情况一直到孟子时候还是如此。《孟子》的第一篇,题名《梁惠王上》,第一句是“孟子见梁惠王”,所以这一篇的篇名,就被叫做《梁惠王上》。
而《庄子》一书的外篇和杂篇,也是以这样一种体例来命名的。比如外篇中的《马蹄》篇,第一句话是“马,蹄可以践霜雪”,所以叫做《马蹄》篇。《在宥》篇的第一句话是“闻在宥天下”,所以叫做《在宥》篇。《天道》《天地》以及《天运》,都是这样命名的。
而相反的,内篇却不是这样。内篇的第一篇叫《逍遥游》。《逍遥游》的第一句话是:“北冥有鱼”,如果要以这样一种体制来命名的话,那应当叫《北冥》篇。但却不叫《北冥》,而叫《逍遥游》。在整个这一篇中,找不到“逍遥游”这样一行字,“逍遥游”是对文章大意的概括。
第二篇《齐物论》,第三篇《养生主》,第四篇《人间世》,第五篇《德充符》,第六篇《大宗师》,第七篇《应帝王》,这七篇的篇名,都像后来人们命名那样,以一个主要的词汇,来对文章进行命名。
《荀子》书中的情况也是这样一种情况。《荀子》一书的篇名,比如说《解蔽》,比如说《性恶》,比如说《天论》,都不是以首句中关键的两个字来命名的。
而在《庄子》一书中,同时出现了这两种情况,所以任继愈先生认为,由这个情况来看,内篇应该在外篇和杂篇之后。
对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应当怎么看?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刚才反复强调,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这本书,在《史记》中,没有提到篇数,在《汉书》中,提到是五十二篇,不是三十三篇。
那么五十二篇,有没有内篇、外篇、杂篇这样的区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史记》中,在《汉书》中,提到庄子,提到《庄子》一书,根本没有这样的提法,只是说五十二篇。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分类。
有的学者考证,对于书的这种分类,把它分为内篇、外篇,这是由汉代开始的,先秦的文献没有这种分类的方法。
我们还要强调,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庄子》一书,是由郭象编定的。郭象把《庄子》一书编成内篇、外篇、杂篇三编。其实这种编次,并不是《庄子》一书本来的原貌。
据说郭象在对《庄子》一书做注的时候,把很多他认为无关紧要的材料,类似于《山海经》《搜神记》那样谈神说怪、荒诞不经的材料,都删去了,并且对有的材料进行了归并,所以才使原来的五十二篇,成为如今的三十三篇。
他把这三十三篇大体做了一个归类,原来有名的可能就保持原名,就放到了外篇和杂篇中,原来没有名的就给它起名。
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不能肯定说,《逍遥游》《齐物论》《应帝王》这样的名字,是由郭象命名的,但是《庄子》一书现在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状貌,却是出自郭象之手的。
如果我们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讲,说什么内篇如何,外篇如何,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不是庄子所作;或者相反地说,外篇、杂篇是庄子所作,内篇不是庄子所作。那么这里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郭象在改编《庄子》书之前,就已经知道哪些是庄子所作,哪些不是庄子所作。他把庄子所作的放在一起,把不是庄子所作的放在一起。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郭象对于这一问题有所肯定,或有所怀疑,也就是说,郭象对于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表现出怀疑。郭象从来没有认为《庄子》一书,哪些篇章是庄子所作,哪些篇章不是庄子所作。他是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形式,把它分成了这样三编。
所以,以郭象所编的《庄子》一书来确定《庄子》书中哪些是庄子所作,哪些不是庄子所作,这样一个基础,本来就是不成立的。这是我们必须说明的。
第二点要说明的是,对于《庄子》这本书,我们不能抱有先入之见,先抱有一种观念,认为《庄子》一书有一部分是庄子所作,另外一部分不是庄子所作。
如果我们放下这个先入之见,我们会发现,《庄子》一书的内篇和外篇、杂篇,它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特殊的理由非得要去说明其间有一个很大的矛盾。话又说回来,即使有矛盾,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内在的不一致,并不是不存在的。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二点。
第三点,如果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庄子》一书与《老子》不同。《老子》一书只有五千言。《老子》一书是在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写出来的。如果依照传统的说法,《老子》一书是老子应关令尹喜的要求写出来的。而且,老子有自己的固定工作,他是一个有职业的人。
而庄子则不同,据司马迁讲,《庄子》一书本来有十多万言,现在的《庄子》一书也有六七万字。这样一个规模,不可能是在短期内写出来的。庄子一生虽然曾经当过漆园吏,也曾经做过买卖,但庄子显然不是以做官或做买卖来维持生活的。所以,庄子一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从事写作。《庄子》一书也许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比如说二十年、三十年内陆续写出来的。如果《庄子》一书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陆续写出来的,那么,不同篇章之间有一些不一致,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事了。
第四点,退一步说,即使《庄子》一书有的为庄子所作,有的可能不是庄子所作,但它反映的思想是庄子的思想。并且,《庄子》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部历史文献。从郭象改编《庄子》和注《庄子》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对《庄子》一书做了非常丰富的解释,庄子的思想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影响了中国文化,影响了中国历史。
而庄子的思想,庄子这个人,我们是通过《庄子》这本书而得以了解的。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庄子,对后代人产生影响的那个庄子,不仅仅是约生于公元前369年,死于公元前286年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通过《庄子》这样一本书,以及这本书所体现出来的庄子,而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发生影响的。
而这本书是哪一本书呢?不是司马迁所讲到的那样一个《庄子》,也不是《汉书》所讲的五十二篇的那个《庄子》,而是通过郭象改编、注释以后这样一个三十三篇的《庄子》,是通过这样一个《庄子》,影响到中国历史,影响到中国文化,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事实,这也是历史。这一历史,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也是无法改变的。
庄子对于历史的影响,庄子对于今人的影响,是以《庄子》一书的全体表现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内七篇。这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且是现在仍然发生的事情,这种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庄子,我倾向于还是应当以《庄子》三十三篇为基础,应当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对庄子的思想做一个总体的把握,而不简单的局限于内篇,或者外篇和杂篇,应当把《庄子》一书看成一个整体。
庄子不是一个特定的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是影响了中国历史,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这个人物的思想,是通过《庄子》这本书体现出来的。我们研究庄子,只能通过《庄子》这本书。
也许人们觉得我的这种思想很保守,其实我在讲老子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观点,我认为后代的材料,在后代人发现的材料没有足以推翻前代人的记载之前,我们还应当维持前人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基本的介绍和说明。我对老子是这样一种态度,对庄子也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研究老子,也是以五千言的《道德经》作为基础的。我们研究庄子,也应以三十三篇的《庄子》作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