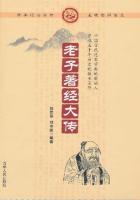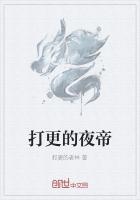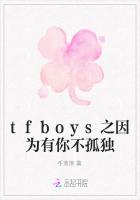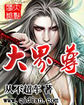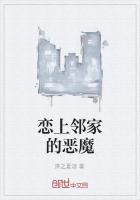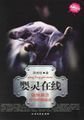这是寓言故事,是不假。但它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真实的。不要以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想当官,不要以为追逐于仕途是天下所有人的追求,不要以为没有当官不是不想当官,而是想当而当不了。当然,真有不少这样的人,不是不想当官,而是想当而当不了。但这并非所有人的想法。不想当,就是不想当,不是没有能力当,不是人们不拥护,只是不想当。这样的人也是不少的。
魏晋时代有所谓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中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嵇康,一个是山涛,他们是好朋友。山涛曾任吏部选曹郎,负责选拔官员,后来迁升为散骑常侍。山涛举荐嵇康出任吏部选曹郎。这件事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嵇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写了一封公开信,宣布与山涛绝交。这就是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在这封绝交书里,嵇康讲了自己为什么不能当官的一些原因。我们现在看来,这些原因似乎都不能算作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哪些?
包括:我这个人爱睡懒觉,当了官以后就不能睡懒觉了;我这个人爱钓鱼,当了官以后就不能钓鱼了;我这人不爱写信,当了官以后我不能不写信;我这个人不爱洗澡,身上有虱子,平时我穿得很简单,身上痒了想抓就抓,但是当了官以后,整天穿着官服,这事也不好办;我这个人不喜欢吊丧,但是当了官以后,就不得不做这件事情。
这些理由,在我们看来都不是理由,都不成其为理由。但是在嵇康看来,这就是理由。
我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我爱睡懒觉,我喜欢钓鱼,我不爱写信,我不爱与人交往。但是,当了官,就不能睡懒觉,就不能钓鱼,就不能不写信,就不得不与人交往。那么,我为什么要当官呢?山涛你是我的朋友,但是你一点儿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的这些感受。既然你不了解我,我们还算什么朋友呢?
庄子不愿意当官,许由、善卷不愿意当官,嵇康不愿意当官,这些人的想法是完全真实的。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当官?因为他们想过自然、自在、自由、自性的生活,他们感到当官以后就再也不自由、不自在了。
有人讲道家的人格是自然人格,自然人格就是没有追求,放弃追求。事实上,道家不是没有追求,庄子不是没有追求。庄子追求的就是过自然、自在、自由、自性的生活,庄子追求的人生,就是自然、自在、自由、自性的人生。
但是,庄子不想当官,他并不因此反对别人当官,也并不因此反感别人当官。庄子并没有反对惠子当宰相,庄子并没有因为惠子当了宰相就与惠子不来往了,就因此而讨厌惠子了。许由、善卷不愿意当天子,但他们并不反对、也不反感唐尧、虞舜当天子。嵇康与山涛绝交,并不是因为山涛当官而与山涛绝交,而是因为山涛举荐他当官而与山涛绝交。因为在嵇康看来,我不想当官,我也不适宜当官,山涛作为我的朋友,应当是了解的。但通过举荐我当官这件事,可以看出,山涛根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我们又做什么朋友呢?
在道家看来,在庄子看来,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一个自主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感受、独立的追求;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自主的个体,也应当是一个自性的个体。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的追求,但是,我绝不将我的生活强加于人,将我的追求强加于人。
一个人成为什么或不成为什么,这是一个人自己职权范围的事,这才是自由,这才是自主。一个人成为什么或不成为什么,不是做出来给他人看的,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愿望而做的,这才是自性。
陶渊明曾经当过官,后来又不当了。苏轼对陶渊明有一个评论: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陶渊明不是没有当过官,但是他当官,他不怕别人说他想当官。我想当官,而且我感觉到我可以当一个好官,我能够当好官,当官对我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满足感,这有什么不对呢?这有什么不好呢?后来陶渊明又不当了。不当就不当了,这纯粹是个人的原因,绝对没有想着通过这件事而表达其他的意思。不是想要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博得一片喝彩,获得一种名声。
一个人可以当官,也可以不当官。当与不当这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这里最为重要的是你对自己身心性命的一种把握。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想使生活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自由、自主、自性,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常常感叹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多少人官场失意而遁于道、释,可又有几人真正领悟到庄子的心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独立的人格。上下几千年,又有几个人不为地位、权势、名利所动,而只醉心于艺术与科学?此乃艺术与科学的不幸,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归宿似乎只有一条,就是投身政治,就是逐于仕途。“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优?社会如是看,知识分子本身也如是看。所谓怀才不遇,所谓生不逢时,只不过是仕途不顺、官场失意的代名词。相比而言,庄子的这种人生追求就显得非常难得了。
庄子并非没有政治追求,而是强调人首先应当自立。庄子并非要同现存政治对立或决裂,而是把个体精神的自由看得比其他一切都更为重要。庄子此种心机,一直不为常人所理解。
5. 精神的宁静与淡泊
《庄子》书中多次讲到真人、至人、神人、圣人,通过庄子对于这些人的描述,可以进一步把握庄子的人生追求。
什么是真人?《大宗师》从四个方面对真人作了说明。
第一,“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不逆寡”,不拒绝寡少,不因为什么事情小,就不去做,就拒绝接受。“不雄成”,事情做成功了,不以功臣自居。“不谟士”,士就是事,不计较,不算计。真人不是不做事,他也做事,但是他没有我们常人那样一种忧心忡忡,那样一种患得患失。
第二,“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真人睡觉的时候,没有什么梦,不做梦;醒着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事情。真人既不忧愁,也不患得患失。
第三,“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说即是悦。活在世界上,没有觉得这是令人喜悦的事情,面对死,也不觉得死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因为自己长寿而感到高兴,也不因为自己短寿而感到忧伤。
第四,“古之真人,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你理解他,赞成他,他是这样一种状态,他不会因为赞成他、理解他,而感到欣慰;你不理解他,不赞成他,他也不会因为你不理解他,不赞成他,而有什么烦恼。
真人是人之真。真人作为人之真,就在于他能够保守人的真实的状态,在于他能够保持自己的真情实感。他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清楚自己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是至人?《齐物论》讲: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
至人的特点是:不管外在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至人不会因为当前社会上流行什么、不流行什么,而改变自己的追求,或是放弃自己的追求。
至人做事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但这一准则不是利害的考虑,不是利害的计较。“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他还有什么可畏惧、可担忧的呢?
什么是神人?《逍遥游》讲,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这当然是一种神化的说法。神人的特点是超然于事外,超然于物外,对人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都能持一种超越的态度。
什么是圣人?老子讲到圣人,孔子讲到圣人,庄子也讲到圣人,但所讲的圣人都不一样。孔子所讲到的圣人,是古代创法垂范的圣王,比如像尧、舜、禹、汤这样的人。老子讲到的圣人,也是一个统治者,但却是一个自然无为的统治者,是一个以无为治天下的统治者。
庄子在《齐物论》里讲:
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
圣人的特点是不从事于务,不做具体的事情。“圣人无名”,人们可能不知道圣人到底做了什么事,甚至他什么事也没有做。
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其名虽异,其实相同。所突出的,都是心灵的淡泊与宁静。真人者,突出的是人的本真;至人者,突出的是人所达到的境界;神人者,突出的是与常人的不同;圣人者,突出的是人格的崇高与伟大。
《逍遥游》讲: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人皆有己、有私,至人所达到的境界则是无己、无私;人皆以建功立业为志向,神人则无功业;伟人之所以崇高、伟大,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丰功伟业,皆因其事,而圣人之所以崇高与伟大,则是因为他无以为名。真人、至人、神人、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能够保守心灵的淡泊与宁静。
6. 庄子的人格理想
有人以为,庄子的理想人格就是所谓的真人、至人、神人、圣人。这种讲法有失片面。真人、至人、神人、圣人,所突出者只是心性静泊的一面,此外还有精神自由的一面。庄子的人生追求,包括精神的自由与心性的静泊两个方面。
有人认为,庄子的理想人格就是自然无为,就是“人貌而天虚”,就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就是“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庄子并非纯任自然,他有自己的追求。
《天地》篇讲:
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謷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傥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
庄子反对追名逐利,反对为物所役使;庄子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洒脱,追求个体心性的宁静淡泊。自然者,是保守心性的本然状态;无为者,是于物欲而无为。“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也不过是于物欲而不动于心。如此,才是所谓的自然无为。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的性命之情就在于兴仁行义。与孟子不同,庄子认为,人性自由而自在,人的性命之情就是自然英发、虚静恬淡,就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
社会的束缚、世俗的偏见、个人的虚荣,足以使一个人感到强烈的威压,足以使一个人感到窒息,并从而发出人不如物的感叹。“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而感叹鯈鱼出游的从容。庄子真正羡慕与追求的就是游鱼、野马、大雁的生性。他多么想像游鱼、野马一样地生活啊!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庄子?齐物论》)
庄子多么想成为一个栩栩然的蝴蝶啊!多么想像野马一样狂奔,像蝴蝶一样展翅,像游鱼一样悠然从容!游鱼、野马、蝴蝶的天性就是自由、自在,而又逍遥。庄子对于游鱼、野马、蝴蝶的赞颂,就是对于自由、自在与逍遥的赞颂。《逍遥游》作为《庄子》一书的首篇,所倡导的正是这种人生境界,这才是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在庄子看来,人类的烦恼与不幸并不是自然界造成的,而完全是人类自己铸就的。实际上,庄子把个性的自由与逍遥看得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庄子宁愿贫贱而不肯贵为卿相,其根本原因正在这里。
所以,庄子所倡导、所追求的人格,决不是纯粹的无为,也不是无所好恶、无所追求的自然。自然无为是针对于名利而言的,自然其实并不自然,无为本身即是有为。这种有为,就是不为物欲、名利所动,就是精神的自由、自在与洒脱,就是心性的宁静与淡泊,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就是“胜物而不伤”,就是“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
德国诗人席勒认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在文明社会,物对于人的统治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终日为功名利禄所困扰而不得解脱。人创造了物,本该是要物为人服务,现在人却要为物而奔忙。物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了。并且人自己也成为上足了发条的钟表,只是身不由己地、无休止地、没有思想地做着机械运动。物,不仅成为统治人的东西,并且人本身也成了物件,成了机器和碎片。庄子高举逍遥游的旗帜,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对抗物对于人的统治。
庄子追求的人生境界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既与天地万物相和谐,又不受一切外在物的约束与限制,“物物而不物于物”。以个体精神的自由、自在与洒脱,以个体心性的宁静与淡泊为最高追求,这就是庄子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庄子为人所确立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