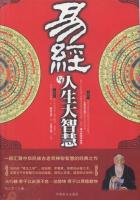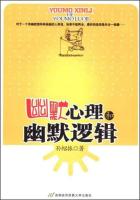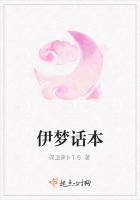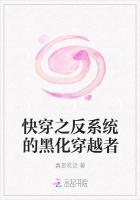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
尧舜的时代不同于桀纣的时代。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所有的人都精神舒畅;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所有的人都很不得志。时势决定着人,时势不同,人的状态也很不相同。所以,人的贵贱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今天的王侯将相,明日可能身陷囹圄。王侯将相的子孙,并不一定还可以成为王侯将相。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为证: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王、谢是南北朝时期最为显赫的大姓、最为显赫的贵族,而王家、谢家曾经养过的鸟,现在竟然飞到寻常百姓家。一只鸟的寿命有多长?这是多么短暂的一个时期,但竟然会发生如此的变化!这就是时,这就是时代的变迁,这就是时代变迁对于人们所产生的影响。
所以,庄子讲:“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常,就是经常,就是恒常。贵者不能常贵,不能永贵;贱者也并非常贱,并非永贱。贵贱沉浮不可以为知。
命的可怕性不在于它发生了,而在于它竟然以这种方式发生了,它如其然地以一种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方式发生了。
西汉文帝时代,有一位著名的大将军周亚夫,他是周勃的儿子。周勃原是汉高祖刘邦的部将,后迁升为太尉,是剿灭吕禄等人叛乱,辅佐文帝登基的第一大功臣。
周亚夫做河内太守时,有相面师给周亚夫相面,说他三年之后将封侯,成为侯爷。封侯八年之后为将相,权重朝野,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成为将相之后九年,将会饿死。
周亚夫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可笑,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周亚夫不是周勃的长子,他有兄长,他的长兄娶文帝之女为妻,世袭了父亲的爵位。即使他的哥哥有一天不在了,那么也会由他哥哥的儿子继承爵位,也不会将爵位传给他。并且,如果他真的继承了爵位,成为将相,权倾朝野,又怎么可能会饿死!
但是事情后来的发展确实就如相面师所讲的。周亚夫的哥哥因为杀人被夺去了爵位。一年之后,文帝挑选周勃之子中最贤者继承爵位,周亚夫时任河内太守,被文帝选中,就这样继承了爵位。
因为周亚夫很会领兵打仗,后来成为车骑将军。景帝即位之后,更迁升为丞相,权重一时。相面师所讲的话,全都应验了。
后来的结果,也正如相面师所预言的。因为周亚夫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在很多事情上与景帝不和,由此而得罪了景帝。景帝就找他的麻烦。如果一个皇帝要找丞相的麻烦,那还不容易?周亚夫借口自己有病,辞去丞相之职。
这之后,有人指控周亚夫谋反。在中国古代,要置人于死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指控其谋反。因为如果谋反罪名成立,那是一定要被杀头的,甚至是要满门抄斩的。
周亚夫被人指控谋反。证据是周亚夫买了很多武器,有图谋不轨的嫌疑。周亚夫说我那些东西根本不是武器,全都是些葬器,也就是说,全是一些木制的兵器,是作为陪葬品用的。廷尉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意思是即使你活着的时候没想谋反,你死后还是想谋反。一个人死后在阴间怎么谋反呢?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周亚夫因此被下了大狱,周亚夫觉得自己非常冤枉。但他不想上告,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有意的,告也没有用,申辩也没有用。周亚夫在狱中绝食,五天之后死于狱中。
相面师所说的一切,全部应验了。当时相面师所说的:三岁而为侯,侯八年而为将相,相九年而饿死。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似乎都是非常偶然的。但是我们想:如果周亚夫不为侯,不为相,那么他就不会得罪景帝。这样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将军,或者只是一名太守。如果这样,他也不至于饿死。但是他成为大将,后来又成为丞相。以他的那种性格,他必然会和景帝发生冲突,必然会得罪景帝,这样景帝自然就要找他的麻烦。如果他向景帝求饶也可以,而他又不是一个会向景帝求饶的人。当然,周亚夫也不会就那样等死。所以,他只有绝食,只有这样饿死在狱中。
饿死在狱中,这实际上是由周亚夫的性格决定的。他本来也可以不这样,但是以周亚夫的个性来讲,当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他必然会那样做事,他必然会得罪景帝,必然会受到指控,必然会选择这样一种做事方式。
这一切似乎是偶然的,但偶然之中又带有必然。事情发展的每一步都顺应着一个逻辑,顺应着一个必然的逻辑。成了将会成为相,成了相以后会怎么样?会下大狱。入狱以后会怎么样?会饿死。这都不是一个人想逃,就可以逃得了的。
庄子对于命的解释,对于命的论述,首先就是承认,人在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是不可逃,也是逃不脱的。
古希腊的哲学中也有这样的思想。古希腊的悲剧最先描写的也是一种命运悲剧。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最有名的悲剧就是《俄狄浦斯王》。
俄狄浦斯是忒拜城的国王,是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儿子。拉伊俄斯得到神谕,说自己的儿子将来会杀父娶母。拉伊俄斯听了以后非常害怕,就把自己新生的儿子两只脚钉在一起,让一位牧羊人把他扔到山里边,让他自生自灭。这个婴儿就是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肿胀的脚。但是这位牧羊人不忍心,就把他送给了另一位牧羊人,后者再把这个婴儿转送给了科林斯的国王。这样,俄狄浦斯成了科林斯国王的儿子。
俄狄浦斯长大以后,有一天到庙里去,传神谕的祭司告诉他,说他将来是要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很害怕,就不敢再回家,离家出走了。在离家出走的道路上,他遇到一群人,因为小事和这群人发生争执,失手打死了人,其中包括一位坐在车上看来很有身份的人。他继续前行,来到一个国家,这就是忒拜城。
忒拜城当时正面临一场灾难,国王前些天出游被人打死了,更可怕的是,城外的山岩上蹲着一个狮身人面的怪兽,这怪兽叫斯芬克斯。它向所有过往的行人提出一道谜语:什么动物早上的时候四条腿,中午的时候两条腿,晚上的时候三条腿?凡是不能回答出来的,斯芬克斯就把他吃了。忒拜城为了解脱困境,宣布谁如果解开了怪兽的谜底,谁就成为忒拜城的新国王,并娶王后为妻。
俄狄浦斯来到城门外,他解开了这个谜语,他说:“这就是人。”人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在地上爬,是四条腿;会走路以后,变成两条腿;年老的时候走不动了,拄着拐杖,又变成三条腿。因为俄狄浦斯解开了怪兽的谜底,这个怪兽就从悬崖上摔下来死了。俄狄浦斯解救了忒拜城的民众,他成为新国王,并娶老国王的遗孀伊俄卡斯忒为妻。
多年以后,忒拜城发生瘟疫。俄狄浦斯追查瘟疫的根源,从神谕那里得到告知,只有找出杀害老国王的凶手,这场灾难才可以免除。后来调查的结果是,杀害老国王的凶手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国王俄狄浦斯本人。是俄狄浦斯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娶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妻。
神的预言果真得到了验证。伊俄卡斯忒得知真相后,上吊身亡。俄狄浦斯更是悲愤欲狂,但他却不能死,因为即使死了,他还会面对被自己杀死的父亲以及做了自己妻子的母亲。俄狄浦斯没有办法,只有戳瞎双眼,将自己永远流放。
这里所表现出的就是命运,就是人在命运面前的一种无力与无助。试想一下:如果老国王拉伊俄斯不相信这一套,那么他就不会遗弃自己的亲生儿子,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出现;如果俄狄浦斯本人不相信这一套,不相信自己怎么可能会杀死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为妻,那么这一切也不会发生。但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在命运面前,总是感到恐惧,总是要逃避、逃脱。但是,这样一种逃避、逃脱,恰恰是一种力量,恰恰是命运发挥作用的一种力量。
3. 安命达德
命运是可怕的,人在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那么,人如何面对命运?人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命运?人是否应当完全听任命运的摆布?
儒家讲知命,道家也讲知命,但所知者有所不同。孔子强调知命,是把它看成一种君子之德。孔子讲“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还讲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知命,知命之有穷,有通,敬畏上帝,不可胡作非为,这是儒家对于命运的态度。知命、畏命所提倡的精神,是“不怨天,不尤人”。但“不怨天,不尤人”,并不就是儒家天命论的根本。
在儒家看来,君子之为君子是担负着道义的,君子把担道行义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而这一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完成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可能有顺境,有顺利,但也可能有逆境,有不利;可能有达,也可能会有穷。那么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君子应当保持一种宽大的胸怀,应当不因身处逆境而改变自己的操守与追求。
所以,孔子讲:“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穷”,并不是说君子本来就穷困,君子天生就穷困,天生就穷命,而是“君子穷亦固”。君子处于穷困的条件下,还能够固守自己的志向,还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还能够坚持自己的追求。孔子赞美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赞美颜回,就是赞美其在困苦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固守自己的志向,始终保持快乐的精神状态。所以,君子固穷,这是一种君子之德。
小人就不同了,小人一旦处在危难的境地,就可能胡作非为,“小人穷斯滥矣”。所以,在孔子看来,“知命”,知命之有通有穷,身处逆境之中而不放弃自己的追求,这是一种君子之德,是君子有德性的表现。
庄子也讲知命。庄子讲知命,是知命之无可奈何,是知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既然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无能为力,那么,人在命运面前应当具有的态度,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就是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来对待一切。
《人间世》篇讲: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