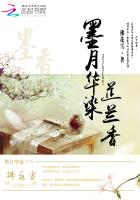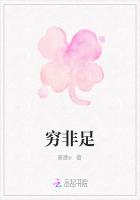“投资发展路径”【以下简称IDP】框架是从折衷范式发展而来的,它将一个国家的净资本流动状况与该国及其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对OLI优势相联系【Dunning,1981和2002】。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O”型特定优势】非常少,同时国内市场狭小,国内资源以自然资源为主【即几乎没有“L”型特定优势】,所以通常很少有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外企也偏好贸易而非投资,这导致净投资头寸接近于零。随着国内市场逐步增长,国家慢慢拥有一些有利的L型特征,开始吸引外来投资。在发展阶段的后期,国内企业将建立竞争优势【即“O”型特定优势】,不但可以在国内某些行业与外资企业抗衡,而且还打入国外市场。国内企业对外进行资本投资以赢得国外市场,因而导致资本的流出。在最后阶段,跨国公司主导跨境交易,原先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活动被跨国公司内部化,促使企业本身变得更加全球化,其国家属性变得更加模糊。
IDP模型将本土企业的“赶超”视为理所当然。该模型舍弃了完美竞争的古典假设【它设想的是一个由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市场】,但是并没有考虑市场结构对本土企业赶超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外国投资对本土资本的影响。由于忽视了这些重要问题,IDP模型在分析本土产业的发展方面就显得非常薄弱。
价值链分析框架
本书以价值链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低收入国家的企业而言,能否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日益取决于能否进入由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Humphrey和Schmitz,2001;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3】。因此,低收入国家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和范围不仅受制于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而且也受制于全球价值链中核心企业的战略决策。这一观点已成为许多价值链研究的中心思想,包括东亚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纺织品和服装贸易【Bonacich等人,1994;Gereffi,1999】,非洲和英国之间的园艺贸易【Dolan和Humphrey,2000】,以及中国和巴西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出口鞋类的贸易【Schmitz和Knorringa,2000】等。价值链分析着眼于全球价值链中企业之间的联系,这种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低收入国家本土企业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方式。
价值链指从产品的设计、采购、生产、配送和营销,一直到售后服务和回收处理等各个阶段所需进行的全部活动。价值链分析侧重于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价值链中企业之间的动态关系。该分析寻求了解企业的竞争策略和竞争优势来源,这些因素不仅决定了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过程,也主导着价值链上各个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传统产业分析【例如,波特的五力分析框架】在本质上往往是静态的,而价值链分析却可以识别协作及竞争企业之间的动态关系。价值链分析“可以揭示不同部门甚至全球范围内生产者之间的经济活动、组织活动和胁迫活动的动态状况”【Kaplinsky和Morris,2000,第2页】。
核心企业的概念
绝大多数的全球价值链通常是由一家或少数几家核心企业【core firm】所主导的。这些核心企业在其价值链中各种商业活动的规划、协调和管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诺兰【2001】认为,在许多商业领域,价值链组织活动的性质已发展成为“全面的规划与协调”。在广泛的行业中,拥有强大技术和营销能力的核心企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产业规划”,在遍布全球的众多供应商中选择能力最强的企业一起合作。这些核心企业通常具有一些关键特征,比如在融资、研发、销售、品牌建设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它们与价值链上游和下游的伙伴一起合作,协调和规划着价值链中的一系列关键商业活动,“大到长期规划,小到对日常生产和运输日程的细致安排”【Nolan,2001,第42页】。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企业之间的界限已然变得模糊。如果以对资产的法律所有权来划分企业边界,核心企业所起到的规划和协调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身的界限。因此,诺兰【2001】首先提出了“外延企业”【external firm】这一概念,用来描述核心企业与受其协调的企业之间的关系。
一个雇用10万~20万员工的主要系统集成商【systems integrator】通过对供应商的规划与协调,很容易就可以有40万~50万以上的全职雇员“为它工作”,这些员工根据核心企业的要求进行着许多价值链中关键性的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说,在这些核心企业周围已然形成了一个由合作伙伴组成的、受其协调的“外延企业”【Nolan和Zhang,2004,第7~8页】。鲁伊格罗克和范·塔尔德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即在每一个现代产业网络的中心都有一家核心企业,充当“产业网络中的一只蜘蛛,在网络的各个参与者之间吐丝织网,编织和管理着它们之间错综复杂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Ruigrok和van Tulder,1995,第65页】。对于价值链的内部结构,以及外部因素对促进价值创造所起的作用,核心企业一般都会有明确的规划。这些规划与设想就像是导航仪,引领着价值链中的各项重要商业活动。不过,核心企业实现这一构想的能力取决于价值链中各公司之间议价能力的分布,因为这决定着核心企业掌控游戏规则的能力【Ruigrok和van Tulder,1995,第66页】。
上述研究均显示,在许多全球价值链中,权力正逐渐向一家或几家企业集中。然而,近期一些有关生产网络的著作却认为,通过网络中的互相协作,企业之间的权力和知识分布更趋于平等。皮奥里和萨贝尔【Piore和Sabel,1984】在对意大利中部和西北部制造型企业的研究中,描述了“灵活的专业化网络”的出现。这些灵活的生产网络基于多用途机器设备、熟练的技术工人和有利于创新的竞争政策。这两位作者预测,这种灵活的生产网络,由于其在应对市场分化方面的优势,将最终取代垂直整合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成为现代化经济生产的主要形式。卡斯特的观点与此相似,他认为网络企业【network enterprises】已经成为信息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这些网络企业并不是基于单家企业或个别企业家,而是由多个不同种类的商业团体所构成【Castells,1996,第173页】。
这里所说的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有别于我们先前所提到的价值链概念。生产网络着眼于一组或几组特定的商业活动,它可能是价值链的一部分。因此,从生产网络关系推导价值链关系的属性时,我们可能漏掉位于网络之外的价值链关系。例如,近期研究发现,电子、纺织、服装和制鞋等行业全球生产体系的垂直分工导致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等低成本生产网络的出现【UNCTAD,2002;Ernst和Luthje,2003】。处于这些生产网络顶部的往往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企业,由这些企业确定产品规格,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产品品牌,供应关键零部件,在高收入国家分销产品。通常正是这少数几家企业???定了生产者之间、生产者和价值链上其他参与者之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模式【Humphrey和Schmitz,2001;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3】。
系统集成的概念
系统集成指的是设计、协调和管理大型复杂系统的能力【Nolan,2001;Hobday等人,2003;Dosi等人,2003;Prencipe,2003;Steinmueller,2003;Nolan和Zhang,2004】。这当中其实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产品和生产流程设计的概念。这里的系统指的是非常复杂的产品,或者是复杂的生产流程。首先必须明白对这个系统的整体要求,然后把这些要求分解到各个子系统和各个零部件。比如说,要设计一架飞机,那么就必须明白市场对这架飞机整体性能的要求,它要飞多远,能坐多少客人,要飞什么样的航线,然后才能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发动机、什么样的电子系统、什么样的航空材料,等等。然后必须设计如何来制造这个产品,需要用什么样的生产流程、什么样的生产设备和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系统集成中的第二个概念是对参与这个系统的各个机构进行协调管理。这里的系统指的就是这个产品的价值链。必须精确地协调系统内各个相关部门之间的互动,使各个子系统和零部件的技术得以发展并得到运用,最终优化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这种管理通常就决定了价值链的结构以及其中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
系统集成的概念最初来自于冷战期间美国的军事计划、采购和生产活动【Sapolsky,2003;Gholz,200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五角大楼面临着随时与苏联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当时双方都在研究和制造最新式的武器,包括喷气式战斗机、直升战斗机、核动力潜艇、巡航导弹、洲际导弹等等。美国军方意识到,要想打赢这场全新的战争,不仅需要大量的技术与研发投资,还必须有一种新的管理体制来协调各种新型军事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在这之前,美国的大型生产性企业都习惯于福特式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从产品的研发、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到组装和产品的分销等大多数的活动都在企业内部进行。现在高科技武器系统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任何一个公司单独设计和生产的能力,它们必须学会更好地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更好地利用价值链中的资源,不仅要管理自己的研发和生产活动,而且要对其他企业的研发和生产活动进行协调和管理。五角大楼是最早推广系统集成这个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美国的军火供应商们能够相互之间进行协调,能有效地研发、设计和生产它所需要的各种高度复杂的武器系统。最终美国赢得了这场军备竞赛,不仅是因为它拥有更为雄厚的资金,而且是因为它拥有更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更有效的研发与生产体系。
到20世纪末,系统集成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大型跨国公司对其价值链的管理。当时大型跨国公司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管理问题。首先是企业规模的迅速膨胀,如何管理好一个拥有上千亿美元资产的巨型公司,防止管理成本的大幅上升,同时又能对市场上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其次,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产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1920年,汽车的组件一共只有1500个;到了2000年,汽车的组件数量发展到了30多万个。1945年,一架飞机总共才有20万个组件;而20世纪末推出的波音777机型一共有350万个组件。1970年,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芯片中只有1000个晶体管;到了2000年,单个芯片中晶体管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亿个。所以,现在设计一套完整的产品系统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资源已经不是从前可以比拟的了。一家公司研究、设计、制造、销售自己的产品,通常需要与多家公司进行合作,这些合作关系也就形成了这个产品的价值链。随着产品的复杂化,价值链中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最后,由于全球各地的市场需求、法律法规以及竞争环境都不完全一样,这就造成了跨国经营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以上这些新的管理问题就促使系统集成作为一种管理创新被广泛地运用。
剑桥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已经在关于全球价值链的一系列研究中给出了系统集成的具体实例【Nolan,2001;Nolan和Zhang,2004;Nolan、Zhang和Liu,2007】。核心企业【或者说系统集成者】与价值链中合作伙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价格关系。在价值链的上游,许多供应商与系统集成者都建立了长期的伙伴关系,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供应商在制定研发规划时会与系统集成者进行紧密磋商。这样,虽然越来越多的研发被外包出去,但价值链中的整体研发方向和进程仍处于系统集成者的严密控制下。其次,为了更好地贴近主要客户,许多一级供应商通常根据系统集成者的厂址规划它们自己的厂址。越来越多的供应商甚至选择将一部分业务活动直接安排在系统集成者内部进行,包括从数据系统的提供到产品制造的一系列活动。最后,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系统集成者会就产品规格、质量和价格对供应商提出严格的要求。同时,供应商就生产与交货时间表与系统集成者进行全面协调,保证所需材料及时到达,把整个价值链中的库存降到最低。
系统集成者与价值链下游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复杂资本密集型产品领域,生产商越来越注重产品的终身保养与维修中所产生的收入。它们在下游的合作伙伴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来监测使用中的机器设备产品,及时向系统集成者反馈信息,从而可以制订最佳的养护和维修计划。在消费品领域,系统集成者会与物流公司一起紧密计划协调系统分销流程,以降低分销成本。这些系统集成者经常会在重要的零售网络派驻它们自己的销售专家,以增加销售网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