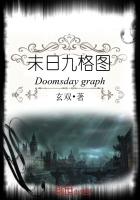回到城内已然掌灯,远远的便看到梅姐姐在店门口东张西望,肩舆停下梅姐姐责骂到:“不是送那姑娘回家吗?怎么这么晚?”又闻到两人一身的酒味,“还喝了酒?两个未出阁的姑娘真是胆大”
辛夷道:“烛心在嵩景的别馆内认了个大哥,一时高兴就都多饮了几杯”
梅儿摇头喟叹,烛心是这性子,到哪里都能攀出三门亲戚,也不忍再责骂她们,伸手去拉昏睡在肩舆上的烛心,熟料这丫头睡熟后竟是死沉,辛夷正想搭把手,鸿烈已经挡在她面前将烛心抱了出来,转头对梅姐姐说:“我先带她回去”又对辛夷道,“你今晚随我们回去暂住一宿,我照顾她终归有些不方便的时候”
虽知道辛夷医术好,梅儿还是多加嘱咐两句,才略放心。远远的看到他们的身影混入人群中,梅儿想到掌灯前宣少爷的来访,究竟真的是顺道来看一下,还是有意而来?他所说的麦田之约又是什么?烛心那丫头平日看起来心性坦然,其实却最是心重。宣少爷身上自有一番商人的精明之气,凡事不会无缘无故为之,鸿烈与这丫头到似一对欢喜冤家,平日里虽多是奚落于她,却在甚微之处显露关切。如今只盼着烛心能有一个好归宿,有一个真心疼惜她的人,她这个做姐姐的才能真正放下心来。
张福将冰镇的梅子汤端出来,正看到梅儿还立在门口,微微一笑走过去轻握一下她的肩膀,两人相望会心一笑。
青石小院内,油绿的柿子果已长成拳头大小,硕果累累压弯了枝头,屋内闷热索性在树下撑了席子,三人露天席地纳凉。烛心酒劲儿正上头,叽里咕噜的说着醉话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以至于鸿烈要不断的将她从席子边缘拉回来,往复多次鸿烈不耐烦了寻了根绳子将两人的手腕绑在了一起。辛夷跪坐在一旁,噙着笑意看着堂堂一国王爷拿这小丫头没办法,这世间种种真是一物降一物。
鸿烈抬眼斜睨一眼辛夷,尽是无奈。
辛夷借机问道:“那日陛下来扣碗店,殿下为何有意躲避?”
他的神色突然变得凝重:“当日,母后日日思念他的时候,他在哪里?”
“所以如今,殿下是在惩罚陛下,让他备尝亲情冷漠之苦?”鸿烈默然不语,眸内已是一片冰冷,辛夷摇头,“当初我也恨过他,毕竟父亲当年出走与他脱不了干系,以至于我母亲忧思成疾致死都未见到父亲”
想到百草叔叔,鸿烈心中一痛:“你父亲客死异乡,你到能对着仇人奉若至亲”
辛夷鼻翼酸涩:“诚如你所说,我尚且都可以谅解他的种种无奈,你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况且他已”想到仁熙帝溃如蝼蚁的身体,她不忍说出实情,“况且他已是悔不当初,你当知晓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
他强撑硬气:“他不是还有两个好儿子吗?我与皇姐已无过多利用价值,他该弃如草芥才对,如今惺惺作态当什么慈父”
她虽知道个中原委因果,却不是说出一切的时候,只是悲痛的凝视着他,说不出话来。他不忍直视她的眼睛,若无其事的在烛心身边躺下,烛心睁开眼睛对着他一笑,咕哝一句:“公子,你许久不来看我了”说完依着他的肩膀昏昏沉沉的睡去
他心中一酸,也沉沉的闭上眼睛,这世间他可追求的只有权势与皇位了,别的再不去多想。
夏夜渐渐静谧,灯烛尽后,萤火点点起舞,萦绕在小院内这般安静祥和。
天微微亮,整个帝都笼罩在一片微蓝的薄雾里。烛心迷迷糊糊的半坐起来想伸个懒腰,忽觉右边的胳膊沉甸甸的,大睁开眼睛看看绑在一起的手腕,又看看睡在一旁的鸿烈,再环视四周,怎么会睡在院子里?思虑着侧身弯下腰盯着鸿烈看了半晌,他的鼻子怎会生的这样秀挺?心念一动,觉得自己现在行为实在猥琐,对着他的小腿就是一脚,鸿烈闷哼一声,睁开眼睛正对上烛心含怒的双眸:“你为什么将我绑起来?”烛心歪着头直视着鸿烈,等着他像往常那样与她争论一番,熟料他只是默默地将绳子解开径直起身,到水缸边舀了水洗漱。烛心挠了挠头,觉得有些下不来台,大声道:“你这个登徒浪子,昨晚对我做了什么?”话音刚落,辛夷端着早饭正好从厨房出来,烛心一下子满脸涨红,辛夷打趣道:“知道脸红了?一个姑娘家一大清早说的什么胡话,不将你绑起来你睡得就不是竹席是石板了”烛心想到自己睡觉的翻腾劲儿,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伸了个懒腰,起身去洗漱。
三人围着石桌吃早饭,说是石桌其实是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周边又放了几块略小的石块当凳子。烛心见鸿烈只是埋头吃饭半晌无话,不禁觉得奇怪,正巧他要夹菜,烛心眼疾手快一筷子夹住他正要夹得那根菜叶,得意的瞅着他。熟料鸿烈只是很淡然的去夹另一边的菜,烛心没来由的一阵气恼连连阻截他的筷子,偏不让你吃,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鸿烈只是抽回筷子将白粥大口喝完,淡淡的说了一句:“我先去店里帮忙”
烛心瞅着他的背影咕哝一句:“抽什么风”
辛夷淡淡一笑,抽的酸醋风
早饭过后,辛夷辞别,烛心背了两筐皮渣送到店里。
鸿烈一整天忙忙碌碌的倒是听话的奇怪,烛心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有时烛心故意找他的茬,他也不像往常那般与她戏谑耍闹,烛心顿觉好没意思,只得将算盘噼里啪啦拨的脆响。
“荷花”
烛心抬起头正对上气喘吁吁的盛呈,唬着一张脸问他:“你叫我什么?”
“额……”盛呈赶忙陪笑作揖,“烛心姐姐”
烛心白了他一眼,慵懒的托起腮:“做什么跑得这般猴急?后边有狼在追你啊”
“倒是没人追我,只是”
不等盛呈把话说完,烛心抢白道:“只是你又嘴馋来蹭饭吧?饭点过了明天再来吧”
盛呈一句囫囵话都没说整急的直冒汗:“哎呀!我的好姐姐,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说罢,低声耳语,“公子病了”
烛心神色一凛:“什么时候的事?请郎中了吗?”
“这还用姐姐说,自然请的是帝都最好的郎中,只是心病难医,几日前有个客商为了讨好公子就送了一幅画,也不知画上画得什么,一向不沾荤腥烈酒的公子,突然醉的不省人事,引得沉疴痼疾又犯了,还吐了血,昏睡了这几日直到现在还没清醒,我听公子梦里喊竹(烛)心,也不知喊得是哪个竹(烛)心,所以想请姐姐去看看公子多加劝慰”经过那次假成亲不知内情的盛呈还以为公子于她有心,所以才会分不清公子的心意
烛心听到公子吐血了,也顾不得再听后话,将账本一扔拉起盛呈就走。
此去经年再入南宫府,她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走近这所深宅大院了,正冥想着,盛呈一把拉住了她恳求道:“好姐姐,咱们还在从后门进去吧,姑姑知道我随便带人进府,肯定会打死我的”
烛心有些生气的瞪了他一眼,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也不忍再为难他。
虽在南宫府做过婢女,却不曾有机会进过内宅,原来公子住的地方是这个样子的,墙角长了一株好大的梧桐树,浓郁的树荫遮蔽了大半个房顶,青砖庭院内没有半点繁花乱草,唯有一小片清幽的竹林奋力的生长着欲与桐树试比高,小时候就常听人说起竹子凌霜傲雨,总是会长过周边的物体,烛心只是觉得好笑还好这里不曾高楼林立,竹子,竹心?公子是否是将这竹子当做了南宫大小姐的化身?盛呈见她呆立着出神儿,连连催促她快进屋,以防让人看见。屋子被屏风隔着外边的小厅陈设简单多是书籍,若不是盛呈说这是公子住的地方,烛心指定当做书房。
绕过屏风,只有一床一矮几,他似乎睡的很痛苦,紧锁着眉头刀刻般的薄唇时不时的微微抽搐几下,呼吸也是时快时慢,脸色十分苍白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烛心急忙上前掏出帕子细细为他擦拭:“那人送来的什么混账画让公子病成这个样子”
盛呈指指矮几上的卷轴画:“就是这副”
烛心道:“打开看看画得什么”
盛呈为难的摇头:“公子的东西,我们向来不敢乱动”
烛心若有所思,支开盛呈让他去给公子熬些清淡的米粥。
在矮几前坐下,刚伸出手又缩了回来,不知在害怕些什么,定了定心神还是将画卷慢慢打开,只是一眼她便觉得自惭形秽,匆匆将画卷合起放回原来的位置,果真是她,定然是连老天都有嫉妒她的美好,所以才让如花美眷过早殇逝。
“竹心,竹心”床榻上的人紧闭着双眸痛苦的喃喃自语
她明白他的意思,却还是忍不住自欺欺人握住他的手温言道:“我在”
他果然安静了很多,不过须臾又痛苦的拧作一团:“竹心,竹心嗟余只影系人间,如何同生不同死”
她的心瞬间沉入谷底,连声将他从噩梦中唤醒:“公子,公子”
宣亦似被惊醒,明眸大睁,异常清醒,见烛心坐在床榻边,瞬间恢复了往日的温和:“你来探望我?”
烛心强颜笑着:“恩”
他虚弱的半坐起来:“店里的生意还好吧?这个时辰该上客了,你该早些回去才是”
或许他是客气,烛心却真的不想再多留一刻,他病了自有南宫府的丫鬟小厮照顾,她在这里也无用,不等宣亦多言,起身告辞,刚踏出半步又退了回来,目光灼灼盯着他的眼睛道:“公子,你多番利用我,我不怪你,只是请你不要再伤害自己,斯人已去,即使念念不忘也不必这样糟践自己的身子”
他的脸色一寒眸中生肃:“你动了画卷?”
若说方才只是劝解,如今见他这样,烛心心里憋得气息不稳,冷冷的道:“公子,这么多年了,你一心记挂在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身上,又何必呢?死了就是死了,尸骨都化成了灰飞,再也不会回来了,且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魂魄轮回”,她说的言辞铮铮最后四个字一字一顿,他眸中的清冷瞬间化为怒火一把抽出床帏上的佩剑,寒光冷冽直指她咽喉,烛心轻轻将利刃推开,轻描淡写道:“认识公子这么久了,有幸观得公子也会生气,实属幸事”
说罢头也不回风也似的离去,刚踏出屋门,脚下一软似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般顺着木门就要瘫下来,刚巧盛呈端着粥进来,眼疾手快单手将她撑住:“姐姐脸色怎么也成了这样子?要不要送你去看郎中”
烛心转过头看着他手里的梅子青釉色瓷碗微微一笑:“好香的米粥”
盛呈叨叨着说:“可不是么,自从公子病了这些日子,厨房里每天都预备着呢”
烛心站起来失魂落魄的向外走去,根本没听到盛呈说些什么,走了好一段才听到他急急的声音:“姐姐,后门,后门”
她转过头,苦笑一声。
念念不忘,他也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的样子,只是自从她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后,南宫老大人就将所有关于她的东西尽数销毁,他夜夜盼她入梦,却始终不见佳人,时间久了他时常因为想不起她的样子而感到惊恐,如今再看到她的画像竟觉得如此陌生,他恼怒自己所以才加以惩戒好让她永远留在他的心里。
夜幕深沉,自扣碗店回到家中鸿烈都对烛心不言不语,烛心心里本就不好受,见他这般冷落于她,气呼呼的不让他睡觉,指使他宵禁之前到城南和城北的粉条店里取回明日要用的原料。劳累了一天,鸿烈面上颇具疲态,却懒得与他辩驳径直出门去。烛心这般无理取闹不过就是想和他痛痛快快的吵一架,出出心里这口怨气,奈何他忍气吞声就是不搭理她。烛心自讨没趣,歪在床榻上迷迷糊糊的闭上了眼睛。
突然有人将门敲得震天响,想是鸿烈将粉条拿回来了,烛心怒道:“敲什么敲,我听到了,你不是武功很好吗?这么矮的墙头都进不来吗?”说着将门拉开,却看到一脸泪水的辛夷,想是来的很急钗环发髻凌乱的不成样子,一进门便急切的问道:“王爷呢?”
烛心呆愣一下:“去背粉条了,先去城南再去城西”
辛夷悲恸微怔喃喃道:“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烛心从未见过辛夷这般慌乱过:“什么来不及了”
辛夷猛地抬头盯着她凝视须臾,一把攥住她的手腕,边向外飞奔边道:“跟我走”
烛心披着被辛夷攥的生疼:“辛夷,你要带我去哪里?大门还没锁上呢”
烛心几乎是脚不沾地被辛夷硬拽着奔至巷口塞上了马车,一声鞭响马车疾驰而起,烛心被颠得东倒西歪,辛夷却驾着车狠命的抽打马背,车轱辘在长街石板上滚滚而过,寂静的夜里似漫天惊雷。烛心突然心跳的厉害,缩在马车内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煌煌帝都,青龙门急急大开,一辆马车飞驰进去,缭乱的影子忽明忽暗,烛心抓紧车壁掀开帘子,眼前的景物虽陌生却极具标志性,这里是——帝宫。烛心镇定下来,扣住辛夷的肩膀问:“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辛夷哭的不能自抑,紧紧咬着的下唇微微渗出血来,马车停下依旧不言语,只是将烛心拉下来,提起裙裾踏着高耸的台阶疾驰而上,工匠们修建这许多台阶本是为显示皇帝的威严,此时辛夷却恨不得插翅飞过去,辛夷脚步飞快,她身后的烛心几乎是连滚带爬颇为狼狈。踏上最后一级台阶,辛夷拽着烛心破门而入,守在门边的婢女着实吓了一跳,见是辛夷才松了口气,将门关好,依旧守着,不时透过门缝像外张望。偌大的宫殿,金碧辉煌,却无一丝让人心暖的感觉,冷冷清清的算上刚才的婢女也不过三人。掩着的盛世腾龙锦帐内突然传出几声有气无力的咳嗽声,然后是沙哑的声音问:“是烈儿吗?烈儿”
辛夷放开烛心,将帐子挽起,轻轻跪在床榻前,忍住哭泣道:“陛下,我没有找到王爷”
烛心周身一僵,陛下?这不是你爹吗?难道辛夷是公主?不对,州国只有一个玉浓公主,他不是辛御医,他是大州国的九五至尊——仁熙帝。他眸内刚刚燃起的清明,瞬间化为灰烬,辛夷胡乱擦一擦掉下的眼泪,一把将呆愣在旁的烛心拉过来:“烛心姑娘也是可信的,她与王爷的情谊,值得陛下将要事相托”
仁熙帝将浑浊的视线移向烛心,烛心颤抖着跪下,他的脸色已近死灰色,气息奄奄,想是大限将至,他闭上眼睛积攒了些许力气颤颤巍巍自怀中拿出一块鱼身玉珏:“好孩子,危难之时将玉珏交予烈儿”
烛心将玉珏接过,不过半月他竟瘦的指若枯骨,想到高阁初遇时他虽清瘦却也是神采奕奕,扣碗小店内他像寻常父亲般殷切的望着自己的孩子,皇家世事纷杂,父子兄弟间的是非恩怨,是无论如何也理不清的。
仁熙帝还欲嘱托些什么,守门的小宫女突然慌张道:“陛下,程相与萧将军带着大批人已至百阶台下”
仁熙帝神色一凛,用尽全力道:“影卫何在?”
烛心一回身,吓了一跳,不知从哪里飞出十几个身着黑衣的侍卫,齐齐跪在殿内个个身背长剑气势凌人,仁熙帝道:“你们十三人拼死也要将她二人送出帝都”
辛夷哭道:“陛下,我不走,我不走,在辛夷心里您不仅是一国之君更是辛夷最敬重的父亲,让辛夷陪着您吧!”
仁熙帝闭上眼睛,轻轻一挥手,上来两人直接将辛夷拖走,烛心看这阵势,急忙示意:不用拖我,我自己走。众人自侧门而出,烛心突然想起那小宫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问道:“你跟我们一起走吧!留下来只有一死了”谁知那小婢女咬着嘴唇眸中带泪道:“姐姐快走吧!”说着一把将烛心推了出去
十三人将烛心与辛夷团团护在中间,来时是辛夷拽着她,离开时却是烛心拖着辛夷。想是现在都忙着逼宫,一路行至朱雀门竟然无人阻拦,只是宫门守卫早已换成萧家军的人,十三影卫与守门的侍卫厮杀成一团,硬是将宫门开启,烛心拉着辛夷趁乱飞奔而出,宫门外早已有人接应,只是烛心看着眼前的高头大马一下子失了神,如若摔下来不死只怕也会摔个骨折,辛亏辛夷已清醒过来:“还不快上马?”
烛心紧闭双眼复又睁开,要么留下来被乱刀砍死,要么从马背上摔下来骨折,想想还是后者生还的希望大,提起裙裾抓紧马鞍手脚并用好容易爬上马背,辛夷这才反应过来她不会骑马,但是如今情势紧迫,两人和骑一骑必定会拖后腿,随拉着烛心的马儿在原地转了一圈,道:“好,快走”
烛心颤颤巍巍道:“这…这就行了”眼见萧家援兵已到。辛夷与十三影卫翻身上马,又在烛心的马儿身上扬鞭一甩,马儿痛嘶一声飞奔而去,烛心吓得夹紧马腹抱着马脖子,转头瞥见身后追兵利器寒光闪闪,也忘了骑马的害怕,勒起缰绳只盼着马儿快些跑。一声哨响,不知从哪里又窜出几股侍卫,此时也顾不得该去哪里,只是哪里没有追兵便逃向哪里,两个影卫护着烛心与辛夷退入另一条长街,却看到不远处火光冲天,厮杀声震天响。烛心一眼瞥见人群中那个熟悉的身影,打马前行大喊一声:“鸿烈”她的声音有些绝望,暗沉沉的黑夜中倍显凄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