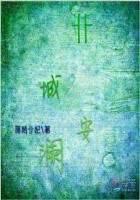清晰如水的钢琴声在透明的玻璃窗上碰落回来,低低萦绕在房间里。我抱着轻松熊公仔懒懒在床上躺着,傅诗言纤长白皙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翩跹如翻飞的蝶。
一曲《绿袖子》奏完,我昏昏欲睡。
“墨宝宝,你说他会不会听得到?”她纵身扑在我床上,胳膊搭在我身上。
“你说谁?”我哼哼了一句。
“又欠揍了是吧,明知故问。”
“方清砚啊?肯定听得到,我记得小时候每次我弹琴他都来敲我家房门,竟然说我像弹棉花——”我翻个身,“放心,像你这种音乐会级别的演奏,不出一分钟他铁定来敲门。”
“你夸我还是损我?”她掐了我一把。
我揉着胳膊,毫不示弱的反击,“我是什么级别,怎么能跟你这个傅家大小姐比,我是说他肯定来听你弹琴。”
可惜的是——五分钟过去——半个小时过去——
门外安静如藏。
傅诗言翻了好大的白眼,阴恻恻的说,“墨宝宝,你忘啦,我跟林古董一起搭电梯上来的。”
重色轻友啊重色轻友,我腹诽了一番。
“我家小砚台的清白啊,绝对不能让林古董那厮给染指——”她垂头丧气。
看着她难得垂着小脑袋含羞草似的可怜样,我于心不忍。
“对了,你怎么没跟你家江小城同学约会去?分手啦?”她瞥我一眼。
我的不忍烟消云散。
“傅诗言同学,怎么说话呢你,你嫉妒了是不,你才分手了呢!”我拿起公仔砸在她身上,“区区一个林古董都对付不了,专拣我这种软柿子捏。”
她眼底幽幽燃起一簇诡异的光,一把握住了我的双肩。
“干嘛——”我被她看得汗毛倒竖,拨拉开她的爪子。
“他不来,但我们可以去啊。”她得意的笑出两个大酒窝。
“注意,是你,不是我们。”我提醒她,懒洋洋倒回床上。
“你是不是我姐妹儿。”她使劲拽我。
“现在我不是。”我一头扎进枕头里,“我很累很困,容我先睡会。”
暑假过了大半,江城打了好几份工,那天下班时赶上一场雨,我不幸感冒了索性在家呆了几天。其间有同学聚会,答谢亲戚朋友的宴席。一遭下来病好了,但整个人脱了大半的力。
“你不去是吧,那我就告诉干妈你跟江小城同学的甜蜜二三事——”
我腾地爬起捂住她的嘴,心虚的看了看门外,压低声音哀求,“行了,我去还不行。”
她志得意满,我在她身后指手画脚。
方清砚开门时,衣冠楚楚,形象尚好。
他见我们来,神色淡淡的将我们让进门里。我在傅诗言身后朝他使眼色,方清砚,你可千万别把怨气施在我身上,我没想搅你好事的。
傅诗言羞答答一句清砚,我愁肠百结。
方清砚哆嗦了下。我暗暗掐了傅诗言一把,话说,大姐你别成了傅古董。
客厅里悠扬响起《魂断蓝桥》的经典插曲,我看着黑白的屏幕,暗暗摇头。林古董就是林古董,品味不是我们这种整日泡在宫斗韩剧日剧美剧的小清新能比的了的。
林亦然侧坐在沙发上,我只看见她一身水仙花似的衣裙。方清砚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清砚,纸巾在哪儿,这个用完了——”抽噎的哭腔,百般娇弱。
我肠子拧成一股,胃里冒酸水。傅诗言看我一眼,我意味深长的眨了眨眼。
看吧,这才是高级别的,你就别东施效颦了。
“我去拿。”方清砚趿拉着人字拖往卫生间走。
林亦然泪眼朦胧看了我们一眼,继续沉浸在悲伤的剧情里。
四个人诡异围在电视前,玛拉与从战场归来的罗伊相遇,费雯.丽一刹那的表情动人。
傅诗言极洒脱的盘腿坐在沙发上,捏着方清砚的军事杂志看的不亦乐乎。方清砚从卧室抱出一大摞放在她手边。
她侧过脸不时问方清砚,两只脑袋挨得极近。我百无聊赖的看着他俩,果然是一对璧人。
傅诗言朝我抛个得意的眉眼,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林亦然窝在沙发里,梨花带雨。
我无奈抱着面前那盆草莓狂吃。方清砚冷冷看我一眼,我看看林亦然,吃的更欢。
老妈的大嗓门隔着门板清晰可辨,“白墨宝,有你电话。”
我迅速撤退,从老妈手里接过手机。
江小城三个字煞是惹眼,我心虚的看了眼回厨房做饭的老妈,躲进卧室里接听。
“请问,是白墨宝女士么——”听筒里是很好听的女声。
我磕磕绊绊的说,“我是。请问——”
“是这样,江城是你的朋友么,他现在在医院里,你能不能——”
脑子一片空白,我匆匆问清了医院和病房,抓起钱包跟老妈打了声招呼就往外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