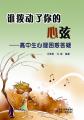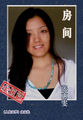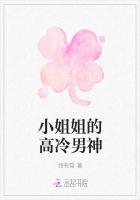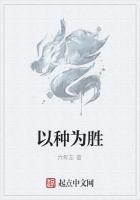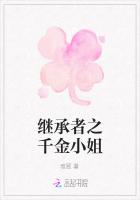社会的残酷与温暖
社会是具体的,家庭、学校、企业、NGO(非政府组织)、政府、教会,当人们哪一样都靠不着时,就会选择极端举动。当他们被结结实实地抛到那个看不见的府层时,亟须一只拉他们一把的温暖的手。
盛世宏景与乱世怪相并存,这就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奥运与世博并举,天灾与人祸齐至。六十周年大庆之后,社会如股市进入下行震荡期一般,发生了云贵百年大旱、玉树地震和一系列触及道德底线的惨案。
学者提醒,中国的犯罪率进入高发期,谋杀、抢劫、强奸等重罪频现媒体。近年来,人们谈论最多的,不是世博盛事,而是校园“七连杀”和富士康“九连跳”。愤怒者谴责惨案肇事者无良知,冷静者在反省这些惨案背后的社会致因。
中国已进入经济起飞期。按发展经济学相关定律,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 000美元之后,社会随即有堕入动荡的危险,收入不均、环境污染、道德崩溃使社会敏感神经绷紧。
但是,经济学定律不能成为我们敷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借口与托辞。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社会学家所谓的“循环剥夺感时期”,简单讲就是人人都觉得自己亏了。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微博上称:“当今的中国,似乎人人都受伤,都被剥夺,自感为失败者。官员很失败,企业家很失败,文人很失败,学生很失败,工人、农民很失败,体育、娱乐明星很失败。如果重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充满了失败感的盛世。”
一个整合的现代社会,应该是国家有目标,社会有共识,个人有希望,而且这三个指标前还要加上“长远”俩字。中国的问题是只及当下,不顾长远。其要害在于失去了社会共识—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改革开放成功的基础。
30多年前17岁的牟其中、杨小凯在不同地方写了同题文章《中国将向哪里去》,此二人如今一个锒铛入狱,一个早逝。新的世代娱乐精神足够,历史感欠缺,他们历史感、沉重感不具,再不会写这类文章了。但问题还是在那里:中国将向哪里去?
请关注那个看不见的底层
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突破4亿。据公布的数据显示,86%的中国网民活跃于在线下载音乐,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55%;64%的中国网民积极参与社区聊天和撰写博客,而美国网民对应的比例仅为36%。中国人缺乏物理世界的娱乐方式和发言渠道是不争的事实。
更应关注的,是那个看不见的底层。他们没有娱乐,没有工作,亲朋好友离他们而去,他们也没有微博这种虚拟的社会链接。家庭社区是初级群体,而底层民众既没有来自初级群体的温暖,更缺乏企业和单位等次级群体提供的保障。面对一个残酷的社会,他们只有选择铤而走险。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在他的《自杀论》中谈道,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富士康“九连跳”是自杀,校园凶杀案本质上也是一种自杀行为,只是自杀者要多拉几个“垫背的”而已。施暴者只感受到社会的残酷,没有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中国逐渐进入一个原子化社会,一个道德失范、失去整合的社会。当今中国,可以表述为个人原子化,利益碎片化,人际关系干燥化,一擦就出火。按涂尔干的概念,这就是社会整合度低下。
我们在富士康“九连跳”惨案中,看到第二代民工对娱乐和交流的渴望。自杀者直到跳楼之前,同宿舍者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一个企业是需要亚文化的,而富士康只有计件流程。可以想象第二代民工离开温暖的初级群体后进入冰冷的流水线工厂那种孤单的境地。
我们在校园“七连杀”凶杀案中看到,肇事者将无法排遣的愤懑直接发泄到更弱的弱者身上。社会忙于亡羊补牢式的大规模防范动员,却不去面对那些潜在的“凶犯”正处于何等孤苦无援的“原子化”境地。他们无法将内心的需求与利益的需求向强者诉说,只有选择攻击社会最柔软的部分。
2010年,浙江台州3名90后网上相约自杀的事件,更昭示了年轻一代看不见的底层正在生成。如果年轻生命不被社会尊重,农二代被排斥在城外,再辉煌的城市化成绩单都会大打折扣。
社会在哪里?社会是具体的,家庭、学校、企业、NGO、政府、教会,当人们哪一样都够不着时,就会选择极端举动。当他们被结结实实地抛到那个看不见的底层时,亟须一只拉他们一把的温暖的手,或许,在他们感受到温暖之后,惨剧就不会发生了。
请将微博焦虑症转化为实际公益行
从玉树地震到国祭日,网上着实演绎了一次公民的公益行。新浪微博上的抱怨忽然停止,社会忽然宽容,骂骂咧咧烟消云散。屏幕上流溢着久违的温暖之情。这种温暖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似曾相识。
但过不了几日,一切照旧。灾难成了消解社会怨恨的解药。但你不能期望灾难频仍。博友将多难兴邦改为“兴邦,多难!”一语中的。
《中国青年报》曾刊文:“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焦虑?”网民回帖:中国少数人垄断资源,多数人为剩余的一点儿资源争夺,大家能不急吗?低收入阶层完全没有保障,养老、医疗、子女教育都没有保障,如何能不焦虑?于是只有金钱才能给人一点儿依靠。但货币也在不断贬值,所有有点儿小钱的中产和白领,依然焦虑。
中国已达4亿规模的网民可大致分裂成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天真快乐的追星粉丝群和焦虑纠结的忧国忧民群。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开开心心在开心,冷嘲热讽在微博,愤愤不平在天涯。抱怨是一种毒药,会毒化人们的心情;但不抱怨出来会更毒,导致社会机体溃烂。
我们面对着一个说谎社会。官员GDP考核致使统计数字造假,造就国民经济虚假繁荣;房地产新政致使假离婚盛行,造就社会大面积说谎;学术评职称致使教授沦为文章计件工,造就学界大面积论文造假;小学生作文致使孩子们胡编英雄事迹,造就社会新一代说谎者……
互联网批量生产乐观主义并不断被复制转发,也可以批量生产悲观主义并不断被复制转发。互联网批量转发的无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微博焦虑症的根源是社会焦虑。据观察,网上有两类狂转帖:一类是励志格言,表明人们在焦虑个人成功;另一类是忧国帖,表明人们在焦虑国家(调侃或恶搞只是焦虑的另一种形式)。如果你既焦虑个人成功又焦虑国家,那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你需要一个坚强的神经。
现实就摆在那里。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是从焦虑开始,但又不止于焦虑,还需要行动。请将微博焦虑症转化为实际公益行。
不要让悲观主义击垮我们乐观的天性
当一个机体出现病症时,生物体会自发做出调整。微博是一种自发的拯救行为,正如义工、NGO等是一种自发的拯救行为,社区公益国学班也是一种自发的拯救行为。当权者要明白,一个社会失去了认同感和自组织能力,政权就失去了基础。到那时,一个小小事端就会擦枪走火,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净空法师倡导“和谐拯救危机”,但拯救世界前先要拯救心灵,中国人的心灵。
当前,“裸体加尸体、绯闻加丑闻”式的传媒报道,对系列校园凶杀案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或至少是传染作用。广州某家报纸报道,清远市一名老奶奶接其就读一年级的孙子时,神经质地携带刀具,并曾持刀在校门口挥舞。有关宣传部门要求传媒少报道校园凶杀案,以免病态普遍传染。传媒应讲社会责任,而政府对人民的信托责任更应该大讲特讲。两者孰轻孰重?
《读者》杂志自1981年创刊,始终秉持“中国人的心灵读本”的理念。在美国,《读者文摘》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中国的《读者文摘》正是充当了软性宗教读本的功能。但中国人光有《读者》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揭露真相的锐利媒体,这样世道良心才不会死。
姚晨被誉为“微博女王”,她是快乐因子,她心态阳光,并不犬儒,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微博的焦虑气氛;她乐呵呵的人生态度与禅宗理念是一致的,即爱这生活、爱这时刻、爱这人。那些不能像她那般快乐的人,也多少被其乐观心态所感染。当今世道之下,我们需要更多姚晨那样的感染者。
潘石屹,地产老板,却将微博当作布道的平台。老潘的老板身份并不掩其公益之心。无论传播善良的理念,或付诸捐款善行,他都是一个高调的人。中国需要更多这样高调的人,这并不是作秀。
乐观主义是稀缺的,乐观不是盲目乐观,需要一种境界;悲观主义也是稀缺的,悲观让这个社会保持警醒,审慎的悲观使这个社会免疫,只是不要让悲观主义击垮我们乐观的天性。
面对社会的残酷,保持人性的温暖,拿出每一个人的勇气与责任。4亿网民已非小数,4亿可以辐射13亿。哪怕一条微博、一条短信,传递善意或警醒世人,都多少有益族群团结。中国人太需要团结了。
当然,我们明白,发微博代替不了实际变革。社会要持续向善须进行伤筋动骨的变革,最终,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将重新获得平衡,社会重新获得意见制衡基础之上的认同。
谁把你逼得不耐烦
在当今世界,每天都是国际投胎日。中国的疯狂速度更比全球快一拍,风风火火,争先恐后,海归同学回国一看,嚯!好一派鸡飞狗跳的景象,我熟悉的祖国又回来啦!
中国人争先恐后的场景可以演化出不同场景来,比如周末打不到车叫国际打的日,世博会排不上队叫国际SB日,世界杯看朝鲜队比赛叫痛骂国足日……反正不耐烦是我们的常态。
当下的浮躁无须再费笔墨。我想说的是,这种浮躁无可指责。都是穷忙族,都是忙生活,都是“老赶”,有啥好指责的。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忙中有劲,忙得出结果,30年之后开始穷忙,忙不出个结果,且忙得没尊严了。所以不耐烦成为基本社会心态,无可指责。
在“奴时代”,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根鞭子
“王老吉凉茶”热销、绿豆断货,今天的中国人易上火,不独股市暴跌、房价暴涨,社会不断撮火的地方还有许多。
中国人急急忙忙“去投胎”,脚踩风火轮,打造了中国速度。但中国人并不享受这种状态。因为被迫,因为这是“奴时代”:房奴、卡奴、孩奴、媒奴及其他什么奴。
愿意当房奴是某种担当,否则你都不好意思上《非诚勿扰》。而孩奴即一辈子替孩子打工不求回报者,则似乎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父母一辈包括贪官在内,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下一代争得一番好天地。媒奴是那些急于跟上时代的人,每天被迫接受资讯,就担心被边缘化,被时代淘汰。
在“奴时代”,不为“奴”你就更无尊严可言。比如没有“丈母娘需求”,你就连媳妇也娶不上,某一天回顾“成功的一生”,发现是“丈母娘需求”造就了你。
在“奴时代”,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根鞭子。不耐烦或急功近利是体制造成的,白领和中产成功学背后是辛酸和无奈。即便是那些体制的受益者—权贵阶层,头上也悬着一根鞭子,否则就不会纷纷把自己或子女弄到海外去了。
“奴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没安全感是因为社会缺乏规矩。我惊叹于日本和香港车流之速,道路不比国内城市的宽,但车速极快,就因为有规矩。该慢的时候就慢,在西方城市的道路上从来都是车让人,有时礼让得你都有点不好意思。在中国你要是礼让,假如没有红绿灯,大概半个钟头都过不去。无规矩融入中国人的基因,香港近年红绿灯乱相,据说是大陆人去得多了。
在“奴时代”,政策可以朝三暮四,房价政策高举轻放,股市政策浑水摸鱼。无论房市股市,在中国永远只能做短线,所以中国永远诞生不了巴菲特。
在“奴时代”,股市最撮火。有人将佛戒引入炒股。佛家称烦恼由贪瞋痴而来,是我执在作怪。炒股大忌是贪,老想一买就赚大钱;是疑,疑心太重,涨了老觉得要跌就卖出……佛戒是救不了中国股民的。
所谓成功人士,即在无规矩中浑水摸鱼和火中取栗者,抑或是善用潜规则的受益者。
《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超七成人认为单靠踏实工作难致富,89.1%的人表示身边年轻人想做“炒钱族”—一个新词诞生了。“少壮不炒股,老大徒伤悲”,炒股、炒房、炒期货、买彩票,神州无处不炒作。
年轻世代沦为“炒钱族”实为现实所迫。如果大头都被权贵集团拿走了,那么多数人抢那一点儿残羹剩饭,只有抱侥幸去炒钱,所以着急,所以“王老吉凉茶”热销。
中国经济在30年高增长之后出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枯竭,社会未富先懒,好日子过完了,开始尝到苦日子的滋味了。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民众对权贵的制约,将成为经济下一步增长的关键所在。
不耐烦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
在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不耐烦仍将是中国社会常态。“王老吉凉茶”仍将好卖。
众所周知,中国民航永远延误。在欧洲机场常见的一景是有人手捧小说阅读,在中国候机厅中鲜见读书者。候机是一种期待,这种期待有时成绝望。一位朋友在上海机场苦等6个多小时才上机,大家才舒一口气,只听一位旅客曝出:“现在半夜两点了,我要回去睡觉!”机务人员鼓动大家说服这位“刺头”,因为只要一人喊着下机,所有人都要下来,所有行李都得卸下来重过安检。最后,该“刺头”终于在众人的声讨中作罢。
中国民航是体制坚固的垄断堡垒之一,屡屡亏损,屡屡腐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原总经理落马,该处级干部在上海购有4处房产,房款多来自“小金库”—审计署公告披露,东航的“小金库”资金充裕得很,而东航前年巨亏140亿!
可怜那些空姐为不合理的航空管理体制承受着顾客不耐烦的口水,她们娇嫩的脸蛋承载着体制的屈辱。因航机晚点对空姐抱怨时,你当怀有怜悯之心。同样的情况出现在银行,银行职员为不合理体制承受顾客不耐烦的抱怨。中国银行可能是全球银行里排队时间最长的,中国银行可能是全球银行里手续最为烦琐的,但中国银行也是腐败案和呆账率最高的银行之一。这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银行职员和顾客要承担腐败成本。银行职员可能忙得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顾客还是骂,因为体制是看不见的,他们是看得见的。
怜悯也好,佛戒也好,并不能帮中国人消除不耐烦的根源。我以为,不耐烦时间长了就会积聚变革的力量,不耐烦正是社会进化的开始。
史上中国农民揭竿而起,都因连年灾害后,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但凡尚存一点儿生活希望,中国人民都不会反的。这便养成了自秦以来2 000年中国人的忍功。鲁迅先生才决定用笔来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
与中国相反,号称绅士的英国人倒是一个潜在的不耐烦者。孟德斯鸠曾写道,英国的气候孕育了英国人暴躁的性格。英国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口号叫“没有面包,便要流血”。英国是权力制衡理论的发源地和实践地。我们曾看不惯人家议会的吵架。议会的吵架是为了社会上不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