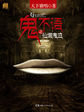清晨,艾美丽像往常一样出去晨练,拉开大门,见一个男人正扒在对面的门上,使劲儿朝门镜里张望。
她站在自家门里看着,见男人十分投入,完全没有发现身后的自己。于是,艾美丽故意弄出些响动,“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住。
男人回过身,是个帅气的小伙。
“你找谁?”艾美丽忍不住先开了口。
“有个叫余蓓蓓的女孩是住这儿吗?”帅小伙和颜悦色地问。
艾美丽警惕地盯住他:“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朋友,从四川来的,顺便看看她。看来,她就住这儿了。知道她去哪里了吗?”帅小伙又回头朝门镜望了一眼。
“她不在,走了几天了,你是她朋友?你没跟她电话联系吗?”艾美丽想要搞清楚这个人的来历。
“大妈,蓓蓓她是几号走的?还能记得吗?”帅小伙露出一脸焦虑。
“嗯,好像是26日晚上……反正,第二天早上一开门我才发现她已经走了。”艾美丽说出话又有些后悔,她本想从对方口里问出点儿什么,不料想反倒是自己说出了当天的实情,这人老了真是不中用了。
“哦,你是说,你27日早上知道她走了,实际上,她在26日晚上就走了?”
“你到底是她什么人呀?”艾美丽突然不耐烦起来,她害怕自己再说漏了嘴。
“我是蓓蓓的好朋友。大妈你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吗?是跟别人一起走的吗?”
“不知道。”艾美丽想起那个女警察特意叮嘱过,案子还没有搞清,不要随便跟其他人说。“要不,你留下名字和电话,等余姑娘回来我让她跟你联系。”
这时帅小伙的手机响起,他向艾美丽摆了摆手,接听电话,“喂……是樊总……好的……”
艾美丽站在他身后,一副疑惑的神情。
帅小伙边听电话边走下楼去。
见他下楼了,艾美丽急忙开了自家大门,跑到窗口朝下望。只见帅小伙走进一辆白色的轿车,她匆忙找出一张废报纸,在上面记下了车号,忽地想起没看清是什么牌子的轿车,又走到窗前朝楼下张望,早已是车去院空了。于是她急忙从抽屉里找到写有霍妍电话的纸片,拿出小灵通开始拨号……
霍妍急匆匆地赶来了。“大妈,什么人来找余蓓蓓?”
“一个帅小伙来找余姑娘,说是她的好朋友,还说是从四川来的,顺便看看她……”艾美丽突然想起什么,“那老家伙抓住了吗?”一副急切的样子。
“没有。”霍妍冷静地说,“还需要你的帮助。那个帅小伙还问了什么?”
“他问余姑娘什么时候走的,我说大概是26日晚上,我是27日早上才知道的。他还问余姑娘到什么地方去了?是跟别人一起走的吗?”艾美丽回想着,“哦,对了,他叫她蓓蓓,看样子挺亲热的。说是从四川来的,哎呀,还说是蓓蓓的好朋友,没准是男朋友?”艾美丽这时不断在心里谴责自己,怎么这么不中用,应该问一句是不是男朋友。
“帅小伙,管她叫蓓蓓?好朋友?”霍妍边重复边思考着,“是从四川来的……这么说……”
“是呀。我猜想,没准是余姑娘的男朋友。”艾美丽一副认真的表情。
霍妍心里纠结,她原本想到的是余蓓蓓也许回四川去了。
“那帅小伙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样子?”
“有二十五六岁吧,长得像电影明星,可帅了。”
“像电影明星?像哪个明星?”
“演什么电影的?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可帅了。我说,那老家伙抓住了吗?”艾美丽似乎对那老家伙耿耿于怀。要是这小伙真的是余姑娘的男朋友,那岂不是……
霍妍说:“大妈,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请您放心,谢谢您的支持。不过,关于那天晚上的经过,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说出这句话,霍妍有些犹豫,她担心艾美丽的证词有出入,倒不是怀疑她故意做伪证,而是证人的证词往往随着自己的想象而出现偏差。因为现场勘察的情况与艾美丽的陈述之间的确存在矛盾,这让她内心纠结着。
那个清纯的女孩,最近,霍妍脑海里不时浮现出四年前那个女孩的身影,她姓金。她真的会是这起案件里的余蓓蓓吗?她为什么要冒用别人的名字?她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两个女孩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可是,这个女孩究竟是谁?她现在是生还是死?她和汤新生之间,一对年龄相差甚远的男女,是什么让他们腻在一起?她,似乎是那种超时尚的女孩,因为金钱?因为那个几乎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有车,也很富有?……无论如何,从现场证据看,不像发生了严重的凶杀,倒像是一场猎艳的游戏。霍妍从内心里是多么希望这个余蓓蓓不是她曾经见过的那个姓金的清纯女孩。
“怎么?还有什么问题?”艾美丽并没有明白霍妍的意思,可是她一双眼睛里闪着极度的认真。
霍妍歉意一笑,说:“是这样,有些情况需要再核实一下,请把您看到的情况再说一遍。”
“是那天晚上吗?从那老头来的时候说起?”艾美丽边说边陷入回忆之中。
“那天晚上,你是怎么看见那老头走进对面房子的?”霍妍耐心地等待着。
“那天晚上,天蒙蒙黑,我看见那老头走进余姑娘家。后来就听见‘砰砰’的玻璃杯摔在地上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尖叫声……搞得我一夜睡不踏实。”艾美丽重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别急,那老头走进对门时,你还看见余蓓蓓在门里给他开门了?”霍妍似乎觉得艾美丽的陈述比第一次听到时更为情感化,似乎添加了渲染和想象的因素。
“我看见了,余姑娘站在门里。”
“她穿的什么衣服?还记得吗?”
“粉红色的睡衣。”
现场的确有一件粉红色的真丝睡衣。
“您刚才说,那天晚上,天蒙蒙黑,您能看清那女孩穿的衣服是粉红色的?”霍妍轻声细语,为的是不打乱艾美丽的思路。
“楼道里有些黑,可是余姑娘家里开着灯,她身后有光,是粉红色的,很好看的。”
“看清睡衣是什么料子的了吗?”
“那就看不清了。好像是很光亮的,看上去有些富贵。”
“还有一点,您说听见‘砰砰’的玻璃杯摔在地上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尖叫声……可是,我们询问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他们都没人听到动静。”霍妍正是对此存有疑虑。
“怎么可能?”艾美丽像受了委屈。
“您再好好想想。”霍妍严肃起来。
“嗯……你们一定是问了一楼的陈妈吧?”
“是的。”
“陈妈八十多岁了,比我大十多岁,耳朵不好使,每天晚上早早就睡了,她邻居的房子租出去了,人家当库房,没有人住。二楼就是我了。再往上的三楼住的都是年轻人,没准儿,他们看电视,听不到。”艾美丽扳着指头边想边说。
她说得也有道理。在地板上摔东西的声音,应该是楼下听得最清楚,可楼下的陈妈大概听不到。
霍妍想到了细节,问:“大妈,你当时听到了几次声音?每一次声音大概是什么时候,是怎样响的?”
“他来的时候,天蒙蒙黑,我记得是他进去后很长时间,听到‘砰’的一声,又过了好一阵,大概是八九点,听到女人的声音,声音还挺大,是喊的声音,‘啊’……好像是在喊救命。”艾美丽张圆了嘴模仿着喊了一声。
这时窗外传来一声鸣笛声,霍妍注意到白天在房间里能听到室外的嘈杂声,能听到街上来往的车流声。晚上八点左右,应该是电视节目黄金时段,三楼住的年轻人,如果专注于电视,有可能听不见楼下的声音。但是,霍妍又想到了新的问题:
“你平时几点睡觉?”
“一般不到10点就上床了,躺在床上听广播,也睡不着。”
“那天晚上有一辆汽车停在单元门外,你知道吗?”
“没注意。”
“你常趴在窗户上向外看吗?”
“白天天气好了就在楼下坐坐,到外面走走。天气不好时,下雨了,只能趴在窗户上向外看,要不我一个人也没事做。”
“除了那老头,还有什么人找过她?”
“还有刚才那个帅小伙,再没见过什么人。”
“你再想想,或者有人在外面叫她。”霍妍扫视着室内,墙上斑驳的涂料像抽象画似的恣意延伸,这间房子跟她一样老态。
“……她刚搬来不久,我想起来了,有个男人来过。”艾美丽声音里有几分神秘,“有个男人四十多岁,中等个子,人很壮实,脸上有横肉。站在楼下朝余姑娘家窗户上看,还打着手机,那是夏天,我们几个老太太在楼下坐着乘凉,只见那男人看了一阵,大概发现我们看他,就走了,看样子不是好人,这儿常有小偷什么的。”
“你喜欢余姑娘?”霍研想到艾美丽对这个邻居似乎特别关心。
“余姑娘不但人长得让人心疼,还心地善良。”艾美丽接着说,“有一次我买了一袋面,提得太累,就在街道口休息,那女孩走过来说要帮我,不顾我的阻拦,一把提起面袋就走。现在的女孩在公交上都不让座,还跟你抢位子呢。”艾美丽说话时脸上浮起幸福感。
“看来真是个不错的女孩!”霍妍自然联想起那个玉石店里的女孩。再看眼前这位大妈,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尽管眼皮松弛了,却还能想象出她年轻时的美丽,“你年轻时很漂亮也很勾人吧?”霍妍笑着开了一句玩笑。
“唉!女人美了是祸不是福。”艾美丽两眼发直,似乎想起往事。多年以前的经历,如同压在箱底的一件旧衣服,重新取出来时,往事历历在目,她满眼的忧伤和哀怨。
霍妍伸手拉住了老人的手,一双冰凉而布满老趼的手,说:“我说的话让你伤心了。”停了一会儿,又说,“说出来也许好受些。”
“姑娘,别笑话我,我同情余姑娘,因为我就被人欺负过,年轻时不懂事啊。”艾美丽两眼发红。
“能跟我讲讲吗?”霍妍希望了解证人心理,包括她的经历,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判断证词的可靠性。
“我家里穷,出来给人当保姆。那是个军代表,他老婆常年在病床上,那时我才十八岁……”一行老泪从艾美丽眼中涌出。
“后来呢?”
艾美丽叹了口气:“唉——我怀孕了,被他赶出来了,我没脸见人呀,跑到城河边,我想跳下去,被一个捡破烂的老婆婆救了。后来,我就住在城墙边的破木屋里,我们相依为命,1970年改造旧房,我才分到这里。”
“老婆婆呢?”
“老婆婆还算有福气,住了一年新房就走了,她比我亲妈还亲。”艾美丽说那天晚上,听到邻居家“砰”的一声,她就想起曾经被那个军代表和她老婆赶出家门时,砸碎的他家几个碗发出的“砰、砰、砰”的声音……
看着艾美丽,霍妍想到了心理学上所说的这种感觉,是一种心理定势。在案件当事人中,特别是在证人心理中,这种心理定势,可能导致很大的误差。
走出艾美丽家,霍研似乎也听到“砰、砰”的破碎声,那是心的悸动。一个青春期遭受如此凌辱的女人,恐惧的阴影会伴随她的终生,令她时常噩梦再现。也许,听到一点儿动静,便会产生联想或者产生夸大式的想象。也许,这就是证人艾美丽的心理定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