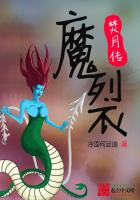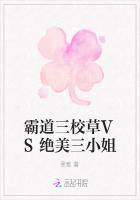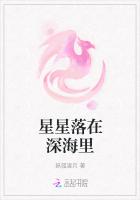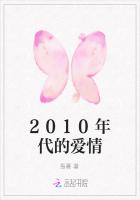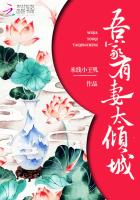另一方面,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文化研究近年兴起于欧美学界,席卷了各个学科,以至于詹姆逊不得不称之为“超级学科”。大学人文学科的传统分类界线正在被打破,文学系、比较文学系、历史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传播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系,都被卷人文化研究的圈子。传统学科的分界标准正面临解体,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也正在消除壁垒。文化研究的盛行得力于后结构主义理论被广泛接受,在后结构主义体系内(假定它有体系,并且有疆界和内在分别的话),各个学说之间并不能相互兼容,它们确实有某种共同性,但不能通约。在德里达和福柯之间,在福柯与拉康之间,在巴特与德留兹之间,分歧有时大得惊人。但在后结构主义之后,人们可以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巴特的符号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拉康或德留兹的后精神分析学,以及“新左派”或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女权主义……由此鼓捣出后结构主义盛宴,这就是文化研究的杰作。在把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全面挥霍殆尽的同时,文化研究就从后结构主义里面死而复生--于是,文化研究就作为“后一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超级学科获取长生不老的动能。文化研究是理论过剩和超载的产物,观念和知识终于全面战胜和压垮感觉、领悟和判断的传统学术方法。文化研究这个起源于传统文学学科的超级学科,它是文学研究的新生、哗变,还是自我颠覆?或者说,就像所罗门瓶子放出的妖孽,已经完全失控了?
在美国,70至80年代被称之为批评的黄金时代,传统的文学刊物突然让位于文学批评。这是文学创作枯竭的时代,文学刊物不再对文学作品感兴趣,而是充斥着新派的文学批评。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那里获得法宝的“耶鲁四君子”,把美国的文学批评推到极致,德曼的细致精当,米勒的挥洒自如,哈特曼的酣畅淋漓,布鲁姆的奇崛绚丽,这些都使文学批评变得花样翻新,魅力四射。没有青年学生不受到蛊惑而顶礼膜拜。这一时期的批评家四处开花,一边在美国那些资金雄厚的大学讲坛上踱着方步侃侃而谈,一边在那些主流刊物上潇洒作文。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赛依德也是虎虎有生气,一方面是美国大学的知名教授,另一边当着巴勒斯坦的议员。只有他才敢于声援拉什迪(1988),并对“奥斯陆原则宣言”(1993)大加抨击。80年代的赛依德真是风光,他的思想方法明显来自福柯,也从德里达那里吸取养料,虽然他始终对德里达颇有微辞。大量的左派人文学者,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大学呼风唤雨,他们热辣辣的文风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现实与历史大打出手,这使他们的知识运作,经常超出文学批评的范围。左派的文学批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区区文学(的审美品质)怎么能容得下颠覆资本主义、挖出帝国主义老底的壮志雄心?文学批评加上了左派的政治发动机,它必然要向“文化”(这是谦词)领域挺进。只有文化,这个漫无边际的空间,这个超级的领域,这个巨大的无,才能成为美国校园政治名正言顺延伸的舞台。文学批评之所以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七八十年代走红,实在是左派激进主义运动的改头换面。在80年代新保守主义当政的年月,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在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茫茫黑夜里”--左派拿什么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呢?拿什么来打发失败的光阴呢?再也没有什么比激扬文字,用花样翻新、随心所欲的文学文化批评来指点江山更能保持体面。在那该死的冰冷的冷战时期,古拉格群岛,就是萨特这样的铁嘴钢牙当年也有口难辩,更何况80年代温文尔雅的左倾教授呢?还是搞搞文学批评,从这里打开资本主义的缺口。想不到这个缺口向文化研究延伸,使得资本主义的人文学科异常火爆,大学课堂上高朋满座,都是未来资本主义的栋梁之材CEO。
如今,文化研究也如潮水般涌进了中国的大学,在全民都走完了奔小康的大道之后,中国的大学也开始脱贫致富,这使那些用人民币打造的“基地组织”(重点学科、研究中心等等),也显示出穷人乍富的阔气。文化研究很快就成为新宠,成为新的学术利润增长点。本来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学中文系,以为在狂热的经济学、法律学抢购风中就要走向穷途末路,却在文化研究中看到起死回生的希望。文化研究令人兴奋,它使90年代初备受责难的西学,不再那么生僻冷漠。这些玄奥的理论知识,因为带有暧昧的政治性,因为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与我们是那样亲近,那样容易合拍和协调--它看上去就具有“本土性”,很快就有人会这样说。不是“看上去”,而是,这就是它的根本诉求。管它是谁的“本土性”,只要在谈“本土性”就行。文化研究就这样几乎是天然地、合情合理地在大学学术中安营扎寨。它目前在中国虽然还只是蓄势待发,要不了多久,它就可以收拾金瓸一片。只要看看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研究》,印行了数千册,影响颇大,创刊号在北京三联书店连续数月进人排行榜首前几名,这就足以说明文化研究在青年学生中的号召力。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列人各个大学的议事日程,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开始转向这个方向。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辙更张。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是肯定的。出台后(走向文化研究)的文学肯定有所作为,向帝国的历史、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向媒体霸权、向妇女的服饰、向边缘人群、向环保产业、向IT网络等等进军,文化研究真是可以四面出击,笑傲江湖,何等风光!这与守身如玉、抱残守缺的传统文学研究的落寂状态,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文学在哪里?在这里,我们更加小心一点限定: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哪里?文艺学在哪里?确实,现当代文学最容易倒戈,只要越雷池一步,就可以进人旁门左道,其知识准备和思想方法,搞起文化研究正是得心应手。
这正是我们要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的动因所在。
当然,学术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只是受到既定的知识传统的制约,同时也受到时代的权力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的间接影响。学术规范只是处理本学科知识的规则和方法,并不能限定本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交互作用。就历史情况而言,并没有一个纯粹的文学学科存在,哲学始终就在直接影响文学学科。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就说明文学研究学科的包容性。不用说儒家道家学说渗透进文学,唐宋文学受佛教影响,文论也脱不了干系。在西方,柏拉图的思想阴影从来就没有离开文学领域,而文学批评更经常出自哲学家手笔。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近代的事,更准确地说,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大学出现哲学和文学批评教席才成为可能。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看法,英语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借着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情绪才走向兴盛的。尽管“新批评”是迄今为止最为纯粹的文学批评,但批评家们并不这么认为,“新批评”首先是宗教(艺术宗教),是整治混乱现实的济世良方,其次才是文学与审美。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更不用说,它确实是政治伴生物。现当代文学学科实际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变种,现代文学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过是在充分的政治阐释之后才留有一席之地。当代文学从来就没有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因此,要指望其他门类或学科的知识不要侵入文学学科,既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因为这种状况不是今天才发生。纯粹的文学研究并不存在,也很难指望以后能存在。
现在,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建立严格的学科体系规则也不可能。知识的更新和权威性的丧失,使严格的规范显得异常脆弱。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在遭遇强劲的挑战中,更是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获取新的活力。问题在于从业人员在完成知识更新的同时,保持对文学本身的关注。文化研究也不是天然地就和文学研究矛盾,根本的问题在于最后的落点。
很显然,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并不是要杜绝其他学科或门类的知识的运用,而是如何立足于文学本身。如何在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中,始终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保持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尽管说,什么叫做文学研究,什么不叫文学研究已经很难分辨,但是,对文学经验本身的关注依然是基本评判标准。在这个学科已有的历史传统序列中来思考不断变更的文学经验,显然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
但是,也许有一点根本的要义是需要把握的:不管过去人们把文学处置成何种东西,或何种样式,它都是在处置文学。问题的症结和严峻之处也许在于,现在人们也许根本不处置文学,文学不是因为被改变而失去存在理由,而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予理睬,连作为佐证的下脚料都无人光顾,那真是文学研究末日。文学在被抛弃的命运中荒芜。
根本的误区就在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总是被“责任感”所装点,批判性不只是长矛,更是一顶桂冠。这使野心勃勃的人们对文学经验、对审美体验之类的东西不屑一顾。大学文学系已经被改名更张,除少数老实巴交者还抱残守缺,其他都叫上了响亮的称号:“人文”、“传播”、“文化”等等。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学文学系已经怀疑向学生传授文学历史和经验的意义。人们信奉那些自以为是的批判能拯救超度芸芸众生,能改变世界。在这个日益粗糙平面单向度的时代,真不知道那些空洞浮夸的批判性是在助长什么东西。实际上,全部历史发展到今天,其混乱与灾难从来就没有在那些自以为是的批判中停息,而是在其中找到最好的生长场所,人们的心智却在种种的攻讦中异化并变得恶劣。因此,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现在也许确实需要建立,目前显然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方案,但却是可以确认出发点,那就是:顽强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回到审美体验本身。这并不只是建立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规范的需要,而且也是摆脱那些虚假的信念,回到我们更真切的心灵的需要。也许多少年之后,我们会意识到,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保持一种阅读态度、一种情感经验、一种审美感悟,也像保持某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重要。
在今天,这样一种希冀像是一种可笑的奢望,像是落败者的绝望请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力发出“建立学术规范”这种呼吁或祈求,人各有志,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选择一种生活,选择一种专业的方式;只是对明显有些荒芜的文学领地,期望有更多地同道者。写下这种文字,并不是要对别人说三道四,而是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文学同仁们的警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在潮流之外,没有人能够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被赦免。正像当年杀死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杀死文学的刽子手,如果现在不放下屠刀的话。
给文学招魂或差异性自由
当代文学呼唤什么?“呼唤”一词显然不只是因为缺失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因为本质性的东西的缺失,或者说魂灵的缺失,这才使得“呼唤”显得如此急迫,如此必需。
很显然,文学不会“呼唤”,是我们--这些文学的守灵人在呼唤;是我们一一在为文学招魂。为什么要如此急迫地呼唤?这是到了最危机的关头吗?是拯救的呼吁吗?我想大部分人是这样看的--这是一个善良的且有责任感的态度。只是我并不这样看,我并不认为当今文学真的就不行了,就是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泡沫,都是文化垃圾。特别是人们把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80年代相比,更是悲观失望。实际上,如果每年上千部的长篇小说还不足以说明当今文学的旺盛,那就是对眼前的事实置若罔闻了。80年代每年才几部作品?开始也就是几十部,最多的时候,到了80年代后期,也就不到200部。但人们就是留恋文学轰动的时代,但那样的轰动真是文学本身的力量吗?那些文学作品在艺术上,纯粹的文学性意义上,真是那么精彩纷呈吗?未必。关键还在于,现今人们对文学失去了热情,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耐心,当然,尤为可怕的还在于失去了信心。
显然,我们对文学有一种理想性的认识,这决定了我们认定文学的魂灵为何物。文学的魂灵是我们的理想性的投射,是我们的本质的倒影。这一切并不难想象,我们试图呼唤文学回到过去,重现往日的辉煌。而连接的方式则是理想性的思想品格、崇高博大的道德情怀,我深知这些东西对文学,尤其对当今的中国文学是重要的东西,但有两点:其一,这些东西太容易与过去的意识形态诉求等同;其二,这些东西并不是决定性的,它只能作为有活力的审美品质的一种原材料。很显然,我的提醒不会有多少人接受,人们依然会执著于大而无当的呼唤。我们设想只要招回往日迷失了的魂灵,文学又会重获新生。这一切真是如此吗?如果历史可以如此简单明了地重复,文学就不会失魂。问题的实质可能在于,丢失的魂灵并不是它的真实的魂灵,而只是被某个“幽灵”附体。
在我看来,文学并没有真的失魂。只是我们,我们这些人被巳死的文学的“魂灵”所迷惑,我们被幽灵附体,以至于我们看不清眼前的现实,看不到未来的道路。
“我们”当然是一个可疑的词汇,在这个多元主义盛行的时代,怎么还会有一个总体性的“我们”呢?在我的叙述中,我们与“他们”是经常重叠的。有时候我在“我们”之中,有时候,我在“他们”之外。但“我们”是在个人叙述中不得不借用的一个意义的集合体,它使我这样个人化的叙述抹去了生硬的分裂感。
文学不再需要魂灵,我们无须给文学招魂,文学只需要回到自身。只需要回到自身的审美品质。我们给文学呼唤什么?就是获得这种回到自身的“审美品质”。
当代中国文学要回到原来的那种历史气势中去是不可能了,在当今时代,它也受到电子信息产业革命带来的图像媒体扩张的挤压,这使它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更注重语言艺术所包含的审美品质。
当然,“审美品质”是一个非常复杂微妙的概念,它既显得笼统抽象,实际又非常具体细微。说到文学的“审美品质”,它首先是一个综合性的指称,这是文学传统形成的一种美学素质。它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怎么构成的?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面详尽论述,但我们可以触摸到它。面对这么一个具体实际的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文学事实,回到当前的一些文学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