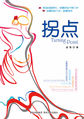西乡吉之助自萨摩匆匆出发,于7月10日再次来到了京都。当时,距离将军家定死讯公布的7月6日已过了四天,同时命西乡进京的藩主齐彬已经病危。而此时的西乡自然对此一无所知。
西乡于6月7日返回萨摩,当时尚在鹿儿岛的齐彬从西乡口中得知,一桥庆喜的拥立运动已因井伊直弼的强硬镇压而宣告失败。对齐彬而言,此事绝对不能放任不理。面对开国局势,日本上下必须做到思想统一、政权集中。倘若在各藩各自为政的形势下开国,日本全国就会出现无数的租借地和殖民地。
既然因武力处于劣势而被迫开国的窘境已成定局,那么确立能够集中日本整体力量的政治体制便成为必行之事,这远比理论更为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面对列强的强硬压力,需要成立凌驾于政党政派之上的非常时期内阁。
而这内阁的首领,非在水户学的熏陶下培养出的一桥庆喜担当不可。
“彦根竟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吗!”齐彬拍着大腿,对西乡说道。
当时,西乡已经变得更加成熟,能够理解藩主的焦躁心理。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要立刻追究幕府的责任,甚至推翻幕府。当此非常时期,依靠既有的谱代大名老中制是无法开辟一条生路的。而水户出身的一桥庆喜则具备明确的大义思想——朝廷是主人,将军是本家。因此,应该让一桥庆喜担任将军(或将军世子),集中日本的整体政权,重新巩固体制,以保证各藩不会在列强的分割政策下变得支离破碎。
因此,齐彬推举庆喜的决定绝对不是一时兴起的想法或玩笑。
“我是朝廷之臣,你们也是朝廷之臣,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凝聚在一起!”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一位能够如此振臂高呼的贤明的领导者。正因如此,齐彬才会特意给家定送去一位夫人,为拥立庆喜而努力。
然而,井伊直弼对如此明显的非常时期内阁的“必要性”却一无所知,不知他是对幕府的权力过度自信,还是对自己的实力过度自信。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容客套寒暄了。齐彬认为必须借朝廷之力,尽快修正条约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一分一秒也不能耽搁,所以才命西乡迅速重返京都,命他重新向朝廷上奏必须立庆喜为将军世子的理由。
虽然提出上奏必然要通过近卫家,但齐彬提出,若有必要,他可以以保护朝廷的名义率兵进京,因为他预想到井伊直弼恐怕会凭借武力威胁朝廷。
于是,西乡在鹿儿岛仅仅逗留了十天,便重返京都,于6月24日到达福冈,7月7日到达大坂。在大坂,西乡与吉井友实一起拜访了城代大久保要,确认了京都和江户当前的种种氛围,后于7月10日抵达京都。
西乡丝毫未能察觉,在他抵达京都的五天后,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岛津齐彬就会病故。回到京都后,西乡立刻拜访了位于鸭川畔的梁川星严的住居——鸭沂小隐,他以前经常出入于此。
梁川星严是美浓的诗人,号称日本的李白,当时已是七十岁高龄。他与藤田东湖也相当熟识,皆为京都学者中的长老。不,不仅仅是京都的学者,他可以说是整个日本的名士,名声甚至传到了公卿和朝廷耳中,而位于河畔丸太町的“鸭沂小隐”也成了忧国人士的聚集之所。
西乡之所以首先拜访这里,除了打算获取新情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
在大坂,他从同藩的吉井友实口中听到了一些自己离开京都期间发生的事情。其中令他感到最为震惊的,便是直弼强行决定立纪州为将军世子,并趁势擅自签订了条约。而且,直弼竟然还以驿使上书的轻率方式将此事通知朝廷。因此,天皇才会大为震怒,提出让位。
西乡听到这里,不禁浑身颤抖。
(这可了不得了!)
西乡诚挚的勤皇之火纯粹无比,已凌驾于其他水户人之上,如今,他高大身躯内的火种已蔓延开来。在鹿儿岛海滨的藩邸内,西乡倾尽心魂侍奉的藩主齐彬曾凝望着樱岛火山喷出的浓烟,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现在又涌现在了西乡心头。
“我也打算于近期率兵进京。”
或许齐彬已经看透了一切。西乡从大坂的八轩屋出发,乘坐大船沿淀川逆流而上,并从伏见抵达京都。一路上,他一直在思考这件事。
若将擅自签订条约的违诏行为,与打算通过驿使上书息事宁人的无礼举动作为独立的两件事情分开来看,那就并非不能原谅。然而,这两件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无视朝廷的不逞举动,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够解释清楚的问题了。
往严重里说,这种行为岂止是无视国体尊严,简直与不可能理解日本国体尊严的夷狄的做法如出一辙。当西乡听闻水户老公齐昭邀尾张、越前和一桥卿强行登城时,心中充满了期待。
(就这么做,就应该这么做!必须得这么做了!)
然而,强行登城也稀里糊涂地被直弼镇压下来,众人反而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禁闭隐居处分。当西乡听闻这一消息后,眼前顿时变得一片黑暗。
(日本这艘大船究竟会驶向何方啊……)
在船抵达伏见之前,西乡一直目不转睛地凝视天空,不住叹息。船靠岸后,他立刻坐上坐轿,片刻之间便已站在锦小路的藩邸前。然而,他并未进去,而是去了萨摩在附近的定点旅店键屋直助(俗称键直),扔下行李后便直接去了星严的居所。
西乡听闻直弼正打算让天皇移居彦根。如此一来,就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阻止直弼的胡作非为,那便是即刻催促藩主齐彬进京,依靠萨摩的兵力保护天皇,然后要求幕府改革。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齐彬定是早已料到会发生如此事态,所以才会向西乡透露自己率兵进京的意愿。
(只有这一个办法能够拯救天皇了!)
面对如此纠纷,京都的志士和学者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天皇的亲信近臣又在……做着如此的思考,西乡已站在了位于鸭川畔的星严家门前。
(镇定!)
西乡嘱咐自己要镇定。自己如今背负的已不仅仅是萨摩的命运,而是与齐彬这位不世出的明主一起承担着神国日本的命运。水户、越前、尾张和一桥都已在井伊直弼面前屈服,土佐和伊予也不出手。如今,萨摩已是日本唯一的希望。
太守齐彬的进京决意可以说是希望之光,西乡打算先向星严明言此事,然后再获取情报。
“有人在家吗?”他特意放轻声音,同时挺起了胸膛。
宅内立刻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应答声,那个声音十分熟悉,正是星严的夫人红兰女史。红兰女史打开拉门,一眼便看见了站在玄关处的西乡。
“哎呀!”红兰女史夸张地瞪大了眼睛,“西乡君,你还在京都啊?”
她并不知道西乡已经在萨摩和京都之间往返过,只是觉得与上次西乡到访时间相隔有些长。京都的生活氛围或许就是这样匆忙。
“不,我是从萨摩回来的。先生身体可好?”
西乡认真地回答着,脱下了草鞋。红兰女史一边高声唤寄读学生端来洗脚水,一边开口说道:“很好很好,他还是经常和年轻人们讨论国事,足以证明身体健康。这不,现在就在同潜庵先生商谈。”
“潜庵先生,是久我大纳言的……”
“就是那个春日赞岐守。两个人都板着脸,今天还没催我去上酒祛暑呢。”
“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潜庵先生。”
春日潜庵是久我家的诸大夫,绰号是京都大盐(平八郎),是与星严肝胆相照的阳明学者,连公卿中的硬汉岩仓具视都视为眼中钉,对其敬而远之。
京都的学者们心怀敬畏地将潜庵和星严称做二长老。如今,这二位长老一脸严肃地商谈,一定是关系到国事的重要谈话。
“是麻烦您帮我通报一声,还是……”
“趁他们不知道进去就行,或者招呼一声再进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
西乡迅速拭去脚上的尘土,走进面向河滩且能够听见鸭川水声的星严的书斋。
“我是萨摩的西乡,打扰了。”
这里同江户的藤田宅邸一样,志同道合之士可以十分随便地出入。红兰女史比星严年轻二十岁,素来开朗活泼,平易近人地迎接各色客人的到来。二人是通过诗歌恋爱结婚的,如此开放的气氛也令星严以自己的妻子为荣。
时值盛夏,拉门已被撤下,换成了帘子,所以即使西乡不出声招呼,对方也能听见他走近的声音。果不其然,今日的书斋之中并无祛暑的酒,瘦弱如鹤的星严和略显肥胖的潜庵正表情严肃地对坐着。现场气氛与平日意气风发的谈论氛围截然不同,空气中弥漫着凝重的沉默,西乡有些不解地打破了这种僵局:“先生,我刚从萨摩回来。”
“嗯……”
“在我出门期间,似乎发生了很多大事。”
“嗯……”
“这真是奇怪,两位先生都是怎么了?”
其时,春日潜庵四十八岁,星严七十岁。只见二人手捻胡须,正襟端坐,互相瞪视,一副互不相让的神情。两人的眼神中甚至还能感觉到一丝怪异。在西乡第三次催促后,星严才苦着脸将一张美浓纸递给了西乡。只见纸张开头写着一个粗大的“檄”字。
星严、潜庵二位长老想必亦感无奈痛心。今诸事并发,西储之事(将军世子)、外交亲和之事,更兼彦根进京之事,天下恐将大乱,宜尽快会集,书不尽言。
既没有收信人姓名,也没有署名,既非星严笔迹,亦非潜庵笔迹。
“这……是什么?”
这一次,潜庵愤然答道:“是立刻征兵杀入彦根的檄文。岂有此理!”
“杀入彦根?”
“没错,否则天皇就会被挟持至关东。星严老先生竟怀疑是我命人在胆小的黄口公卿之间散发檄文的!”
西乡哑然地打量着二人,因为他对自己出门期间京都内的种种流言还不是很了解。天皇被驿使文书激怒,提出让位……当西乡听到这一传闻时,他刚好出发去了萨摩。
“也就是说,井伊直弼当真打算挟持天皇?”
“没错。不知道彦根那家伙在做什么,竟然命江户的塙次郎调查承久的典故。我的确说过要先下手为强,但我不会说如今立刻杀入彦根这种胡闹的话,这实在是冤枉!”
“这就奇怪了,散发这份檄文之人究竟……”西乡疑惑地盯着手中的信纸。
“是赖三树三郎门下的大乐源太郎。”星严迅速地说,“大乐明明白白地对我说,春日赞岐守是知道此事的。”
“那是他迫不得已才说出的借口……他们借用我的名字……”
“大乐源太郎?”西乡想了一会儿,对这个名字十分陌生,“那人究竟是哪里的?”
“听说是长州吉田松阴的陪臣。吉田松阴最近突然变得十分激进,几年前他曾来过寒舍,自己的禁闭令解除后又开办了村塾,突然变得意气风发。因此,我才会告诉潜庵,倘若直弼要求天皇移居,我们只能秘密说动吉田,谋取西幸。我曾劝告他,在这种情况下,不要煽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要散布杀入彦根这种暴力传言。”
“您还是认为是我暗中煽动啊?”
“纵然你没有煽动,只要你一瞪眼,石头就会滚动,树叶也会飘落!”
“那可不是我的过错!我想,实际上应该是您老给大乐灌了太多酒的缘故吧。人喝醉后就会变得过于勇猛,叫人束手无策。”
“你对我的酒有意见吗?”
“不,我只是提出忠告,对年轻人的放任要适可而止。”
“哦,真有意思!”
争着争着,二人似乎都有些不好意思。
“如此说来,春日先生是不会喝我星严的酒喽?红红!拿酒来。”
身后的纸门突然打开,红兰女史端来酒盘,笑着坐了下来。
“先放这儿吧,祛暑一定要用烫酒,请不要烫到舌头。”
红兰女史命婢女拿来酒杯,先给西乡斟了一杯酒。西乡有些拘束地坐正了身子。
“这份檄文已经广为散发了吗?”
“是的,倘若落入狗贼之手……”说着,星严重重地拍着自己的大腿说道,“对了!散发这份檄文的罪魁祸首或许就是附近的梅田源次郎。”
“如此说来,还是和您老的酒不无干系啊。”春日潜庵仍旧显得毫无兴致,板着脸拿过酒杯。
“总之,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制定万全之策。不过,没有武力负责保护天皇,实在是太危险了。”
“关于这件事,”直至此刻,西乡才终于找到了说出要事的机会,“我家主公很快将会率兵进京,请二老放心。”
“什么?萨州公要率兵进京?”
“这……这是真的吗?”
“我何必说谎?”
“不,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放心了。其实,日下部伊三次曾自江户匆忙赶来通知,称彦根已经变得彻底狂乱。水户、尾张和一桥都在幽居,倘若井伊直弼趁势将手伸向京都,势必……所以才会出现这份檄文。原来如此……岛津大人他……”
二人的欣喜程度极其夸张,令西乡看得瞠目结舌,一时无语。
“如此一来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