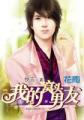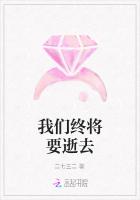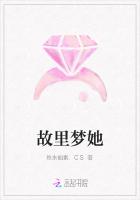梁寒烟看着围墙上方,墙外的那株大杨树,无论怎么修剪,每当一个盛夏一过,就会倔强地朝墙里伸出几根枝条,将许多黄叶摇落在这户每年开春都要伤害它一次的人家围墙里。现下已是深秋,大杨树的叶子掉得正欢,一阵风吹过,那些没伸进院墙来的枝条上的黄叶,也趁机飞进了院来。黄叶们似乎对这个小院的环境很满意,仗着秋风给他们撑腰,一忽儿在砖地上滑动,一忽儿向上飞舞,得意的时候就盘旋上几圈。
她已经看了很长时间,眼前的这些黄叶们随着风儿起伏,舞动的节律美妙也好,难看也罢,往者不可追;而接下来又会如何翻覆,则只有风知道。她觉得自己的命运似乎也和这些黄叶一样,曾经有过的勃勃生机,曾经有过的亮眼浓绿,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过去,现在就像这风中落叶,正在走向未可预知的最后一程。
其实她离生命的末路还很遥远,她今年四十岁刚过,常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得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还年轻几岁。她比十几年前稍稍胖了一点,但绝没有许多富家太太们那般的赘肉,除了眼角有几丝浅浅的鱼尾纹,脸上并没有更多岁月的划痕。如今的她正应了一句俗语——“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只是她的心态却比她的容颜更早的衰老了,已经没有了昔年那种锱铢必较、不甘人后的冲动。
邻居家的媳妇张继芳前两日来求她,要她劝说丈夫出手救人,那个待援救的人居然就是娘家的邻居赵汉昌。她没怎么多犹豫就答应了,在她的要求之下,丈夫夏玺臣倒是很卖力气,不过两天,事情就已经解决。上午邻居家的媳妇过来告诉她,赵汉昌已经在昨天放回家去,人是被打得不轻,但不会落下残疾,张家和春梅都表示了感谢,不过应她的要求,春梅并不知道是她和夏家施的援手。
她看着满地落叶,想到以前和春梅及赵汉昌的恩恩怨怨,感到当年和春梅争强好胜实在有点可笑,也觉得有些对不起赵汉昌——不管怎么说,赵汉昌落到如今的地步,追根溯源自己也有责任。正因有此心理,当她知道是赵汉昌需要帮忙时,马上就答应了下来,还催着丈夫去通门路。要说到她现在心理的变化,其中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与她目前的家境不无关系。
她嫁到夏家以后,似乎在她身上延续了夏家几代人都摆不脱的“魔咒”。夏家几代都是单传,每代都只有一子延续香火,而她在嫁过来的第二年生了儿子夏文翰,之后的二十年,再也没有能够生育哪怕是一个女儿。正因为此,夏玺臣违背祖训,居然在外与一个女人暗中来往。夏传林知道以后,装聋作哑不置一词,不过约束着夏玺臣,对此事绝不张扬,更不许将这个女人带回家中。
梁寒烟是前不久才偶然得知此事的,后来和丈夫吵了几次,夏玺臣最后答应她:和那个女人的来往,开始时完全是为了再想为夏家添个后代,这么些年下来没有达到目的,现在也已经渐渐冷落了,他不会给那女人什么名分,更不会将那女人带进家门。梁寒烟见事已至此,吵开去也没什么光彩,也就放过了丈夫。他将全部的心思和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文翰身上。但是现在这个寄托了她和夏家全部希望的儿子,却让她和全家都为之忧心忡忡起来。
夏文翰是夏家独苗,对他自然百般呵护,在教育上也很是重视。文翰还算争气,自小读书就很好,在滨湖读完小学,他爷爷夏传林做主,托朋友照顾,让他去了江海市上中学。夏文翰到了江海以后,不负爷爷之望,进了震旦大学附中。“七七事变”紧接着“八一三事变”,本已考入大学的夏文翰,在日本人占领江海市以后重新开学时,没有再回到学校。这两年他一直在家帮着打理家中的粮店,虽说中断了学业,但在这战乱的年月,他能在家里平平安安度日,全家也就满足了。谁都没有想到,几个月前,夏文翰的一个同学回到了家里,他开始常和这个同学还有其他几个同学聚首。一个偶然的机会,梁寒烟听到了儿子和那个同学的谈话,原来他们几个同学正在酝酿着离家出走,要到江北去参军打鬼子。夏玺臣知道后,和梁寒烟一样都很担心,坚决不同意此事,还想方设法要断绝夏文翰和几个同学的来往。反倒是年迈的夏传林,知道此事以后,认为孙子有志气,支持他去江北,还斥责儿子儿媳不该阻止文翰。唯有一点老爷子不同意孙子的选择——那几个同学中,大部分人都想去投新四军,唯有最早来找文翰的那个秦镇海,力主去投****。夏文翰原本随大流,想和大多数同学去江北或者茅山找新四军,夏传林发话要他投****,告诫孙子说,只有****才是正统。
夏老爷子一发话,夏玺臣和梁寒烟自然不敢再公开阻挠。夏玺臣倒还放得下,真的不再多管此事,梁寒烟却不免忧心忡忡,心中极度不安。
梁寒烟正在那里为儿子担心,夏文翰从外面走了进来。这几天他和秦镇海等几个同学已经商量好了,不管他们各自今后打算参加哪一支抗日队伍,现在还是一起走。他们决定渡江到江北去,秦镇海说他有熟人在那边,那熟人已经是少校了;而另一个同学的哥哥原本在茅山,是新四军,前些日子刚刚过了江,他们几个也打算渡江去找那个同学的哥哥。两拨人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同意一起走,路上互相好有个照应。
夏文翰在学校里的时候,和这个秦镇海关系最好,还是住的同一间寝室。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夏文翰已经报考了本校大学部,考试结束后和几个要好同学在江海最后聚一聚,就准备回老家等待通知。这个秦镇海本也是考大学的,但一听说北方日本人发动了事变,那里的中国驻军已经和日本人开打了,立即就买好车票到北平去。他临走时还拉上了几个同学一起走,当他试图劝说夏文翰的时候,夏文翰没有答应,秦镇海就在一天早上和十几个同学从学校里消失了。
夏文翰回到了家里,后来的“八一三事变”,以及日本人相继占领南京、徐州及半个中国,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夏家所在的村子在县城南边,离城还有一段路,日本人并没有在这里驻军,附近大镇上的日本驻军对夏家也并没过多的骚扰,他们家的粮店照常营业。但是这样的平静只是表面上的,这种平静的表象之下,首先是粮店的经营出了问题:日本人对粮食严格控制,特别是西边茅山有了新四军活动,日本人建立封锁线,不许物资向茅山那边流动,更不许那边的粮食向东边进入日伪占领区,凡是有偷越封锁线者,一经抓获立即当场枪决。如此一来,夏家的粮店断了货源,靠日本人的那点配给,粮店的生意也就名存实亡了。
夏家旦村上虽然没有驻扎日本人,但是周围日本人驻守的地点不少,还常常在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中国人只要是通过关卡,或者是经过升着日本膏药旗的地点,都必须脱帽鞠躬,一旦忘了鞠躬或者一个疏忽被日本人以为“不敬”,轻者被扇耳光,重者甚至当场毙命。夏文翰这两年来目睹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种种悲惨境况,开始后悔当年没有和那几个热血沸腾的同学一起去投军——即便是战死沙场,也要比现在这样强得多。
江南极其富庶,是日本人重点控制的地区,但是就是在这个日军密集驻防的地区里,出现了抗击日军的武装。远一些的是新四军在卫岗伏击日军,奇袭镇江火车站;近一些的则是在吴湖上出现了一支“吴湖抗日游击大队”,就在滨湖附近活动,而日本人却始终拿他们没有办法。夏文翰在心情郁闷的时候也想过去投奔这些抗日队伍,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能找到他们。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相对安定富裕的生活,也使他下不了决心。
正在此时,当年去北平的同学秦镇海竟然回来了。秦镇海是本地人,回来以后首先找到了夏文翰。他在了解了夏文翰的情况以后,就对他直说了他这次回家来的目的——
当年他和一些同学北上,本想投奔二十九军杀敌报国,谁想火车刚一到浦口就不走了,等他们步行北上的时候,在路上就得到了平津失陷的消息。后来同学们分散了,他就在徐州北参加了****。由于他是震旦附中的高中生,上司很快就看中了他,送他参加了干训班,后来又分到其它部队,现在已经是中尉军官。
秦镇海说他现在江北的****部队里,这次是奉命回来联络昔日的同学,还有家乡有文化的青年,要将这些青年动员回去充实部队的。他说****的部队里有文化的官兵实在不多,所以特别渴望有文化的青年从军,像夏文翰这样的名校高中生,一旦入伍就会迅速得到提拔。
夏文翰本就有意,秦镇海又是好同学,当时就表示了同意。他们又联络了一些同学,还有几个热血青年,准备一起投奔抗日战场。不过在决定投奔谁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分歧,大部分人想投奔新四军,秦镇海和少部分人则想投奔****。
夏文翰对****还是新四军本来都无成见,既然秦镇海和爷爷都想让他投奔****,他也就答应跟着秦镇海走了。他们已经商量好,就在这几天走,他现在回来,看到母亲那种担忧的眼神,一时倒也不知怎么说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