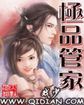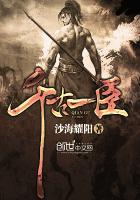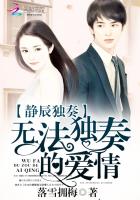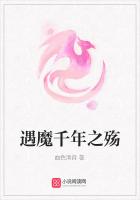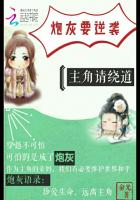文治三年(公元1187年),曾经一度归国。已经50岁的荣西,因觉得自己的学问修为仍然远远不够,所以再度西渡中国学习佛法,四年后回到了日本。这一次,他带回了两样东西:茶种和禅宗。
其实茶叶在日本一直都有,早在延历二十四年(公元803年),从唐朝归国的遣唐使永忠和尚就带了几麻袋茶叶回日本,并且呈交给了当时的嵯峨天皇。据说这位文艺天皇在收到这份独特的礼物后显得非常的高兴,还专门为此做过和歌一首。
不过,当时在日本的茶叶全都属特供产品,仅给上层贵族享用,而且还被当作了一种名贵药材,并非是饮料。
那会儿的茶叶主治中风、糖尿病、厌食症以及脚气病等病症,并且还附有强身健体等功效,在朝廷的王公贵族中人气非常高。
当然,这只是茶叶,一种能干嚼或是泡开水的食物,和茶道没有零星半点的关系,甚至和茶这种植物也没几毛钱的联系,因为永忠和尚带回来的,只是被晒干了的茶叶罢了。
虽然如今也有说法,认为永忠也把茶种带了回来,并且也确实在京都一带种植,但这即便是真的,那也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内流行,而且也无法改变茶叶药用的事实。
事实上日本真正开始产茶,并且成为了近代亚洲重要的茶叶产地,确实是荣西带茶归国之后的事情,而且在他的带动下,热茶这种东西也就此步入日本的民间,并且大受好评,还得到了时任镰仓幕府的三代将军源实朝的大力推荐。
且说在荣西第二次回国后曾经拜访过一次源实朝,结果却发现位于坐席之上的将军大人不但眼神游离,而且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全然一副病怏怏的模样。
于是荣西问道:“大人,你是不是病了?”
“让大师见笑了,我是昨天喝多了,头疼。”源实朝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说了实话。
日本人是一个天生就不怎么会喝酒,却偏偏特别爱喝的民族,所以宿醉对于日本男人而言,属家常便饭,从古代到如今,从将军到平民,都不乏受害者。
荣西听完后便表示这么个疼法也不是个事儿,您还是吃点什么吧。
可当时日本医疗水平相当落后,像宿醉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医学上的对策,只能靠人本身的能力把酒劲熬过去。所以源实朝连连摆手,说:“没啥好吃的,就这样吧。”
“等等。”荣西突然想起了什么,“大人,贫僧有药。”
这药其实就是茶叶,因为他觉得打禅的时候累了喝茶能醒脑,那么醉酒的话喝茶也能变得清醒,道理是相通的。
在喝下了一碗热茶之后,源实朝确实感到清醒了很多,头也一下子不疼了。
于是,将军就这样成为了饮茶爱好者,而且每次开会或者会客都会向别人推荐喝茶。
不过对于此时此刻的日本而言,茶仍然是一种比较名贵的东西,所以一般享用之前,客人为了表达对主人的尊重,而主人又想凸显这东西的稀罕,往往会搞出一套又一套相当繁琐的礼仪。这也就是茶道在日本的由来。
其实茶还没说完,但得先说说禅。
跟茶一样,早在唐朝的时候,禅宗的一些理论就被各种僧人从中国传入了日本,比如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唐朝僧人义空应嵯峨天皇的老婆橘嘉智子皇后之邀,东渡日本开坛论禅,可是因为当时日本人对禅宗全然没兴趣,朝廷方面也不过是叶公好龙,所以在日本待了几年却毫无建树,顿感前景渺茫的义空,灰溜溜地回了国。
之后的数百年里,虽然陆陆续续地有两国僧人在各类往来中将禅宗点点滴滴地传来日本,但终究只是点点滴滴,并无系统可言。
但是荣西却不一样,这人之所以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的原因,就是他带回来的并非鸡零狗碎的豆知识,而是一整个宗派——临济宗。
临济宗是禅宗南宗下五个主要流派里的一个,始于中国唐代,讲究的是心即是佛。
到了宋朝,临济宗被分出了杨岐派和黄龙派,其中荣西传回日本的,正是黄龙派。
至于杨岐派,则是在宽元四年(公元1246年)由中国僧人兰溪道隆东渡日本带过去的。
再说荣西为了避免数百年前义空和尚的前车之鉴,特地跟镰仓幕府搞好了关系,比如隔三岔五给将军弄点热茶解解酒什么的,然后在幕府的支持下大力开始推广禅宗。应该讲这一招的确很有效,至少禅宗就此在日本生根发芽了。
镰仓时代的日本禅宗主要分为两个宗派——临济宗和曹洞宗,然后再在这两宗之下,衍生出二十四个分流派。
临济宗前面提到过,而曹洞宗也是起源于中国,信奉“万物皆虚幻”,在嘉禄二年(公元1226年)的时候由一个叫道元的入宋僧给传入日本的。
说起来这个道元也算是传奇人物了,自幼就有神童之称,而且貌似天生带有佛性,他学成曹洞宗归国普度众生的那一年不过26岁,因为实在是过于年轻,所以当时还成了轰动一方的大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道元其实是荣西的徒孙,他的师傅叫明全,乃荣西门下高足,本来是跟道元一起去的中国,但却在求佛的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圆寂于湖南的景德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荣西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日本禅宗之祖。
插一句,虽然曹洞宗在如今的中国可能连听说过的人都不多,但其大本营却是超级有名,那便是嵩山的少林寺。
禅宗被传入日本之后,除了理所当然地在佛教圈内流行之外,还有点让人意外地跟茶道结合在了一起。
这事儿要从公元16世纪开始讲起,那时候的日本茶道在形式上已经开始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首先,参加茶会的人不再只拘泥于贵族了,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好这一口,而且手里有个茶碗,都能开一场茶会;其次是茶道的礼节,也不再跟以往那样喝一口茶都要搞一套繁琐的礼节,而是被直接简化成了四个字:敬寂清和。
“敬”就是尊敬,表现为上下关系分明,有礼仪;“寂”就是凝神、摒弃欲望,表现为茶室中的气氛恬静,茶人们表情庄重,凝神静气;“清”就是纯洁、清静,表现在茶室茶具的清洁、人心的清净;“和”就是和睦,表现为主客之间的和睦。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值战国乱世,兵荒马乱,人人都过着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日子,难免就会发生厌世的烦躁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就能让人静下心来的热茶,和教人向佛度人极乐的佛禅,因其本质其实是相同的,于是便被顺理成章地凑在了一块儿。
而随着人们对茶道和禅宗理解的不断加深,一个堪称是日本茶道终极精髓的理论也被提了出来,那就是“一期一会”。
一期,就是一生;一会,就是见一次。两个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一辈子只碰得上一次。
放在茶道里的意思便是你现在喝的这杯茶,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同样的一杯;甚至是现在喝的这一口茶,这辈子也不会有重复的第二口;而现在陪你喝茶的那个人,兴许这辈子就再也碰不到第二次了,于对方而言也是如此。
这种人生无常的道理,在无常的战乱时代相当流行,同时虽然这道理表面看起来相当悲观苍凉,但实际上却包含着一层更深的意思——不仅是人生,即便是在人生中经历的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重复。作为人类而言,要珍惜每个瞬间的机缘,并为人生中可能仅有的一次相会,付出全部的心力。若因漫不经心轻忽了眼前所有,那会是比擦身而过更为深刻的遗憾。
顺便插一句,这套说法不光能放在茶道上,就算在其他方面也被广泛地运用着,比如在赏花方面,日本人就相当推崇“今年的樱花只有今年有”这么一个说法。
可以说,日本茶道最终是走向了一条和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时因为变化实在是过于巨大以及融入了太多的自家文化,以至于时至今日,有很多人误以为茶道乃是日本的国粹。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必要来专门说一说茶道中所不曾变化的地方,那就是泡茶喝茶的具体过程。
不管茶道的礼仪动作是繁琐还是简单,也不管这碗茶是不是讲究“一期一会”,日本茶道的本质流程却是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先是在茶碗里放上一勺茶粉,然后倒上热水泡开,为了让茶粉很均匀地溶在水里,还要拿一个小刷子刷几下,刷完之后,再注入些许热水,一杯热茶就这么泡成了。
由于我们中国人平时喝茶一般都只是往杯子里放点干茶叶,然后浇上开水了事,再加上日本人在搞茶道的时候通常还要穿和服什么的,所以每当看着他们泡茶喝茶,真会有一种“日本制造”的感觉。
其实这是错觉。
日本的茶道,堪称是形意结合。我们不能否认其中的“意”,比如“一期一会”,确系日本人自己的原创,但是这“形”,则是完完全全传承于中国。
具体说来的话,就是宋朝的“点茶”。
点茶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和焚香、挂画、插花三样并称为宋代四艺。
其中,插花、焚香和点茶都传入了日本,经过各种融合发展后,变成了今天的花道、香道和茶道。
点茶也叫抹茶法。因为其泡法跟上述的日本茶道几乎无差,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只是就一些专业名词和需注意的事项做一个简单的补充说明。
首先,那个舀茶叶末的勺子,叫茶匙。
其次,那把小刷子,叫茶筅,在日本也被称作茶筌,多为竹制。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就有明确说法:“茶筅以劲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然后茶筅上面的小刷穗儿也有讲究,日本人根据穗数的不同,可以分为平穗(16根)、荒穗(36根)、野点(54根)、常穗(64根)、数穗(72根)、八十本立(80根)、百本立(100根)、百二十本立(120根)等八种,刷穗儿的多寡,可直接影响到这碗茶的浓淡。
第三,用茶筅刷茶的这个动作,叫运筅或者击拂。在具体的点茶操作中,运筅的同时还要往里注水,将茶粉跟热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个过程非常注重双手的配合,故而宋朝的那些茶道高手,也会有“三昧手”之称。
从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开始算起,至今已然有一千多年了,一样东西在邻国被完整保存了一千多年,而我们自己这里倒是弄得像快要失传了一样,这实在是令人无语。
平心而论,越是深入品读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往往就越会产生一种对中国的喜爱和崇拜,伴随着这种喜爱与崇拜而生的,却是一股淡淡的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