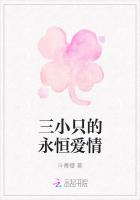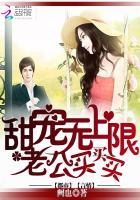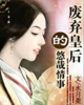但索尔斯并不想当这个官,杜鲁门找到他的时候,他一再推辞,因为他知道中央情报主任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然而,杜鲁门却极力劝他接受这个任命,并不无奉承地说,在找到一位合适的“常任中央情报主任”之前,必须要有一位担当大任的人来临时担任主任之职。杜鲁门向他保证,一旦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协商提出一个自己所能接受的人选,就立即解除他的中央情报主任的职务。无奈之下,索尔斯只好答应了。
索尔斯终于上任了,成为第一任中央情报主任。1946年1月25日,杜鲁门亲自为索尔斯任职举行了一个小型招待会。与会者都接受了总统赠送的象征秘密特工的斗篷与匕首。显然,杜鲁门赠送的礼物有些欠妥,因为根据当时的美国法律,中央情报组并没有进行间谍活动的权力。
索尔斯虽然上任了,但是这个机构的权力与它的职能任务并不相称,也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和力量协调美国各情报机构对付当时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索尔斯在这样一个颇受局限的职位上虽然只做了四个半月,但是,他对中央情报组的影响却十分深远。
索尔斯与多诺万一样,都是情报机构的组建者。然而,两人所处的境遇却大相径庭。多诺万组建情报协调局的时候,是完全听命于总统的,其他部门无权干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拥有大笔不用报批的经费去招募人员、租房子、买设备、开展各种情报活动,还拥有独立的处分权,完全都是自己说了算。索尔斯则不同,上面有许多部门是他的上级,而下面又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人,也没有独立的经费,没有开展工作的自主权,也没有人员的调用权,自己说了不算,因而组建初期极为艰难。
多诺万擅长做没人敢做的事,什么事情他都敢尝试。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还善于动用各种关系,想尽各种办法去说服别人或别的部门。多诺万首创外国情报搜集和协调的工作模式,在实现自己计划的过程中,显示出了令人折服的创造力与领导力。而索尔斯则不同,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奉命行事是他的习惯。虽然他是这个新的情报机构的主要设计者,然而他十分清楚,在机构组建过程中,各方激烈的明争暗斗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埋下了障碍,使之很容易与其他情报机构发生争议。
特别是当他意识到,他的中央情报组在人员与资金这两个重要方面,都必须依赖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时候,他就更为谨慎小心了。
索尔斯十分清楚,自己的顶头上司是汇集了权威部门的权威人物的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委员们个个都惹不起,他们与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帮家伙都能对他发号施令。索尔斯在担任中央情报主任仅仅135天的时间里,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便给他下了三道训令。
除此之外,索尔斯还受制于一个名气不大但势力不小的情报咨询委员会。情报咨询委员会的四名成员分别来自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陆军航空兵,他们分别是国务卿特别助理麦科马克、新任陆军情报局局长霍伊特·范登堡中将、海军情报局局长英格利斯少将和陆军航空兵情报处处长乔治·唐纳德准将。在这些人的牵制之下,索尔斯的工作更加难开展。
有些时候,联邦调查局局长也会应中央情报主任的邀请,出席情报咨询委员会的相关会议。这些情报单位的头头们与中央情报组之间的利害关系直接而具体。仅从表面上来看,情报咨询委员会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咨询机构。而事实上,中央情报组的人员、经费和设备统统靠它提供,因此,索尔斯也不敢得罪。情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们各自维护各自的利益,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中央情报主任和中央情报组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
如此多的限制,让索尔斯束手束脚,就如同“三明治”,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也就注定了索尔斯难有作为。
索尔斯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各个部门请示工作。除此之外,索尔斯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向他们借调人员——没有人员中央情报组无法运作。于是,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陆军航空兵局长各为索尔斯调派了两名人员,由此,中央情报组才正式运作起来。可见,在这种机制下当中央情报主任,的确是一个苦差事。
虽然索尔斯的权力有限,但工作思路非常清晰。上任之后,他首先以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给自己下达指令,规范中央情报组的性质、职责和使命,以此作为新机构的工作方针和原则。
从国务院借调来的蒙塔古上校和小詹姆斯上校,曾分别任职于陆军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围绕中央情报组的设置各方争斗的内幕十分清楚,他们奉命与索尔斯一起起草了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给中央情报主任的第一项指令与第二项指令。这两项指令草案于1946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提交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和情报咨询委员会讨论通过,2月8日正式颁布实施。
第一项指令,首先规定了中央情报组的性质,规定中央情报组的“组织与运行属于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陆军航空兵平等参与的部门之间的合作活动”,明确了中央情报组的行政性质属于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的非独立部门,是几个部门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合作机构。这项指令还指出,中央情报组的任务是,为总统、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提供战略情报和国家政策情报。这一点在后来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中央情报组是否有权开展国家情报评估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是将中央情报组作为一个大型研究分析机构看待,还是作为一个小型专业评估机构看待。
第一项指令还规定,中央情报组提出的任何建议,首先要提交情报咨询委员会讨论通过,再提交情报管理委员会。如果情报咨询委员有任何一名委员不同意该建议,那么需将不同意的理由和建议一并上报给情报管理委员会。事实上,这项规定为中央情报主任与情报咨询委员会及各情报部门主管之间的长期权力之争埋下了伏笔,也让中央情报主任多少掌握了一些与情报咨询委员会及各个情报机构主管对抗的权力。由于该规定是要求中央情报组将情报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反对意见和理由上报给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并非要求情报咨询委员会作出同意或反对的决定,使得情报咨询委员会委员无法作出主观决定,也使得情报咨询委员会更像是咨询机构而非领导部门,这一点在日后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第二项指令题为《中央情报组的组织与职能》。该指令规定,中央情报组具有协调情报工作、汇编情报简报以及开展情报活动等职能。后来,索尔斯根据此规定,在中央情报组下设了三个部门,一个是负责提供战略和国家安全情报的中央报道办公室,一个是负责情报活动协调计划的中央计划办公室,还有一个是中央情报处。
第二项指令规定了中央情报主任须优先考虑的两项紧迫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对现有的搜集外国情报的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索尔斯为此组建了中央计划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事关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并就情报政策与目标提出建议,以确保有效地完成国家的情报使命。起初,索尔斯倾向于由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计划协调情报活动。然而,要从相关部门召集足够的工作人员十分困难。无奈之下,他只能依靠自己的中央计划办公室。
第二项紧迫任务是,把每天有关国家安全和与外国重要事务相关的情报大事和情报活动编成情况综述,供总统及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成员阅读。
事实上,当初杜鲁门组建中央情报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获得综合性的每日情报摘要,以便尽快浏览情报概要,还可避免出现之前的各个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相互矛盾的现象。然而,杜鲁门对中央情报组的这个希望和要求,却引发了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内部的第一个分歧。在一次会议上,国务卿贝尔纳斯指出“向总统汇报有关外交政策的事务”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他认为,让中央情报组负责这样的事情有损国务院的地位,因而一直不同意签署第二项指令。
索尔斯详细地了解此事之后,便申明中央情报主任向总统汇报情报只是基于情报急件,并不会带任何个人色彩,也不提供任何建议。海军上将莱希进一步解释了总统需要这些情报综述的原因。然而,他们的解释并没有打动贝尔纳斯。中央情报组只好让步,决定先将情报综述报给国务卿,国务卿审阅之后再报给总统。贝尔纳斯与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杜鲁门向他保证说,自己只需要中央情报组报告实际的事实情况,贝尔纳斯才勉强同意签署第二项指令。在会上,贝尔纳斯强调,总统要求的情报综述中只能包含“事实的陈述”。第二项指令还要求四个有关部门为索尔斯调配165名工作人员。
之后,索尔斯宣布了中央情报组内部的第一项人事任命。他一共任命了三位主任助理,他们各自负责一个主要部门,蒙塔古上校负责中央报道办公室,戈格金斯上校负责中央计划办公室,福蒂埃准将负责中央情报处。各项任命完毕后,中央情报组组建工作基本结束,开始正常运行起来了。
当中央情报组正常运转之后,索尔斯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应该给总统提供一份怎样的情报综述呢?
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对此有着不同的答复与解释,索尔斯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不受情报管理委员会委员们的左右。于是,中央情报组中央报道办公室在接到索尔斯指令一周之后,便正式出了第一期《每日情报摘要》。由此,索尔斯开创了一个先例,那就是每天为总统提供一份最新的情报摘要。杜鲁门于每天早晨8点15分浏览这份情报摘要。一段时间后,杜鲁门对中央情报组的《每日情报摘要》相当满意,他认为《每日情报摘要》解决了情报协调与综合的难题,也找出了一个让总统直接了解情况的好办法。
1946年2月21日,在《国情咨文》中,杜鲁门提到情报工作,说战时的一些活动已经成为常规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杜鲁门这一表态,无疑是对情报工作的认可。几天以后,杜鲁门又宣称成立新的中央情报机构是一项必要的工作安排,中央情报组将为美国的最高利益开展工作。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公开宣传情报工作,并且是出自总统之口。这一宣传的效果就是,80%的美国民众认为国会应当出资建立并维持一支强大的秘密特工队伍,并使这支强大的特工力量活动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以保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
当然,如果没有索尔斯妥善地、出色地打理中央情报组,使中央情报组的工作得到杜鲁门的高度认可,杜鲁门是不会这样宣传的,而美国民众对情报机构的态度也不会由反对转变为支持的。
在为总统与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提供情报的问题上,索尔斯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对情报进行研究与分析,撰写外国实力与意图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评估性材料,他认为这是中央情报组的首要任务。然而,中央情报组人手太少,并且没有人员招募权和必要的经费。所以,索尔斯在任期内,没能提供从国家角度所作的评估性材料。索尔斯原本希望把原来战略情报局的研究与分析处并入中央情报组,但该处当时已划归国务院的研究与情报办公室,后来更名为情报协调与联络办公室。索尔斯打算自己筹建研究与分析部门,但由于任职时间太短,筹建这个部门的工作只能留给第二任中央情报主任范登堡。
索尔斯十分希望在《每日情报摘要》中加入解释性的内容,然而有禁令在先,中央情报组只能提供“事实的情况”。不过,索尔斯并没被难住。为了避开禁令,索尔斯试着以一种变通的形式来编一份《每周情报摘要》,在这份情报摘要中,加入了解释性文字。索尔斯向情报咨询委员会通报说,对于中央情报组的工作而言,《每周情报摘要》的编写是十分必要与迫切的,必须派熟练的情报人员来做这件事情。
没过多久,索尔斯便出了第一期《每周情报摘要》试刊,新任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兰格对此产生了警觉。他曾是原战略情报局研究与分析部门的负责人,战略情报局解散之后被调到国务院任助理国务卿。他从助理国务卿的角度认为,中央情报组不具备对情报数据进行任何解释的权力。当然,兰格的警觉并没有让情报咨询委员会其他成员对索尔斯的《每周情报摘要》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反而很支持。
索尔斯在任中央情报主任期间,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处理,那就是对政府各情报机构的工作进行协调。当然,这不仅是索尔斯的职责所在,也是整个中央情报组的职责所在,中央情报组也的确履行着这一职责。中央情报组在成立伊始,就开始征询军方情报部门、联邦调查局对情报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并对这些意见与建议进行研究汇总。这种可有可无的协调,虽然看起来似乎能对一些机构进行指挥,能协调一些机构的行动,还能协调通过一些美国商业公司搜集外国情报等事宜,但这所谓的权力没有任何意义。
就这样,索尔斯在这样一个没有实权的位置上担任了四个半月的领导人。虽然只有四个半月,虽然没有实权,但索尔斯依然让这个受制于许多部门的机构发挥了它的作用。其中,《每周情报摘要》的编写与在摘要中加入解释性文字便是明证。中央情报组在受制于其他部门的情况下,依然推动了美国中央情报界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索尔斯也对后来中央情报局的建立有着重要贡献,也应该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