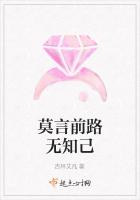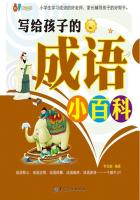叙事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民族对世界的体悟和认知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倾向于被表述为一种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东方的思想文化传统则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面,追求天人合一。表现在叙事上,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民族的叙事思维也有着不小的差别,甚至有的时候达到了彼此难以相互理解的程度。那么,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它一方面根植于中国文学艺术传统中源远流长的“离与合”的叙事和抒情原型,另一方面又有着不同于美国好莱坞古典叙事模式的对叙事时间的整体性把握、叙事空间的复沓轮回、时空结构的点面结合、循环往复以及充分利用有意味的意象细节贯串影片始终,并且对全知叙事格外钟情等特点,所有这些都凝聚成了中国电影悲欢离合叙事结构怎样的艺术魅力呢?它与好莱坞主流电影中英雄凭借个人超常的意志和能力最终战胜对手、赢得胜利和得到奖赏的叙事模式有着怎样不同的吸引力和审美形态呢?这是笔者在本章中力图解决的问题。
(第一节)曲折掩映的叙事构思
中国艺术富于线性美,“注重以线构形”[1,P153],关于这一点,李泽厚曾经做了反复阐释,诸如“在造型艺术部类,线的因素体现着中国民族的审美特征。线的艺术又恰好是与情感有关的”[2,P66],“中国艺术是时间的艺术、情感的艺术。……‘线’则是时间在空间里的展开”[2,P270],他甚至把“线”的运动提高到这样的地位:
“你能掌握这音乐——线——情感的运动么?那就是华夏文艺的精神”[2,P271]。
李泽厚还分析了中国艺术讲究线性美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讲究‘线’的艺术,正因为这‘线’是生命的运动和运动的生命。所以中国美学一向重视的不是静态的对象、实体、外貌,而是对象的内在的功能、结构、关系;而这种功能、结构和关系,归根到底又来自和被决定于动态的生命”[2,P283]。
由此可见,“线”不仅是中国艺术最有表现力的一种艺术元素,更是对中国艺术独有魅力的概括,那些在时间流程中展开的、富有动感的实在或者虚幻的“线”深深凝聚着中国艺术之美,这与西方艺术注重对面与体的展示情趣迥异。譬如,中国古典绘画讲究线条美,人物画也不突出立体感,而是衣带飘飘,重在神韵;中国的传统建筑,飞檐之流线,回廊之曲折,极富回环往复的线条美;中国的书法艺术更是一绝,完全靠线条的轻重缓急、粗细浓淡传神;中国的古典音乐也多是清雅的独奏,而没有西方交响乐的立体感。中国叙事文学也讲求叙事的婉转曲折之妙,金圣叹说“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斯真天下之至乐也”[3,P290],所以,我们在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中很少见到如巴尔扎克作品中那般详细地对某一具体场景的描写,中国人似乎更习惯于在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错落掩映上下工夫。因此,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其异于西洋文学艺术之精神者,即在中国文学艺术之可供人之游”[4,P221],而“可游之美,乃回环往复悠扬之美”[4,P224],是一种线性美。具体到中国电影,其悲欢离合叙事结构通常观照的是人物角色在一定历史阶段或者比较长的时间跨度中的经历,因此故事时空流转比较快,影片并不特别注重对某一空间的细致铺开,却尤其注重人物经历的曲折离奇和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摇曳流动的趣味。对此,中国电影人似乎早就有了自觉的认知,如郑正秋就曾这样阐述他的编剧经验,“戏剧情节、不宜率直、求其曲折、必须多所映衬、旁敲侧击”[5],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叙事的曲折掩映之美。而且,为了增加叙事的趣味,使叙事的线性演进多些回环曲折的美感,而不是平铺直叙、一泻千里,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有一些常用的叙事技巧和叙事手段。
比较突出的有两种,首先是利用人物身份制造趣味。例如1926年张石川导演的《空谷兰》,影片叙事的一个重要玄机就是纫珠的身份之谜。她离家出走之后,由于把自己的披肩借给侍女翠翠,以至于翠翠出车祸死去被误认为是纫珠身亡,从而有多年之后纫珠化名幽兰再度归来、并最终与兰荪破镜重圆的离奇情节安排。1928年依然是由张石川导演的、娱乐色彩更浓的《白云塔》中,凤子在父亲死去、恋人被绿姬迷惑疏远自己之后黯然离去,后来当地来了一个风度翩翩的佳公子红叶,用计拆穿了绿姬母女的阴谋,却原来红叶公子竟是凤子女扮男装,于是一对恋人得以重归于好,人物身份的扑朔迷离是影片叙事趣味的关键所在。
1947年田汉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忆江南》中,先后嫁给周稚云的沦陷区乡下姑娘黛娥与香港交际花玫瑰竟是同胞姐妹,这一离奇的角色关系使《忆江南》的情节展开显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极尽跌宕起伏之能事。1958年谢添导演的《探亲记》中,田大爷去北京看望参军离家十几年的儿子田刚,在火车上、在北京,他遇到了许多故旧亲朋,但是这些人都不知道田大爷的儿子在北京做副局长,而田副局长和他爱人却也是百般躲避和田大爷相见、不把田大爷接到自己家里;影片最后田副局长出现,大家才发现他根本就不是田刚,而是当年和田刚并肩作战的战友;原来是他不忍心把田刚牺牲的消息告诉老人,于是十几年来一直以田刚的身份给老人写信和寄钱,影片借助于田副局长的身份之谜不仅增添了一波三折、疑窦丛生的叙事趣味,而且欲扬先抑,赞叹了军民、战友情意。《小花》也是一部借人物身份之谜叙事和抒情的影片。小花原来是周医生的女儿董红果,英姿飒爽的民兵区长何翠姑才是真的小花。影片在叙事过程中对此多次加以暗示。如赵永生第一次见到何翠姑,朦胧中把她看作自己的母亲,小花与何翠姑在水田边踩水车时也发现何翠姑很像年轻时候的母亲;而周医生带小花来到战地医院寻找她的哥哥的时候,女护士们都猜测小花是周医生的女儿,晚上周医生和小花卧床谈心,说起十八年前送掉的女儿红果时感慨“现在就是在我跟前,我也认不出来”!真假小花的谜团,叙事的藏头露尾,使观众迫切期待故事向前发展,直至谜团揭开。
其次是利用偶遇来增加叙事的曲折。“巧合”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常用技巧,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更是屡见不鲜,李亦中的论文《“巧合”备忘录》就专门分析了“巧合”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影片中的运用。而具体到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角色的偶遇,由于在人物的离与合之间隔了漫长的时空跨度,就更有一种绵长复杂的感慨在里面。相隔多年之后的偶遇,不仅带有巨大的情感冲击力,更令人迅速地想起曾经的前尘往事,从而使得叙事的线条愈加清晰和突显。例如在1958年由马拉沁夫编剧、朱文顺导演、反映内蒙古人民斗争岁月的《草原晨曲》中,胡合和朋友因为抗争日本侵略被追捕、与妻子绣枝分别,内蒙古解放之后,胡合回到家乡指挥工业建设,从北京来的技术人员张祥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的一个优秀青年,在草原人民庆祝建设成绩的夜晚,张祥的母亲从北京来看他,此时胡合发现张祥的母亲正是自己苦苦思念的妻子绣枝,于是一家人得以团圆。1982年于洋导演的《大海在呼唤》这部影片中,巴波罗来中国探望自己的老朋友陈船长,然而船长却已经随“上海号”出航了,巴波罗眼睁睁看着轮船远去,船长也只能向老朋友鸣笛致意。此后,影片以三条线索交叉叙事,一条是现在的巴波罗不断换乘飞机追赶着陈船长,另一条是陈船长现在在客轮上的工作,还有一条就是陈船长回忆二人的友谊以及在旧社会的海轮上二人曾经受尽外国人欺压的痛苦经历。一个海上的风雨之夜,“上海号”救助了小岛灯塔上的一名病重患者,而这个患者正是巴波罗,他是为了来这里迎接自己的老朋友、带病修灯塔而使病情变严重的,两个双鬓斑白的老朋友以这样的方式在茫茫大海上相遇。2004年黄建新、尔冬升监制、小江导演的《电影往事》中,毛大兵在北京打工、送纯净水,一天他经过一个小巷子撞倒了一摞砖头,一个女孩冲上来用砖头把毛大兵拍晕,在派出所毛大兵接受了女孩的请求,在她被拘留期间去她家照顾金鱼。通过阅读女孩的日记,毛大兵发现原来她竟是自己小时候的玩伴玲玲!
这次偶遇打开了毛大兵记忆的闸门,通过玲玲的日记,过往的岁月一一浮现,所有与电影有关的人生悲喜从头道来。
(第二节)委婉动人的情感抒发
一、对抒情性的追求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抒情的传统源远流长。古代文论家陆机有“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刘勰更有“故情者,文之经”的阐述。对中国文学长于抒情的特点,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例如,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在其《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重点在抒情”[6,P10],台湾学者孙隆基也认为“无论指物或指人,中国人的文艺创作的内容都偏向于‘情’这个方面。事实上,在中国人的文艺里,个体精神形态之其他种类的表现——例如:个人的心理状态、存在状态——是相对贫乏的,但是,却产生了世界上最丰硕的‘感物伤情’或‘触景生情’
的文学传统”[7,P96],有的研究者也从比较文学这个角度出发,指出“就古典文学而言,西方以叙事文学为本位,中国以抒情文学为本位”[8,P245],唐君毅先生则另辟蹊径,通过考察汉语语言的特点悟出中国文艺之所以长于吟咏和抒发感慨的一个原因,即“中国词类之特多助词,如矣、也、焉、哉之类,皆所以助人之涵泳吟味”[4,P234235],李泽厚也认为“情感和感受的细致、微妙、含蓄、深远,经常成为所谓‘一唱三叹’、‘馀意不尽’的中国艺术的特征”[2,P240]。由此可见,对抒情性的追求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固有传统。
具体到中国电影,其悲欢离合叙事结构本就着眼于人生的悲欢离合,最易于抒发情怀,正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对人生中诸多生离死别、劫后余生、不期而遇的观照,使得这些影片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气息。特别是当影片中的这些“离”与“合”又与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更相结合,其中所蕴涵的“物是人非”之感就更加容易深深打动观众的心怀。例如蔡楚生编导的《南国之春》这部影片,其前半部分极力铺陈南国春景之美和年轻人朝气蓬勃的快乐生活,当一对相恋的爱侣遽然在雨夜分别,从此天各一方,男主人公甚至远赴法国,然而当他摆脱羁绊,日夜兼程地赶来与恋人团聚时,昔日青春活泼的心上人却已经病入膏肓,在爱人的臂弯中长逝,此情此景不能不令观众洒泪。孙瑜导演的《天明》,菱菱和表哥本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家乡的贫困迫使他们远走上海,都市的罪恶打碎了纯洁的梦想,表哥只能离开菱菱去远洋货轮上工作,然而当已经参加北伐军的张表哥在码头与菱菱不期而遇的时候,她却已经在恶势力的逼迫下沦落为妓女!
虽然孙瑜以他特有的浪漫主义笔触把菱菱与张表哥的离合拍摄得美丽乐观和充满希望近乎不真实,但是一个天真无瑕的美丽少女噩梦般的遭遇却不能不引起观众内心深处的忧郁,特别是影片中那串象征着菱菱纯洁美好心灵的老菱串成的项链不时出现,与菱菱身处的黑暗社会和她的变化互相映衬,更令观众心生欷歔。由善于营造恐怖诡异氛围的马徐维邦导演的《秋海棠》同样不吝惜对主人公之间离合之情的浓墨重彩。吴玉琴和罗湘绮被军阀拆散,吴玉琴被毁容,带着女儿躲在乡下苦度凄楚岁月,后来父女二人流落上海,女儿梅宝为了给父亲治病,到酒楼卖唱与母亲巧遇,梅宝的一曲《罗成叫关》不仅对罗湘绮、而且对观众也产生了强大的情感冲击,因为这正是罗湘绮与吴玉琴定情时吴玉琴所唱之曲,然而当罗湘绮匆匆赶到吴玉琴的住处,昔日的恋人却已经从高楼跃下,躺在血泊之中,十几年的分离竟以如此凄厉的方式团聚,而且影片就此结束,对观众的感情冲击如闪电般有力和急速,这不能不说是马徐维邦的抒情特色。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中,当宋薇重返天云山,见到这片曾经见证她青春时期的美丽和爱情的土地,她的好朋友已经逝去,对于那个深藏于她内心深处的白马王子,她也只能远远凝视,历史和时间的距离隔开了一切,空留此情不再的浩叹。香港导演关锦鹏拍摄的《胭脂扣》中,当如花从阴间归来寻找她的陈十二少,不仅时代变了、故事空间变了,昔日英俊潇洒的十二少也已经垂垂老去、沦落不堪,影片中如花终于见到了十二少的那个镜头段落催人泪下:在暗蓝色影调所营造的清冷氛围中,如花决然离去,一个长长的全景镜头凝视着十二少在后面追赶的蹒跚身影,然后切换到他苍老不堪的面容。昔日的山盟海誓、如花玉人,眼前的背弃盟誓、猥琐老人,巨大的时空和情感差别对观众所造成的感情震荡可想而知。杨德昌的《一一》在把目光投向台北的一个普通家庭、默默关注家庭中每个人的细小生活遭遇的时候,重点表现了家中老人的逝去给他们带来的生命沉思。而中国电影悲欢离合叙事结构的故事情节设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巧合和偶遇,也与“情”有着密切的关系。诚如编着了多部才子佳人小说的烟水散人在《<合浦珠>自序》中所言“惟深于情,故奇于遇”,“自非情深千古,岂能事艳一时”[3,P367],可见,“情”是中国电影悲欢离合叙事结构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情”的牵引,所以才会有人的离合。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中李翘和黎小军竟然在美国街头巧遇,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并非绝无可能,但是毕竟微乎其微,影片中她们因“情”
而驻足,从而成就了这份机缘巧合。
事实上,中国电影人对其作品的“抒情性”有着明确和自觉的追求,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他们都在影片的抒情性上下了不少工夫。如张铮和黄建中两位导演在谈到《小花》时反复强调“它只是通过三兄妹的命运谱写了一首革命战争的抒情曲”[9,P70];“在小说传奇性的故事中,我们增加了这些兄妹之间、两个妹妹之间、母女之间相见而不相认的戏剧矛盾,都是为了突出影片的人情色彩”[9,P72];“影片中的‘情’成为很重要的表现手段。寓理于情,以情动人”[9,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