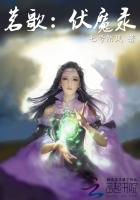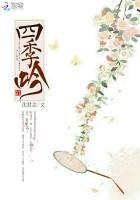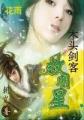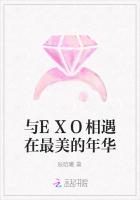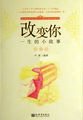犹太商人发迹的另一财源,就是人类的嘴巴。可以说,嘴巴是消耗的无底洞,地球上当今有50多亿个“无底洞”,其市场潜力非常的大。为此,犹太商人设法经营凡是能够经过嘴巴的商品,如粮店、食品店、鱼店、肉店、水果店、蔬菜店、餐厅、咖啡馆、酒吧、俱乐部等等,举不胜举。毫不夸张地说,只要能进入嘴巴的东西,他们都经营,因为这些行当都能赚钱。
犹太人认为,入口的东西要消化和排泄,一美元一只冰淇淋,10美元一份牛排,进入人的口几小时后,都会化作废物排泄掉。如此不断地循环消耗,新的需求不断产生,商人可以从经营中不断赚到钱。当然,经营食品不如经营女性用品见利快,为此犹太生意经中把女性商品列为“第一商品”,而把食品列为“第二商品”。而从事“第一商品”经营的犹太人比经营“第二商品”的多。犹太人自诩比华人更具有经商才干,依据就是华人经营“第二商品”者居多。
当然,任何一种生意,要想做好它,光生搬硬套生意常规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具有聪明的头脑和深邃的洞察力。“嘴巴”生意也不例外。下面的一个日本人经营肉馅面包生意取得成功的例子刚好证明了这一点。
该日本人是大阪人,现今有名的大富翁,也是日本肉馅面包店的创始人。20世纪70年代初,他与美国麦当劳公司合作,向日本人提供物美价廉的肉馅面包。
开始经营的时候,日本的商人都笑话他,认为在习惯于食大米的日本推销肉馅面包,无疑是自找死胡同钻,绝不可能有市场。但他不这么认为,他看到日本人体质弱,身材矮小,这可能同食大米有关,同时他又看到,美国的肉馅面包店的效应正向全世界发展。基于这两点,该日本商认为,同样是“嘴巴”的商品,在美国能畅销,在日本为什么不可能?再说,按照犹太人的观点,“嘴巴”生意绝对赚钱,只要经营得法,为什么不能获取利润?
凭着这些信念,该日本商的肉馅面包店开业了。不出所料,开业的第一天,顾客爆满,利润还大大超过该日本商原来想像的程度。以后利润日日升高,一连用坏了几台世界最先进的面包机器,还是满足不了顾客的消费要求,该日本商利用肉馅面包,即利用“嘴巴”生意发了大财!
直接靠女人赚钱,亦非歪道
女人和嘴巴作为消费者,作为顾客,也就是赚女人手里的钱和赚人们花在吃上的钱。而另有一些人,却直接将女人作为赚钱的手段,这或许有道德上的争议,但犹太人不拘于赚钱的方式,认为凡能赚钱者即为真智慧。况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经济学铁的规律就是有需求必有供给。上帝分人为男女各一半,女人对男人,当然有莫大的吸引力,这就蕴含着商机。
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社的创始人赫夫纳的发迹便是靠的“女人”这一商品。
赫夫纳生于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犹太小康之家。他从小聪明顽皮,不喜欢学习,是一个功课较差的学生。
1944年,赫夫纳中学毕业。时值二战,便响应政府号召欣然应征入伍。
1945年二战结束,赫夫纳复员回家。由于他持有军方的推荐信,按照政府的规定,他有权优先进入大学。大学期间,他读到了一篇当时轰动美国的关于女性性行为的文章,使他对该领域发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这成为他日后创办《花花公子》杂志的推动力之一。
大学毕业后,赫夫纳先后在芝加哥的一家漫画杂志和畅销杂志社工作过。但他老觉得自己做一名小小的记者未免有点大材小用,而且薪水也低,因此他来到总编辑的办公室,提出自己的要求:
“请总编每月给我增加40美元的薪水”。
“哼!像你这样的水平,值那么多钱吗?”
总编对这个自命不凡的小记者不屑一顾,不由自主地狠狠揶揄了他一番。
赫夫纳受辱后大为恼火,毅然辞职。
不想这辞职正使赫夫纳大展其才,他凭借以前在杂志社工作的经验,并且以他犀利的眼光洞悉出经营“女人”商品大有潜力,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向父亲和弟弟及银行贷款凑足1万元,创办了《花花公子》杂志。
赫夫纳深知,第一期杂志的成败与否是他关键的一环,头炮打响,他可以一鸣惊人;头炮打哑,杂志无人问津,他就很难再有资金去出版第二期。他精心策划第一期的内容,又以好莱坞性感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写真照片作为封面,同时在正文还插入了梦露的数页半裸照片。1953年11月,第一期《花花公子》上市了,赫夫纳本人做梦也没想到,一下子“洛阳纸贵”许多读者了为了一睹梦露的芳容,对《花花公子》形成抢购之势。这不仅使赫夫纳一直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而且使他大喜过望。
一个月后,赫夫纳就销售了5万多本杂志,并在第一次的印数上增加了近1倍的印数,这不仅使赫夫纳收回了全部投资,而且使他一夜成名,一下子成了闻名遐迩的老板。
最初,几期《花花公子》主要采用梦露及一些其他性感明星的写真照片作封面和插页,随着销售量的急剧增加(1954年的销售量已达到17.5万份),杂志社已经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于是,赫夫纳开始聘请模特儿拍照片,拿这些活生生的形象作为杂志新栏目的内容,彩色精印,令读者耳目一新。此外,为了扩大广告宣传,赫夫纳还在芝加哥及全国各地开设《花花公子》俱乐部,甄选貌美而性感的女郎化装成兔宝宝(Playboy),招摇过市,杂志销量再一次大增。
之后,《花花公子》还开设了一个叫“小家碧玉”的新栏目。这个栏目玉照上的女孩一律是纯情少女,杂志的销量再一次增加。
《花花公子》大肆登出许多性感明星的艳照,并同时为“性爱非罪恶”而疾呼后,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人们褒贬不一。但当《花花公子》在杂志上提出反对保守,支持堕胎合法化等许多新观点后,却获得社会一致赞扬,被誉为“开放”的象征。
现在,《花花公子》不但成了一本风靡全球的着名杂志,而且“花花公子”这个品牌也成了世界着名的品牌之一。
精于计算,锱铢必较
犹太人在商场上,绝对容不得模棱两可,马马虎虎。特别在商定有关价钱时,他们非常仔细,对于利润的一分一厘,他们计算得极其清楚。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旅行者的汽车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抛了锚,他自己修不好,有村民建议旅行者找村里的白铁匠看看。白铁匠是个犹太人,他打开发动机护盖,朝里看一眼,用小榔头朝发动机敲了一下——汽车开动了!
“共20元。”白铁匠不动声色地说。
“这么贵。”旅行者惊讶至极。
“敲一下,一元,知道敲到哪儿,19元,合计20元。”
由此可见犹太人的精明。只要他们认为该赚钱的地方他们一定会脸不红心不跳,不卑不亢地赚它回来。在长期的商场磨炼中,犹太人练就了闪电般迅速的心算能力。
某导游引导某犹太人参观一个电晶体收音机工厂,该犹太人目睹女工作业片刻后问到:“她们每小时的工资是多少?”
导游一边盘算着一边说:
“女工们平均薪水为25000元,每月工作日为25天,一天1000元,每天工作8小时,那么1000用8除,每小时125元,换算成美元是等于……”
花了两三分钟,那导游才计算出答案,可那位犹太人,听到月薪25000元后立即就说出“那么每小时35美金”。待工厂的一位负责人说出答案,他早已从女工人数与生产能力及原料等,算出生产每部电晶体收音机,自己能赚多少钱。
犹太人因为心算快,所以他们经常能做出迅速的判断,这使他们在谈判中镇定自若,步步紧逼,直至大获全胜;在商场上游刃有余、坦然从容。
对于犹太人来说,精于计算,是为了锱铢必较。他们不像大多数东方人一样,羞于“斤斤计较”。他们认为,该攫取的利润绝不应放手。他们既要计较得清,又能迅速地计算出结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是犹太人的聪明之处,也是他们善于做生意的诀窍之一。
使犹太商人得以精明并越来越精明,有诸多原因,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且独具犹太特性的因素,是犹太人包括犹太商人对精明本身的心态。
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都不乏精明之人,这是毫无疑义的。虽则相互比较起来自然还有个程度的不同,但对精明本身的态度却大不一样。
中国人不可谓不精明,能精明到发明“大智若愚”的程度,可以说精明已臻于极境,然而,正是从“大智”需要“若愚”可以反窥出在中国人的心态中,精明是一种适宜于在阴暗角落中生存的物种,中国人的典故中多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训诫,共同反映出“精明”在中国文化心态中多多少少有点像个丑角。而犹太人则不同,犹太人不但极为欣赏和器重推崇精明,而且是堂堂正正的欣赏、器重、推崇,就像他们对钱的心态一样。在犹太人的心目中,精明似乎也是一种自在之物,精明可以以“为精明而精明”的形式存在。这当然不是说,精明可以精明得没有实效,而是指除了实效之外,其他的价值尺度一般难以用来衡量精明,精明不需要低头垂首地在宗教或道德法庭上受审或听训斥。下面这则笑话可以说最为生动而集中地展现了犹太人的这种心态。
美国和苏联两国成功地进行了载人火箭飞行之后,德国、法国和以色列也联合拟订了月球旅行计划。火箭与太空舱都制造就绪,接下来就是挑选太空飞行员了。
工作人员先问德国应征人员,在什么待遇下才肯参加太空飞行。
“给我3000美元,我就干。”德国男子说:“1000美元留着自己用,1000美元给我妻子,还有1000美元用作购房基金。”
接下来又问法国应征者,他说:
“给我4000美元。1000美元归我自己,1000美元给我妻子,1000美元归还购房的贷款,还有1000美元给我的情人。”
以色列的应征者则说:
“5000美元我才干。1000美元给你,1000美元归我,其余的3000美元雇德国人开太空船!”
由这则笑话透露出来的犹太人的精明,用不着我们多说了,犹太人不须从事实务(开太空船)而只须摆弄数字,而且是金融数字就可以享有与高风险工作从事者同样的待遇,这正是犹太商人经营风格中最显着的特色之一。
令人意外的是,这不是其他民族对犹太人出格的精明的一种刻薄讽刺,而是犹太人自己发明的笑话。这里就大有文章了。
平心而论,犹太人这里并没有盘剥德国人,德国人仍然可以得到他开价的3000美元,至于是从有关委员会那里拿到的还是从犹太人那里拿到的,这在钱上面并反映不出来。至于犹太人自己的开价,既然允许他们自报,他报得高一些也无可非议,怎么安排纯属他个人的自由,就像法国人公然把妻子与情人经济上一视同仁一样。所以,在这则笑话中,犹太飞行员的精明又没有越出“合法”的界限。
而且说实话,仅就结果而言,任何一国的飞行员要处于这种“白拿1000美元”的位置上,都会感到满意的。但无论在笑话中还是现实生活中。他们都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甚至连想也不会想到,因为这种“过于直露的精明”在潜意识层次就被否定了:他们会为自己的精明而感到羞愧!
但从这则笑话本身来看,我们丝毫感觉不到犹太人有为自己精明得“过分”而羞愧的意思,只有一种得意,一种因为自己想出了如此精明甚至精明得无法实现的念头而“洋洋自得”的心情。至于是否“过于直露”这种考虑,丝毫不能影响他们的精明盘算,更不能影响他们对精明本身的欣赏。他们把精明完全看作一件堂堂正正,甚至值得大肆炫耀的东西!可以说,对精明自身的发展、发达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坦荡的态度更为关键、更为紧要了。犹太商人可以说就是在为自己卓有成效的精明开怀大笑声中,变得越来越精明的!
犹太民族的笑话大多都是精明的笑话,而现实生活中的犹太商人更多的是精明之人,而且还是同样对精明持这种坦荡无邪态度的精明之人。
旧上海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犹太富商哈同,他是来上海的犹太人中惟一由赤贫而至豪富的人,他的精明在上海也是妇孺皆知,几乎成了一种传说,还被看作犹太商人的典型。
哈同全名为雪拉斯·阿隆·哈同,又名欧司·爱·哈同,1851年出生于巴格达,1872年只身到香港谋生,于次年来到上海,其时衣衫褴褛囊中空空。他通过熟人介绍进入老沙逊洋行供职,先做守门人员,后当跑街(外勤),很快转任烟土仓库管理员和收租员。由于工作勤勉、头脑灵活,于1879年被提拔为大班协力兼管房地产部。1901年,他独立开办了哈同洋行,专门从事房地产,事业兴旺,最后于1931年去世。
哈同做生意时的精明以及他对精明的心态,从他计算地租房租上就可以看出来。
哈同出租一般住房和小块土地的租期都较短,通常3至5年。租期短,既便于在需要时可及时收回,又可以在每次续约时增加租金金额。在哈同的地皮上,哪怕摆个小摊子,也得交租。有个皮匠在哈同所有的弄堂口摆了个皮匠摊,每月也要付地租5元。哈同每次向他收地租时,总是很和蔼地对他说:“发财、发财。”但钱是一个不少的。
哈同计算收租的时间单位也与众不同。当时上海一般房地产业主按阳历月份收租,而哈同却以阴历月份订约计租。大家知道,阳历月份一般为30或31天,而阴历月份为29或30天,所以阴历每3年有1个闰月,5年再闰1个月,19年有7个闰月。所以,按阴历收租每3年可以多收1个月的租金,每5年可多收2个月的租金,而每19年可多收7个月的租金。
还有,哈同发达之后,曾花了70万两银元建造了当时上海滩上最大的私家花园,名之为“爱俪园”。为了便于管理园内职工,哈同对职工的职责和等级作了明确的规定,并让账房制作相应的徽章。但即使这样一个表明工作职责的徽章也要职工自己掏钱购买。每个徽章的制作成本仅为5个铜板,“零售价”却为4毛!
哈同的这种精明可说是已到了精明的极境,连每个月为29天还是30天都要算计一番。但反过来看,这样的精明固然需要一定的算计能力,但毕竟又用不了多少聪明,真正需要的恐怕还是一种心态,一种对于精明本身的心态。随便什么地方,不但要想方设法地精明,而且一旦有了精明的点子,便理直气壮地付诸实施,而不顾别人会怎样想。可以说,当时的同行会采用哈同收小租的办法而没有广泛采纳他按阴历计租的办法,既是一个不如哈同精明的表现,更是一个不具备哈同对精明的坦荡态度的表现:当其他民族的商人为了自己是否会显得过于精明而犹豫不决甚或将精明的点子搁置一边时,他们同犹太商人的距离就拉开了,他们在同犹太商人的交易中处下风的必然处境也就决定了。
灵活商规:生意场上无禁区犹太人素以清规戒律繁多而着称于世。犹太人对于他们的613条戒律充满自豪之感。对此,外人也许很不理解:“作茧自缚,还自豪些什么呀?”
其实,这多半出于对犹太人的不了解。在实际生活中犹太人相反倒比其他许多民族都要少受束缚。因为规则越多越详尽,某种意义上反而意味着可以明确不受限制的地方也越多。反过来,初看起来没有明确限制,但做起来动不动就触电,反倒令人更无所适从。所以,相比之下,犹太人反倒更加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商业活动中,就是犹太人做生意几乎没有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