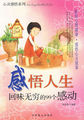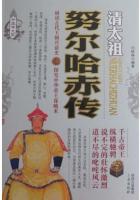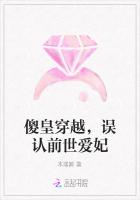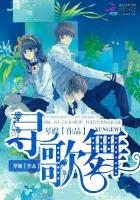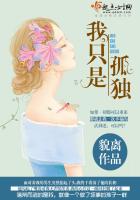至嘉靖二十九年,对吴维岳来说,刑部的酬唱已持续了八年。这一年,王学甫离开京城,吴维岳深情地写下《绎交四首道别王学甫》:“我狂子善恕,子直我弗嗔。数年胶投膝,乖分在兹晨。”写于同年的《送沈子由别湖广按察》说:“论交却忆并官时,登楼先酌看青酒。归院时弹赌墅棋,一时艺苑骈英豪。貌瘦休文堪调笑,此日惟余出送君。旧游星散谁能料,君行努力堪奇勋。”好友的离别使吴维岳黯然神伤,悲凉的言语里流溢着无限寂寞。次年春,吴维岳因审录江西狱事而离京,同他一起离京的有袁太冲、徐汝思和莫如忠,给他们送行的是谢榛、李攀龙和王世贞。同年,王宗沐也出任贵州提学副使。嘉靖二十九年前后,白云楼中世事苍狗。诗社的早期成员纷纷离京,星散江湖。但是旧人哭泣新人笑,刑部诗社的唱和依然如故,主盟文坛的换成了留下来的李攀龙和王世贞,诗社中的诗学思想也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革。
廖可斌先生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对这个诗社的新群体有着独到的洞见:“从嘉靖三十年到嘉靖三十一年春,是复古派诸子最集中最频繁的一段时光。凡休沐之暇,都在一起商榷唱和。不许有不同的主张,甚至不许有另外的交往。”对复古派兴起的时间及其结盟性质作出准确的论述。嘉靖二十九年,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余日德、张佳胤、魏裳进士及第,其中,宗臣、徐中行、梁有誉授职刑部,加入刑部诗社的酬唱活动。嘉靖三十一年,谢榛被招揽入社。谢榛《诗家直说》第八十五条作了如下记述:“嘉靖壬子春,予游部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计君延人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列坐于竹林之间,颜貌风神,皆得虎头之妙。”这一年春六月,梁有誉病归,诗社的几名骨干成员又倡为“五子诗”,“用以记一时交游之谊”,每个人各写“五子”,实际上共为六子。此后,由徐中行介绍,吴国伦也加入了诗社。七子之诗,遂擅名天下。虽然他们经历了谢榛被摒和梁有誉去世的事件,又在嘉靖三十四年前后补人余日德、张佳胤,复称“七子”。这个文学群体在嘉靖后期里虽然或隐或宦,聚散无常,却以其共同的文学领袖、统一的文学思想和严密的结盟性质,同声相应,经久不衰,从嘉靖末年到万历中叶成为笼罩文坛的文学主流。
嘉靖三十年前后,以吴维岳为代表的“白云楼社”发展为唯李攀龙马首是瞻的“后七子”,这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人事变动,而是一种诗文思想的转换和变革。
一般认为,在后七子结社以前,刑部的白楼诗社只是诗人燕宴酬唱的一个松散的群体,没有共同的纲领和诗学风尚,这无疑是未经考察的看法。前期的“白云楼社”同然未如“后七子”一样组成极为严密的社团,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群体特征和诗学趣味。从诗社成员的地望看,这个诗社大抵以吴地人为主,诗社早期的五个成员,除了张瀚是杭州人以外,其他四人籍贯都在吴中,后来加入酬唱的莫如忠、沈炼、袁履善和王世贞也都是吴人。虽然,地望并非他们结社的唯一原因,其他重要成员,如王宗沐是福建临海人,王崇古是山西蒲城人,然而,吴中文化的特质鲜明地体现在早期白云楼社的创作倾向与文学精神之中。吴人在文学写作上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六朝语人中唐调”,形成了崇尚清远明澹的写作风尚,这在四皇甫和华察、蔡汝楠等诗人的文学写作中有着显著的表现,也同样体现在“白云楼社”成员的文学思想中。张瀚是诗社的早期领袖。其《斸苓集序》说:
夫不局于艺,是谓通才;不滞于迹,是谓妙道。宜其汗漫江河。辉煌星日,胶轕寒暄,陶镕花鸟,绝无家居火食之气如此。是所谓本性情,该物理,自然之音,非夫探奇索异,猎声华亡。本实也。
其《明处士彬斋李君墓志铭》记载李君的语录说:
尝曰:诗本自然之声,亦有自然之节。本乎性情,随感而发,从心中律,审其疾徐,协于音调,信指合拍。其亟称高光州赠遗诸篇,谓俊逸有巧思。效法中唐矩镬,不爽分毫。余诗直率己见,澹薄无色相,详味其旨,若有妙悟。凡得于性灵,与其交游浸润,非必学力能然也。
一是本乎性情,一是自然之音,两者相为表里。“本性情”指直抒胸臆,随感而发,这与探奇索异、猎华亡实的写作全然不同。张瀚把这种文学思想化约为“非关学力”的“性灵”说,又将“直率己见”和“自然之音”结合起来,确然与讲究“性情之真”的吴中文学同声相应,却也似乎濡染着讲究“直写胸臆”的毗陵一派的文学气息。
吴维岳是“白云楼社”自始至终的中心人物,虽然其文集散佚不存,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序跋集录》里收存着他的《枫潭集序》,其言曰:
余既读懋卿集竞,言曰:甘受和,而五味之变不可胜尝,白受采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甘,天味也,白,天色也。用以成之而五,巧以杂之而成为变,愈变愈杂,愈杂愈下,未始有加于成也。由晋迄唐,沿于今日,诗凡几变,亦不可胜论矣。盖穷情组状,引物连类,钧深抉微,无不极其致焉。世人论诗,往往忘其性情心术而辄较体裁声调,定工拙之论,犹之口腻醇酸、目眩绮缛,以求所谓天味天色,安能识也!”
吴维岳是唐顺之的弟子,其“天味天色”说无疑是从唐顺之存乎至道的“天然真味”说直接推衍出来的。甘白之论,意味着文学书写应当任其质素而不劳文饰,表现性情心术的天然本色。唐顺之教人直写胸臆,他说:“六艺之学,先王所以寓精神心术之妙也”。又谓:“文字不论工拙,只要真精神透露”。吴维岳则批判世人“忘其性情心术,而辄较体裁声调,定工拙之论。”把抒写性情视为文字工拙的要件。他否定以“富于材积”为要件的文学写作,把“直写己意”的本色书写视为写作的源泉。其写于嘉靖二十二年的《田园十首并序》说:“昔鲁仲连欲以贫贱肆志,仲长统欲以清旷乐志,上之颜巷点沂,蒙园伊野,皆实以一身安止,至乐备焉,非有托而投也。嗣后。词赋家发摅隐佚之旨,吟纪林泉之迹,积架盈几,往往而嘉,若工部咏江村之画纸敲针事最实,右丞咏田园之落花啼鸟趣最闲,尤可咀含以理性情者。”要求在诗歌写作中表现“颜巷点沂,蒙园伊野”的性情之至乐。这种抒写性情的自得之乐与天然韵味,显然与张瀚“本乎性情”的“自然之音”有着相通的文学趣味。
朱彝尊《明诗综》里保存着陈羽伯的几则诗评。他评价金大车说:“子有诗学襄阳、随州,辞义兼美。”评金大舆说:“子坤诗清新秀朗。”评景呖诗说:“公诗直写性情,无论唐宋。”从“白云楼社”成员的文学旨趣看,张瀚的“直率己见”、吴维岳的“直写己意”和陈羽伯的“直写性情”及其对“清新”风格的认同,与“陶韦”一派的诗学倾向相契。值得注意的是,张瀚在《明处士彬斋李君墓志铭》里赞扬“效法中唐”的诗歌趣味,陈伯羽则提出“无论唐宋”的观念,彰显出他们对汉魏盛唐派的摒弃。“无论唐宋”的景汤与陈伯羽论诗,以为:“辞取达意。若惟以摹拟为工,尺尺寸寸,按古人之迹,务求肖似,何以达吾意乎?”“盖亦矫北地之蔽者。”杨慎在致陈伯羽的信里说:“学古而不蹈袭,以矫近日之蔽,良是。尝慨近日一二学古者,规规杜子美,不学其意而袭其句,是少陵之盗臣也。少陵称太白诗为‘清新俊逸’,岂日规规蹈袭哉!文章如日月,朝夕常见而光景常新,兹读佳什,有印鄙见矣。”可见,陈伯羽及其志趣相投的文人们,深渍于嘉靖前期“无用少陵”的文学风气。杨慎以来盛行的六朝、初唐诗风,原本就是对李梦阳“拆洗少陵”的反动,至嘉靖中叶,文学风尚发展为清新淡泊的中唐诗风,和唐顺之倡导的“洗尽铅华,独存本质”逐渐合流。这种趋向显然对提倡“直写性情”和“自然清新”的白云楼社影响甚著。然而,对于推崇“沉郁顿挫”的杜少陵、追随“雄豪亢硬”的李献吉的“后七子”来说,这却是“黜意象,凋精神,废风格”的堕落。
现存文献记载了吴维岳与李攀龙之间的两次冲突,有助于我们认识此期文学风尚的转移。一次是嘉靖三十年前,吴维岳与李攀龙争夺对王世贞的影响力,以吴维岳失败告终。嘉靖二十七年,王世贞授职刑部,参与白云楼社的唱和,并受到吴维岳的青睐。《列朝诗人小集》说:“峻伯在郎署,与濮州李伯承、天台王新甫攻诗,皆有时名。峻伯尤为同社所推重,谓得吴生片语,如照乘也。已而进王元美于社,实弟畜之。”这里关于吴维岳和王世贞的关系的说法是可靠的。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说到:“明年为刑部郎,同舍郎吴峻伯、王新甫、袁履善进余于社。吴时称前辈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尝不击节称善也。”考吴维岳《天目山房岁编》,吴维岳在嘉靖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春主盟白云楼社时,与王世贞、李攀龙同在刑部。在这期间存有大量赠答王世贞的唱和诗,却没有和李攀龙的酬唱之作。在《明诗评》“李君攀龙”条里,王世贞如是说:“于鳞折节与余好,居恒相勉戒:‘吾子自爱,吴人屈指高誉,达书不及子,子故非其中人也。’予愧而谢之。又尝慨然称:‘少陵氏千余年,李何廓而未化,天乎属何人哉!’”按照王世贞的说法,李攀龙在这段时间里“折节与余好”,并且以“子故非其中人”来说服王世贞与“吴人”的社群保持距离,引导王世贞走上学习“少陵氏”的文学道路。王世贞在《明诗评后叙》里说:“予为郎比部,郎之长孝丰吴维岳烨烨有一时誉,至同列相勉,得吴生片语如照乘云。予雅自好,不能吴生下,顾下李攀龙也。吴愕愕怡盛气欲夺我不得,乃悟而折节请正。”王世贞放弃吴维岳而追随李攀龙,这不仅仅是嘉靖三十年刑部人事变动的结果,其本身就是在吴中风尚和复古思想这两种文学思想间的选择。
身为吴人的王世贞对吴中文风深为不满。其《李氏山藏集序》说:“某吴人也,少尝从吴中人论诗,既而厌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闾而望,欢者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其《明诗评后叙》说:“吴人黄氏、皇甫氏者流若倚门之伎,施铅粉,强盼笑,而其志矜国色,犹然哉。”他又在《艺苑卮言》里批评陈伯羽为“如东市倡,慕青楼价,微傅粉泽,强工颦笑。”这代表了王世贞对吴中诗风的一般认识。两相对校,陈伯羽之流的诗歌写作,和六朝派的黄氏、皇甫氏原本就是“一丘之貉”。大约嘉靖三十一年,王世贞在写给李攀龙的信中如是说:
足下所讥弹晋江、毗陵二公,及其徒师称而人播此。盖逐影响,寻名迹,非能心睹其是也。破之者亦非必输攻而墨守,乃甚易易耳。吴下诸生则人人好褒扬其前辈,燥发所见,此等便足,衣食志满矣,亡与语汉以上者。其人与晋江、毗陵固殊趣,然均之能大骂献吉云:“献吉何能为,太史公、少陵氏为渠剽掠尽。一盗侠耳。”仆恚甚,乃又笑之,不与辨。呜呼!使少有藻伟之见可以饰其说,仆安能无辨也。“吴下诸生”的诗学不但趋向于“直写性情”,恐怕还不免有“人人好褒扬其前辈”,“均之能大骂献吉”的习气。王世贞认为,这些人虽然与晋江、毗陵有所不同,但是同样不能理解太史文章少陵诗的文学精神。
嘉靖三十七年,吴维岳出任山东提学副使时,欲造访家居历下的李攀龙,却被严词拒绝,再一次发生广为人知的冲突。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记载:
峻伯数使候,于鳞辄谢病不复见,余得交关其间。以谓于鳞。于鳞曰:“是膏肓者,有一毗陵在,而我之奈何。为我谢吴君,何渠能舍所学而从我。”峻伯不尽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谁肯为今者,且我曹何赖焉。我且衷之。”故峻伯卒而新都汪伯玉著状云:“济南以追古称作者,先生即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其独造盖有足多者。”所谓毗陵,则武进唐应德也。
吴维岳离京后,经过“后七子”的标榜和酬唱,李攀龙已俨然居于艺苑的领袖地位。这时,羽翼丰满的李攀龙断然拒绝了吴维岳的请见,其原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王世贞在《集序》里谈到吴维岳的写作倾向说:“诗必协情实调,声气盖庶几高蜀州、钱左司之遗,晚而稍务为严重,称贵体,至于才情之所发,亦不能尽掩也。其文尤善,缘本经术,中章程,往往庀材班、范,而步武于庐陵、南丰间,嗟乎!士得一当生,号名家言足矣。亡论毗陵,即峻伯不亦彬彬哉。”作为毗陵弟子的吴维岳,诗歌写作大抵吟咏性情,风格在盛唐与中唐之间,古文写作则宗示欧曾。根据汪道昆的判释,李攀龙“以追古称作者”,吴维岳“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师心”和“追古”的对立成为李攀龙拒斥吴维岳的全部理由。
无论如何,李攀龙固执而毫不妥协的态度令人惊讶,文学复古思想成为其接物择友的标准。在李攀龙主导复古思潮的嘉靖后期,后七子诗社通行着这样一些烙着李攀龙性格印记的思想观念:“舍所学而从我”,“能为献吉辈者,始能不为献吉”,并且不许诗社成员有“境外交”。这既是“后七子”诗社取得成功的组织保障,其实也是李攀龙和吴维岳、李先芳和谢榛等前辈诗人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李攀龙和吴维岳的诗学冲突只是受儒家心学影响的创作群体与复古派冲突的冰山一角,这种冲突随着复古思潮的壮大在不同层面不断地表现出来。
三、李攀龙和李先芳文学思想之比较
“白云楼社”延续着何景明、唐顺之一脉的诗学趣味,形成直写性情的清新诗风,其诗歌思想打上了吴中文化的印记。李攀龙与白云楼社的对立,只是复古思潮回澜的一种遭遇。王世贞说李攀龙“性孤介少善”,这种性格生成于其“九岁而孤”,与其母“影相吊也”的成长环境,但却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嘉靖二十年代里李攀龙的文学处境。在刑部这个文人荟萃的环境里,李攀龙似乎很长时间没有融入吴维岳、陈伯羽、王宗沐等人的文人圈子,独自举步维艰地走在自己的诗歌道路上。
从地望看,“白云楼社”基本是一个由吴中士人主导的文学群体,而作为山东人的李攀龙也有自己的小圈子。这个圈子才是孕育复古思潮的群体。据殷士儋所作的墓志铭,李攀龙嘉靖二十五年“还京师,聘充顺天府试同考试官,简拔多奇士;丁未,授刑部广东司主事,既曹务间寂,遂大肆力于文词。余时为检讨,日相引,上下其议论,而于鳞交一时胜流,若吴郡王元美数子,名乃藉甚公卿间矣。”殷士儋是李攀龙少时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之一,他们从小便培养了“复古”的志趣。《济南府志》说:“(李攀龙)稍长为诸生,与友人许邦才、殷士儋学为诗歌,已益厌训诂学,日读古书,里人共目为狂生。”嘉靖二十六年殷士儋进士及第,授翰林检讨,适逢李攀龙还京,遂能“日相引,上下其议论”。与他们唱和的还包括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李先芳、谢榛和王世贞。李先芳与王世贞、殷士儋同为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于慎行《李符卿墓志铭》说他“中丁未进士,时先生诗名已著,而不与馆选,识者惜之,乃与历下殷文庄公、李宪使于鳞,任城靳少宰、临清谢山人结社赋咏,相推第也。”根据于慎行的记载,在嘉靖二十六七年里,结社赋咏的至少有五个人,其中,除济南的李攀龙和殷士儋外,李先芳是山东濮州人,谢榛是山东临清人,靳学颜是山东济宁人。由此可知,嘉靖二十六年,李攀龙从顺天府同考归来,适逢李先芳、殷士儋进士及第,因而,二李、殷、谢、靳以同乡身份“上下议论”而“结社赋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