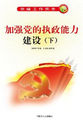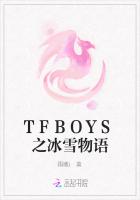“思想界”的国家意识
1920年代,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与混战,地方自治的思潮大张旗鼓。在地方军阀的支持下,省自治、联省自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正如杜赞奇指出的,在1920年代,充斥中国的政治方案是地方自治之“分权”,甚至远超过了要求统一的民族主义。①罗志田也指出,那是一个“五代式的民国”。②那时,联邦制、新的“封建”理想曾一度使新旧知识分子趋之若骛。不可否认的是,1920年代前期国家意识在知识分子中是相对薄弱的。
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统一的呼声逐渐占据了上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在长期的分裂后,又具备了统一的坚实基础。虽然国民党政权最初的势力范围不过局限在江浙及其周围几个省,但是它体现出了统一全国的决心和实力。在此背景下,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的诉求,在思想界逐渐成为主流。③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难”危机,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思想界的国家意识,探讨193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状况,国家意识的提升(从理性与感性两个方面来说④),是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
一、从“个体”到“国家”:时代意识的转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时代变了,所面对的问题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对时代问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努力把握时代变动的脉搏,并且把时代的问题转化为自己的思考对象。同时那些曾经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也自然是带着个人的选择以及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引发对时代问题的思索。因此,我们可以从那些著名思想家的问题意识和知识结构出发,来探讨思想界所关注的时代问题的变化。
1930年代思想界“国家”意识的提升,我们可以从那些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时代问题的变化中窥见一斑。下面就以《独立评论》的胡适和《再生》的张君劢为代表,来讨论时代意识的转向。⑤
胡适在1920年代曾积极介入政治,呼吁“好人政府”,然而残酷的现实,使胡适不得不最终远离政治。转而办《新月》的胡适,寄望于文艺与学术的努力,“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点体魄”,这个时代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但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欠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⑥因政治上的失败而对现实失望,悲观的情绪由此而发。但由政治而转向文艺,并不意味着胡适彻底放弃了对政治的关怀,《新月》最初确实是一份文艺的期刊,但是残酷的政治现实使他不得不站出来说话。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国民党推行“清党”,并趁此机会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的政策,大肆逮捕和审判所谓的“政治犯”,从而使得个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使得胡适等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个体的生存权利和自由的问题。胡适和罗隆基等人先后在《新月》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评国民党的政策,从而引发了国民党的口诛笔伐。胡适等人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为《人权论集》而出版,于是遭到国民党各地党部的“围剿”,《新月》杂志因此被没收,《人权论集》被查禁。罗隆基因为抨击国民党,结果遭到逮捕。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由上海北上北平。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以及随之日益迫近的“国难”危机,是胡适思考时代问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据蒋廷黻回忆,当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常常在饭后聚集在北院七号叶企荪和陈岱荪的家里,讨论和战的问题。在清华俱乐部组织的一次聚会上,蒋廷黻提出希望能够创办一个刊物,系统地讨论中国的问题,当时在场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等人,后来又经过几次的聚会、讨论,最终选定了胡适拟订的刊名——这便是《独立评论》的创办过程。⑦
由于“国难”危机,胡适已经开始自觉地由《新月》时期对“人权”问题的探讨,而更多地转向了对“国家”问题的关注。如何“建国”成为了《独立评论》讨论的中心话题。1932年2月,独立社聚餐,讨论“怎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认为应该努力做到实质上的统一,推行“法治”,停止内战。对于政权的分配,大家的意见也普遍认为,应取消“党内无派”,使国民党分化成政党;应取消“党外无党”,使国民党以外能有政党发生;但又承认国民党的专政,是事实上不能避免的。⑧此后在《独立评论》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大体都围绕这些基本的观点展开。“人权与约法”的争论,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呐喊,而对于中国出路问题的关注,则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胡适对国家意识和秩序建构的思考。个体自由的追求和对保障人权的呼吁,需要激情的力量和批判当局的勇气;而“国难”之际民族前途的探索,则需要理性的思考和对当局一定程度的支持与理解。1933年2月,身为“民权保障同盟”成员的胡适在《独立评论》撰文,认为民权保障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并强调一个政府有权力镇压这样的反抗活动。⑨这导致后来胡适被开除出民权保障同盟。由此可见,胡适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有了根本的改变。
随着胡适所关注的问题的转变,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发生了转机。从《新月》时期的“反党分子”,胡适一变而成为蒋、汪的座上嘉宾。1933年3月,胡适偕翁文灏、丁文江赴保定与蒋会面并讨论内政和外交的问题。⑩而胡适与汪精卫则保持了更为密切的书信往来,在胡适给汪精卫的回信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批评还是建议,胡适的口吻都十分直接。胡适多次婉拒了汪精卫的邀请,不愿意加入政府,“我细细想过,我终坚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并表示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此种诤臣、诤友的角色,正是从国家的立场出发,而为政府贡献力量。
1930年代,张君劢所关注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张君劢曾经强调,他的政治思想是英国的,而哲学思想则是德国的。1920年代后期,当时在上海的张氏对英国的“费边社”政治理论很感兴趣,尤其是对拉斯基的著作大力鼓吹。他以“张士林”的笔名翻译了拉斯基的名著《政治典范》,在该书的序言中,他介绍拉斯基的学说:
一时代之政象,有其一时代之学说为之后先疏附。以陆克之《民政论》为十七世纪英国政治之代表,以边沁之《政治零拾》与穆勒之《自由论》、《代议政治论》为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政治之代表,则现在之政论家可以代表英国者,舍菲滨协会之槐伯夫妇,工党之麦克洞纳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之柯尔氏,与新进学者之赖斯基氏外,无可他求矣。我所以独好赖氏者,槐氏等专为政治上一种主义鼓吹,而赖氏于政治学有全系统之说明,故继承陆克边沁穆勒之正统者,殆赖氏矣乎。
这里,张君劢以拉斯基为继承洛克、边沁、穆勒之英国政治学的正统,评价很高。其时,拉氏刚刚崭露头角,属于“新进之学”,张氏的这一番赞誉,代表了他对英国政治学的认可,同时也说明张氏力图将拉氏放在英国自由主义的谱系中加以肯定。我们知道,以洛克、边沁、穆勒等人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今天一般归为古典自由主义流派之列),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认为应该尽量缩小国家的权力,以保障个人的充分自由,斯宾塞甚至认为应该将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因此,站在个体的立场强调对国家权力的制限,是英国政治学的一脉之承,从这一点来看,拉斯基确实继承了英国政治学的传统。
20世纪的20、30年代,对“国家权力”的制限体现为一种“主权多元论”的观点。其时,在英国学者中间,颇有一些否定主权由国家独占的看法,拉斯基早期的理论也主要反对国家为当然的主权者的“一元论”倾向。拉斯基说,“国家的意志不偏向于一个方向,假定国家是一个把各项要求使之生效的组织,那末国家所遭到的力量,益是平均分配,国家对答的总合益加大。”也就是说,国家意志不是绝对的,一国之内还存在许许多多的意志力,国家只是表现为各种力的总合罢了。《政治典范》一书的出发点,就在于澄清现实中国家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它究竟是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还是残害个人自由的工具?拉斯基不同意将国家神圣化为十全十美,显然针对的是德国哲学的一般看法,而是认为国家应该是满足人民欲望的工具。一国之道德上胜任不胜任的标准,即在于它是否能满足人民的欲望。因此拉斯基在该书(《政治典范》)中的“自由主义”立场非常明确。但是此后他的立场有了一定的转变:
拉氏早年的著作,都是专为攻击主权论而做的,所以都以主权论为名;《政治典范》(GrammarofPolitics)一书,则集合各派的长处,而自成一个系统,以个人道德为政治的鹄的,以权利为自我发展的条件,而认为国家之基础在保障人民之权利,……(因此)《政治典范》一书中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现代国家中之自由》一书,则进一步把自由的意义,加以发挥,《在危机中之民主政治》一书中,思想渐渐转变了,今年(1935年)出版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更可见出拉氏的思想中,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消长了。
《政治典范》不仅是拉斯基的成名之作,而且是其思想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可以说,此前的拉斯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拉斯基,他反对当时世界范围内国家权力绝对化的普遍现象。因此对于拉斯基的认可,说明张君劢1920年代末,更多关注的是“个体自由”,而到了1930年代,张君劢组织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时,他的思想资源已经由英国的政治学而变为德国的哲学了,他关心的问题也已经变为如何造就一个近世的中国。
张君劢指出,“中国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变成一个近世国家”,所以他提倡一种“造国”(MakingofNation)运动。张君劢在国家社会党的纲领和他1930年代写的书中,一再强调了“民族—国家”本位的基本立场,他的研究兴趣也转向了“国家哲学”。1938年出版的系统阐述他的“造国”主张的书名就叫《立国之道》。张君劢认为,“民族国家”应该是唯一正确的立场,“我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而且认为民族立场符合民众的“公意”,“我们说以民族为立场乃是注重民众心坎中的真正要求”,“中国前途的一线出路亦就在于这个有民族自觉心的民众”。不是以国家为个体欲望满足的工具,而是要求个体以国家为归宿的一体自觉,显然已经是对拉斯基在《政治典范》中的“个体”本位的否定了。而张君劢无疑也反对“主权多元”的观点。柯尔和拉斯基等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家,都认为主权不应该由国家独断,国内的各种团体和社会组织都是具有意志力的实体,因而它们也应该拥有主权。1930年代,张君劢反对“主权”的分割,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抨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马克思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截断国家的主权,而不是以民族国家为最终归宿:
马克思想以阶级作大的横断而有以打破民族国家的纵断,实是一种迷梦。实际上已经屡次试验了。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即以苏俄论,他的成功处不在阶级斗争的国家化,却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
以某一团体或者某一阶级为基础,都是否定国家本位的。在张氏看来,这阻碍了国家对内成为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实体。国家本位对外则体现为与“世界主义”之争斗,张君劢认为国家本位必然是最后的胜利者。抗战胜利后,他说:
俄国革命之初,共产党认为非将各国现有政府推翻,全世界共产主义无法实现。如德、意的专政和匈牙利的暴动,都是世界主义的表现。但德国和意大利都从民族本位做出发点来刺激国内人民反对共产主义,同时俄国一九二八年史太林第一五年计划颁布后,他觉得世界革命无希望,故标榜一国本位之社会主义的建设。中间经托劳斯几与斯太林的斗争,实即世界革命派与国家本位派之胜败所系。
俄国初时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行世界革命之实质,而在斯大林之后转向民族主义和国家本位,不再以世界革命相号召,以张氏看来,更能说明国家本位为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趋向。
总之,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思想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关心的问题,大体上都由“个人主义”的立场而转变为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并且以国家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下面我们分别来讨论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具体看法。
二、“国难”危机与国家意识的增强
“九一八”事变对于知识分子和思想界“国家意识”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九一八”以及随着而来的“一二八”上海的战事,打破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社会秩序,一时间“国难”危机的呼声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国民党政府召开了“国难会议”,思想界也开始纷纷思考解决国难危机的办法,整个国家的忧患意识陡然提升。傅斯年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强调了“九一八”的影响力,“‘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机,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两件自然一个是世界大战,一个是俄国革命。”将“九一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相提并论,足见“九一八”日本的入侵对于知识分子的巨大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