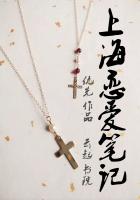“九一八”使得中国丧失了东北的领土,“一二八”上海的战事,更是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1930年代初国民党还没能完成中国的统一。1930年蒋冯阎还正在打内战,国民党统治势力所及只是江浙及其周围省份,尤其上海是南京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丁文江就指出,“‘九一八’以前,中央能自由运用的款项每月不到三千万。上海的事件(二十一年一月一二日)一发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就落到二百万,当时凡有靠中央接济的机关,立时等于停顿。军队的饷项就没有着落。”财政的困窘首先影响的就是军事开支,以及教育经费的拨给,此后纷纷兴起的学潮很多都和教育经费的支绌有关。程其保曾言及战事对上海教育界的影响,“自暴日入寇,沪滨生命财产损失固无从计,而最可痛心者即教育文化机构之摧残。计公私立之大学及专科学校直接受害者约十校,大学生因而失学者约一万一千人之上。”上海当时还不是教育界的重心,北平才是教育的重镇,当时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几乎都集中在北平,而北平正处在“国难”危机的最前线,大批的知识分子都切身体会到兵临城下的感觉。翁文灏在1932年指出,“近来大家感觉平津有被侵略的危险”,进而担心如何保存北平的文物和建筑,虽然他认为在此危机之下,知识界仍然要“做一天工算尽一天责”,然而也需要作好牺牲的准备。可见东北失陷对于平津无异于唇亡齿寒。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其影响,《独立》群体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其中颇有一些人将“国难”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胡适认为,“‘九一八’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他不过是五六十年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一个危险局面的一个爆发点。这座火山的爆发已经不止一次了。”他将“九一八”与日本以及俄国历次对中国的侵略相联系。同时胡适强调了日本的入侵与中国的自救运动的起伏之间的关系,认为每一次危机的爆发同时也直接间接地刺激了中国的革命。将“九一八”事件放在远东中、日、俄三国数十年来的外交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胡适多少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傅斯年对于“九一八”的观察分为浅层次和深层次两个角度,他虽然认为从浅的层面看无疑应该表示悲观,而从深入的层次看来,却不得不对中国的前途持乐观的态度,“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国民的品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傅斯年从长远的历史眼光出发强调,“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中国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民族的这种生存能力在危机关头体现得更为突出。最后他转向了现实政治,“所以没有办法者,只是政治,而政治之所以没有办法是没有政治的重心……一有政治重心,中国是能有大组织的。”在这里,放长历史的眼光,实际上就是试图将日本入侵的突发事件,作为思考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契机。
于是,日本入侵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的内政问题。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入侵恰好成为了中华民族是否有能力存活于世界的试金石。国联的调查报告是为调解东北问题的,不过它对中国内政的判断显然对于当时知识分子更具触动。《国联报告》以相当的篇幅论证了东北属于中国的主权,然而报告关于中国内政的部分,留给知识分子普遍的印象是:中国还不具备一个近世国家的资格,于是才有将东北交予国际共管的提议。
思想界对国联提议的反响颇有分歧。比如《独立评论》内部的胡适和蒋廷黻就认为“国际共管”是可以接受的,而《再生》和《时代公论》的成员则大多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国际共管”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不过大家都承认“国联”对中国之不成国家的判断是准确的。在胡适和蒋廷黻看来,正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因此需要“国联”这个代表世界公正的组织的帮助,因此胡适对国联的调查举动表示欢迎,并认为此举体现了“国际的中国”之资格。而张君劢也指出,“中国尚未具实际上之国际人格(军事的,非法律的),军力不足与人比较,财政不足以图远大,虽欲与人联合,而人视为决无可取。有外交问题生,皆人之助我,此种外交自为偏(片)面的乞怜的。”张君劢抨击了外交上的依赖心理。他认为不论是亲英美还是亲日本,于中国都没有益处,因为中国缺乏近世国家的一些基本要素,体现在外交上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国策,而专靠依赖外国势力于世界各国中讨生活。对于中国外交无出路,是源于中国还不成其为一个国家,杨公达的观察最为独到:中国的政客们不过满足于把外交当作方法,于是便出现了亲日还是亲英美,抵抗还是妥协的纷争。然而他指出,无论“亲日”还是“亲英美”,都非外交长久之策,“亲日的代价,最高限度,不过求得一刹那的苟安,绝对的亲英美,也只能得现时的经济上奥援,不可视作永久的打算”。现代国家的外交首先必须是“自主外交”,“‘自主外交’的首要条件在决定外交国策”,“外交国策,本诸时间性和空间性决定的,不得因人而更易,尤不得因个人的特殊目的而更易。如今的外交,只有方术,而无国策。”这种外交无非是中国传统的“术”的应用,而非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外交。因此,外交政策的检讨,最终仍归结到中国是否有资格成为一个世界承认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不幸的是,日本否认侵略事实的言论,正与国联报告对中国政治的判断如出一辙。日本提交“国联”的意见书中指出,“中国者,乃曾成为统一的国家之现在之广大地域之名称也”,进而为其侵略辩护,“夫领土不可侵之原则,虽应神圣视之,而在无政府之国家则不适用,盖以已陷于无政府状态之国,已不成为国家故也。”对于“无政府”的国家,则一切现代国家间的基本原则全不适用,而“中国”不过是广大地域的名称罢了。这种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情感和理智两方面的刺激可谓深切而剧烈。中国遭遇“国难”的种种不幸,最后都归结于中国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1930年代外国学者、专家从局外人的角度对中国政治进行了观察,他们大都承认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但没有建立起现代国家。英国政治学家陶鼐对东北问题发表看法:
东三省的命运最后不会在东京和日内瓦,是要在关内的中国决定的。因为东三省论文化和民族完全是中国的。如果日本能割据东三省,那必是因为日本能使用一个有组织的国家的种种力量而中国不能。如果中国也能,那末,东三省一定要受中国的吸力,不受日本的吸力。一句话,就东三省论,中国本可拖延,只要——这是很要紧的——在拖延的时候,中国能够得到内部的安定和团结。
以陶鼐的看法,东北毫无疑问从民族文化的归属上应该属于中国,然而中国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才能真正收复失地。最后东北的命运实际上全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从长远来看,即要使得中国经过长期的发展,而成为有竞争力的国家。胡适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谨慎乐观,以及傅斯年深层次角度对复兴民族的信心,都是看到了中国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段的努力能够建立国家的政治出路。正如格里德指出的,“胡适认为,30年代的中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危险并不是日本侵略的威胁。相反,他所焦虑的是,中国人可能会采取的将会把过去几十年的物质和思想成就毁灭掉的抵抗方式。”国人必须从理性上认识到“建国”的长期性,而不能以短浅的目光而阻碍了中国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点点滴滴的进步,这是《独立》全体一再强调的主题。丁文江在提及青年在国难之际的责任时,不同意青年贸然赴死地牺牲自己,而是要求青年立足于建立国家的长远目标,也正与胡适的主张相合:
今天青年的责任是什么?青年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要十二分的努力,彻底的了解近代中国的需要,养成功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了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功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抵抗日本,收复失地,一定要到中国能有战胜日本力量的那一天,才会得成为事实。要中国能有那一天,一定要彻底改造一个新式的中国。做这种改造新国家的预备工作,是今天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唯一的责任!
“九一八”以后的几年中,国人对于“国难”大多持悲观的论调,但是一些有识之士却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思想界的“国家”意识不断增强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塘沽协定》签订之际,即使在“中日亲善”甚嚣尘上之际,举国对于外交大多感到失望的时候,胡适等知识分子仍然坚信“国家”意识的增强必然使中国走向复兴。1934年的“双十节”,在举国一片悲观的氛围中,胡适也不忘“唱一些高调”,他总结了民国以来中国在教育、社会改革方面的进步,“明白承认了这二十年努力的成绩,这可以打破我们的悲观,鼓励我们的前进”。而作为《大公报》主笔的王芸生也在1937年的文章中写到这一段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
记得在二十四年夏天《何梅协定》之后,我悲愤极了……在那时期中,我给南方一位老朋友写信,无意中说了一句最悲愤的话,‘尚冀及身的见国运之转隆’,不料他回信说我‘其志尚壮’,说他自己‘而今祈望能以中华民国国民了此残生’。我在那篇文章中表现的却没他这样悲观,对于中日问题的认识,眼光放远大些,我始终是乐观的。我在许多篇文章中,一贯的指出九一八以来的结果,是唤起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相反的,日本人在道德方面确实堕落了。
“国家意识”的增强,确实起到了支持知识分子的心态在“国难”之际乐观向上的作用。正如王芸生指出的,“九一八”成为促使中国“国家”意识提升的关键。
三、“建国”:“现代化”与理性制度
1933年7月号的《〈申报〉月刊》上,刊登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系列讨论。陶孟和、诸青来、郑学稼等知名学者,分别从教育、实业、农业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方式、条件等多个角度,对现代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思考。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促进现代化需要哪些条件;其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采取什么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以及实现的具体步骤如何。应该说这次对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还是比较深入的,其目的正在唤醒民众对经济残破现状及其救治办法的认识,“事实上,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面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的整个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不过,参与讨论的学者大都认为,只要把握住“现代化”的方向,中国的全面落后就有望一步步地改变。虽然,其讨论的重点在经济和军事,但是现代化也可以说是一项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事业。胡适就指出,“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国家的建立,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同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每一项具体问题的解决,又必然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完善。胡适对这次“现代化”的讨论大加赞赏,“‘现代化’也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明白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使他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立脚,可以安稳过日子。’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因此,“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解决各种问题以建立现代国家(即“建国”)。
以胡适的看法,“建设”中取得的点点滴滴的进步,都应该使民众对国家充满信心。“建设”的成绩可以成为结合民众力量的黏合剂。他对中国政治的任何一点进步都大加赞誉:1932年5月,上海工商界组织了“废止内战大同盟”,胡适高兴地指出,“这正是中国政治具体化的一个好现象”,体现了经济界的政治觉悟,相信就此可以造成一种“道德的制裁力”。1934年底,蒋汪通电,对国事的基本原则发表声明,胡适对于其中提到保障人民以及社会团体的“言论结社之自由”,表示欢迎。他似乎认为,中国只要认清了整个国家努力的方向,并且不为其他的歧出因素所干扰,就会在建国的道路上不断地前进,这种点滴的进步又足以造成民众信仰的向心力。这种看法,自然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观念相关,整个社会的进步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人为的主观努力只能体现为对社会进程洞察基础上的“改良”,而不是彻底地改变社会结构的“革命”。胡适认为,一切的创新和进步,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的,因此,从已有传统中所获成就出发,才能有不断的进步。而已经取得的成就,也自然为继续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使得胡适对社会进步持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