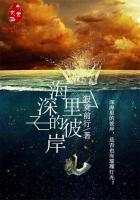当然,胡适的乐观建立在整个国家必须有一种团结的机制,也就是他所谓的“社会的重心”。中国的种种病源之无从下手,在于有一大困难,“这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中国政治出路就在于社会重心之创造,“既然没有天然的重心,所以只可以用人功创造一个出来。”“社会重心”的造就将有助于中国各种问题的逐渐解决。以傅斯年的看法,中国首先应该有一个中央政府,“所以好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的,最可怕者,是中国此时大有没有政府的可能”,而“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因此,他主张以国民党为团结的中心。翁文灏显然认为对中央的服从应该是不证自明的,主张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该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傅、翁两人是以权力的实际归属为社会力量服从的依据,而未曾考虑人们服从权力的原因,也就是权力背后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胡适的考虑则进一层,他固然同意建立一个中央,但是认为人们服从中央不是因为它握有权力,而是因为它是民众信仰的“权威”。1932年底,在长沙的一次讲演中,胡适指出:
今日的出路:1努力造成一个重心:国民党若能了解他的使命,努力作到这一点,我祝他成功。否则又得浪费一二十年重觅一个重心;
2努力建设一些可以维系全国人心的制度:如国会制度,如考试制度;
3建立一种建设的哲学,“知难行易”是革命的哲学,不适于建设。建设的哲学要人人知道“知难,行亦不易”。明乎此,然后可望有专家政治。
这里,胡适自然是要求由国民党主导造就一个“社会的重心”,但是用来维系民众信仰的必须是一整套现代的理性化的制度,即国会制度、考试制度,以及专家政治等。即以宪政而论,胡适认为,一切现代国家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宪政之上,宪政是一切政治得以开展的基础:
第一,我们要明白宪政和议会政治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方式,不是资本主义所能专有……
第二,议会政治与宪政不是反对“民生”的东西……
第三,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办法。
显然,宪政是进入现代国家的基本条件,宪政可以包容其他的各种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的、独裁专制的、统制经济的等等)。胡适不象许多将民主理想化的知识分子那样,认为民主制度是多么崇高的价值理想,毋宁说他倡导宪政正是因为它是最便利的改造中国政治的工具。宪政是可以获得政府“合法性”的有效的政治符号。在胡适看来,宣布宪政本身,就意味着整个国家走向政治轨道的开始,这在政治还未能上轨道的中国,诚然是可以具备号召力的、足以造成民众信仰的“重心”了。同时,反对“知难行易”说,胡适意在破除国民党的革命思维。以“建设”的眼光来看,“知”固然要紧,但是“行”的意义则更重要。胡适号召人们不断地努力工作,“建设”当然是“干出来”的。
蒋廷黻指出,“我们的出路,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设,所谓建设就是物质的和制度的创造与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在1930年代,“建设”已经成为了动员各个阶层力量的有效的政治符号,“苦干”、“实干”等政治口号确实取得了对内维系民心的作用。而蒋廷黻认为“建设”更应该是博得国际同情的条件,“在最近几年之内,我们外交活动的能力及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半要靠我们建设的成绩”,“我们以后要引起国际的同情也不在乎我们对日的强硬态度,而在乎我们建设的成绩”。但是他感觉建设的号召力有所减弱,“三四年以前,全国几是一致的笃信建设。最近风气似乎又转了,由笃信以至于怀疑、反对,建设的前途大有堵塞的可能。”以合理的制度来结合民心,就必须使民众看到制度的有效性,因此“建设”的成绩一旦不理想,就会引起民众的怀疑。蒋也承认“人民对建设的反感由于以往的成绩不良”,但是他相信通过一定的调整,可以使得民众重获对国家的信心。
附论:个体主义与国家意识
学界一般都把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这里有必要考察1930年代胡适对于国家和自由关系的基本看法,从而更好地考察中国自由主义的特点。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胡适主要宣扬的是个体主义,他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要求塑造一种“易卜生主义”式的人格理想,即强调个体的创造力和独立特行的人格。但是到了1930年代,他却更关注世界范围内“国家意识”的增强。胡适说:
试看这四年的国难之下,国家意识越增高,党派的意识就越降低,这不单是中国一国的现象,世界各国(包括德意志)的‘全国政府’的倾向也是有同样的意义。有远识的政治家应该抓住这种大趋势,公开地建立‘国家高于一切’的意识,造成全国家的、超党派的政治。
他对世界范围内集中权力于国家的现象加以肯定,认为最终可以实现一种“无党”的政治,“况且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如果真能逐渐实行,也可以防止政党政治的流弊,依我个人的看法,五权宪法的精神是‘无党政治’的精神。”“五权宪法”是否能够造成“无党政治”,消除政党的竞争是否真的可行,暂且不论。然而以“多党竞争”才能保证权力不为一种势力所垄断,这是自由主义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此时的胡适无疑认为政党竞争影响了“国家高于一切”的意识。
诚然,1930年代胡适也仍然坚持着他的“个人主义”的人格理想。他赞同张奚若对“个人主义”哲学的宣传。胡适在“‘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仍然不忘纪念“五四”,阐发“五四”自由主义的精神。他认为“五四”的意义,“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人们应该培养“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认为易卜生就最能代表这种健全的人格理想,一方面他要求发展个人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求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个人主义的人格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因此人们应该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一个伟大时代的造就,往往伴随着一批具有自由独立人格的伟大人物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个新社会的进步也必须依靠一批自由的人们,那么要建立现代的中国,就必须先使得国民成为自由的个体。
在这里,胡适把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培养自由精神的“人生观”和价值理想,似乎与一般理解的“政治自由”(Liberty)有所区别,反倒更接近于“精神自由”(Freedom)。因此,胡适才对自由得以实现的许多外在条件,比如如何制约权力,重视得不够。
不过,胡适坚决反对张奚若将“五四”同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相提并论。他指出,“‘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狭义的民族运动体现为盲目排外的情绪,而不是对于国家民族问题的理性思考,他指出民族主义至少有三个层面:
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走上前面的两步。
国民革命由于输入了苏俄的党纪律,而表现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因此在胡适看来,距离“五四”自由主义的精神相去甚远。他将“济南惨案”之后,以及“九一八”以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均视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在他看来,党纪律抑制了个人主义精神,而无法造就理性的民族主义。
如前所述,胡适的民族主义首先体现为一种开放的态度,在否认中国是所谓“黄金世界”的同时,他要求输入西方自由的人格理想,以“充分世界化”的心态努力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这种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以“建国”为最终依归,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建立现代国家秩序的破坏。在这里,个人主义的自由精神的创造力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很好地结合为一体,造成了胡适思想的两面。这也使得他可以从个人主义的宣传直接跨越到国家意识的构建,而缺乏了自由主义理论所需要的建构一种共营的社会制度的层面。
四、“造国”:塑造政治的“共同体”
《再生》群体关心的是如何将国家塑造为一种政治的“共同体”。如果说,《独立》把国家看作一个“机器”(machine),而注重国家制度的“合理化”的话,那么《再生》则倾向于把国家看作一个“有机体”(organism),而注重建立国家的道德基础。与《独立评论》群体有所不同,《再生》在1930年代主要关注于国家学说的普及,以及如何建立国家的道德基础。
1“国家主义”哲学的倡导
要造就一个近世的国家,首先必须从理性认识“国家”为何物,而这一思想的资源为中国传统中所缺乏的。张君劢认为中西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国家”思想之有无:
东西政治思想之异同,可以一语别之:曰东方无国家团体观念而西方有国家团体观念是矣。唯以团体观念为本,然后知国家为一体,其全体之表示曰总意,全团体号令所自出曰主权,更有政权之活动方式曰政体,与夫本于团体目的之施为曰行政;反之,其无团体观念者,但知有国中之各种因素,如所谓土地、人民、政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矣。东方唯无团体观念,故数千年来儒、道、法、墨各家政治思想之内容,不外两点:曰治术,所以治民之方术也;曰行政,兵刑、铨选、赋税之条例而已。
以有无“团体观念”为中西政治思想之根本区别,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只是,梁启超以是否能够“合群”来比较中西文化之不同。在梁启超看来,“群”是一种社会有机体的理想模型。“有机体”的原理在,作为组织成分的个体,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系,使整体具有了比各个组成部分简单之和更大的功能。梁启超对于西方“国家学说”的引介,也是不遗余力,他在《清议报》上连续刊登了介绍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文章。1930年代,介绍西方理论的知识分子也大多从德国思想家那里获取思想资源,张君劢指出了他介绍费希特的缘由:
有人于‘国难期中应读何书’之标题下,首列黑格尔氏之大论理学两部,黑格尔书名曰论理学,与若国难风马牛之不相及。数千年之历史中,大声疾呼于敌兵压境之际,列举国民之受病患,而告以今后自救之法,如菲希德(即费希特)氏之《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可谓人间正气之文字也。菲氏目的在提高德民族之自信心,文中多夸奖德人之语,……呜呼,菲氏之言既已药亡国破家之德国而大牧其效矣。吾国人诚有意于求苦口之良药,其在斯乎。
费希特所处之时代,德意志尚在四分五裂,又逢敌兵压境、内忧外患,颇与中国“九一八”后“国难”之情形相似,因此费希特“提高德民族之自信心”的国民讲演,便成为了“国难”之际挽救“亡国破家”之命运的良药了。不只是张君劢,国内有识之士大多极力推崇费希特的学说,一时间费氏的《国民讲演》不胫而走,成为了重要的“国难读本”。而介绍费希特的思想,更能促使国人之反省,“他又以自省的要旨,劝告国民认明自身的过失,亦系中国目前所最急切需要的反省。至于菲氏所倡导的新教育,虽经过百余年来的修改,尚未十分完备,然其对于公民道德的训练,则自始至终,即收莫大的效果。中国社会果欲彻底改革者,此点亦亟需注意。”
费希特的演说之所以能鼓舞个体之意志力、提高民族之自信心,与其哲学思想的基本主张有关。费希特继承笛卡儿的哲学主题,将“自我”作为其哲学思想的起点。在他看来,“自我”表现为与“非我”的对立,“自我”的特质在于其为一行动的主体,而“非我”(自然界)则表现为“自我”活动的质料。主体的意志力必然体现在客观世界中,“宇宙之责任,由自我造成之,以自我有原初的自动力也,此自动力表现于意志,表现于思想,自此而推演之,则‘非我’亦‘我’之所立定者也。”这种思想带有鲜明的“唯意志论”的意味,目的在弘扬主体性。然而此“自我”为一有限的“自我”,而且有无数个“自我”,因此“自我”还必须处理与其他“自我”的关系,不能以此个体之自由而干涉、损害其他个体之自由。因此,既可以保护个体自由,又可以保全他人之自由者,唯有团体,其中最至高无上的,无疑就是“国家”。费希特的思想既认可个体意志力的张扬,又以“小我”投身“大我”,以个人服从国家,以“自我”之有限而成就团体、国家之不朽,最能提升“国难”之际的国家意识。
除了费氏,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为知识分子的另一重要思想资源。据贺麟所述,中国真正对黑格尔哲学的大力鼓吹是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这一段时期,正值“国难”危机的前后。1931年北平《晨报》以及《大公报》文学副刊专门发表了纪念黑格尔逝世百年的专家论文,瞿菊农、张君劢、张颐、贺麟等人就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展开激烈的讨论。贺麟也积极介绍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他自述其中动机在于:
我之所以译述黑格尔,其实,时代的兴趣居多。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都是:政治方面,正当强邻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的时代;学术方面,正当启蒙运动之后;文艺方面,正当浪漫文艺运动之后——因此很有些相同,黑格尔的学术于解答时代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而黑格尔之有内容、有生命、有历史感的逻辑——分析矛盾,调解矛盾,征服冲突的逻辑及其重历史文化,重有求超越有限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实足振聋起顽,唤醒对于民族精神的自觅与鼓舞,对于民族性与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吾人既不舍己鹜外,亦不故步自封,但知一定之理则,以自求超拔,自求发展,而臻于理想之域。
贺麟介绍黑格尔的动机,正与张君劢推崇费希特有相合之处。毫无疑问,德国思想家的国家哲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容易为大力引进西方国家理论的学者所接受,又有鼓动大众爱国心的宣传效应,可以使高深的哲学思想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张君劢由英国思想转而倾向德国的哲学,其中确有其内在原因,即德国人看待国家与英国人截然不同。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张君劢曾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