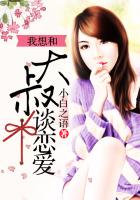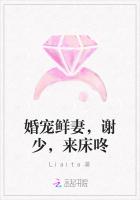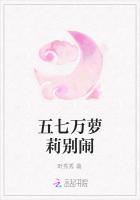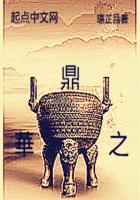“五五宪法”的公布应该是国民党实行宪政的一个政治信号,然而宪法却远未获得想像中的民众支持。民众对宪法的热情已经大减,“而国民方面,则依吾人所知,较之民元二,民五六,乃至九一八事变前后,对于宪政之施行,显有重视热视与轻视冷视之区别。”《大公报》的这个观察应该是不错的。民国以来制定的宪法已经够多了,但政治的混乱依旧,中国迟迟无法走上现代政治的常轨,那么这一次立宪能够不是另一次政治的闹剧吗?“立宪”正如胡适所希望的已经成为了一种获取政治同情的资源,然而仅仅以此为政治上的手段,又如何保证民众的政治热情不会消退呢?《大公报》指出,“宪政乃改造中国之最后一剂药。”而它也确实卖力地在为宪法颁布而鼓吹,“吾人以为目下宜发起一种国民运动,即全国一致,主张以实施宪政,为打破现状改造政局之较善办法,至少应促成国民党领袖辈之反省,藉宪政为解消恩怨之机会,同时并将此辈有力领袖,一概纳诸宪法活动之中,使各自由表示其对宪法之见解,且能于宪法之下,效力国家”。除了要求重新点燃民众的政治热情之外,这里言外之意是要求通过宪政这个全国的“共识”,来消除国民党内的分裂斗争。1936年粤桂势力与中央的关系正处于紧张阶段,这是要求李宗仁、陈济棠等地方军阀对宪法表态,达到全国的统一。这也是宪政必须在中国承担的一种政治责任。
注释:
①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1月23日),引自《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601页。
②《训政纲领》(1928年10月3日),引自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33册,黄山书社,1999年,33页。
③参见孙中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以及《三民主义·民权主义》,收于《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
④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1月23日),引自《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602、603页
⑤《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引自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33册,黄山书社,1999年,20—32页。
⑥参见张佛泉:《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四期,1933年11月6日。
⑦参见(日)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译:《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第五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14—128页。
⑧郭绪印主编:《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33—134页。
⑨参见(日)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译:《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第五章第三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8—133页。
⑩“全能主义”(Totalism)必须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区分开来。邹谠指出,“我用‘全能主义政治’这一个专门名词来表达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某一种特定的形式,而不涉及该社会中的政治制度或组织形式。‘全能主义’仅仅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他强调“全能主义政治”不同于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以及20世纪30、4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的极权政治和个人独裁。而Totalitarianism,从词根(Total)看,应该翻译为“总体国家”,意即一种“无所不在的统治”,然而“极权主义”似乎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译名。“极权政治”就广泛的意义而言,如萨托利所指出的,并不一定是一种明确的国家类型,而是一种趋势,即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是指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的信仰和推行。同时“极权政治”是一种现代的政治形式。邹谠对于“全能主义”的分析,见邹谠著:《20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222—237页。关于Totalitarianism译名,参见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194页注2。萨氏的观点见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203页。
邹谠:《中国20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收于《思想家:跨世纪探险》,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19页。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1年,429—430页。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4—5页。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1929年3月21日),引自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33册,黄山书社,1999年,34页。
(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75—276页。
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其一,以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党为代表,它们一般通过竞选的方式获得执政的资格,以对于政治上的共同看法来形成党的纲领和政策,即以“政见”来团结党员。这种政党政治的存在需要有一个共同遵循的政治秩序为基础,一般由两党或者多党轮流执政,一党上台还是下野,全在于党对于“民意”的争取。民初中国的政党纷纷兴起,然而政党政治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致使党争成为了扩大的派系斗争,因此“政见”结合的党在中国无法产生。20世纪以来的全面危机,并没有给中国提供一个足以开展政党政治的社会秩序,伴随着“社会革命”的日日紧迫,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得以在中国获得了它滋长的土壤。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35页。
王奇生对于国民党的改组中的苏俄因素,作了具体的检讨。他指出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只是采取了苏俄的组织形式,其“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未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使得国民党变的纪律严明、组织严密。参见王奇生:《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参见(美)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24—26页。(澳)布赖恩·马丁著、周育民等译:《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14—118页。
小科布尔和易劳逸都认为,蒋介石政府是出于维护其地位和利益,而利用与操纵对它有利的资产阶级。因此,认为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大资产阶级的说法,并不准确。科布尔的看法见氏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尤其是结论部分;易劳逸的看法见氏著:《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亨廷顿著、江炳伦等译:《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338页。
转引自亨廷顿著、江炳伦等译:《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339页。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1932年5月23日),收于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596页。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收于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33册,黄山书社,1999年,20—32页。
国民党最初也使用“党化教育”的提法,要求教育“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国民教育方针草案》,《教育杂志》第19卷8号),后来在192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取消“党化教育”,而改称“三民主义教育”。
参见戴维汉(W.J.Duiker):《蔡元培的人文主义与民国的教育改革》,收于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收于《政治论文》,新月书店,1932年。
参见陆宝千:《中国国民党对总理遗教解释之确定》,收于“中研院”近代史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1932年5月23日),收于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587页。
阿斗:《一件比蒋桂战争还重要的事情》,原刊《醒狮周报》198期,1929年3月。
关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参见JeanChesneaux,FrancoiseLeBarbierandMarie-claireBergere,Chinafromthe1911RevolutiontoLiberation,(NewYork:RndomHouse,inc.,1977)pp.190-205。
周作人:《谈虎集·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国民党的胜利适应了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追求。这一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支持国民党。鲁迅一度信服国民党的主义,他与顾颉刚的冲突,起于他批评顾对国民党的主义态度不明确。而顾也出面澄清他从未怀疑过国民党的党义。见HarrietMills,LuHsúnandtheCommunistParty,ChinaQuarterly,no.4,p.19.国民党建立的现代学术体制(如中央研究院、“大学院制”)也是吸引许多知识分子同情国民党的重要原因。顾颉刚在傅斯年的邀请下,南下到中山大学。鲁迅也到了中山大学。
参见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于氏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新月》二卷四期,1929年6月10日。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二卷六期,1929年9月10日。
国民党意识形态塑造的不成功,是导致其政治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像共产党那样将“共产主义”视为奋斗的理想(体现为一种面向未来的趋向),国民党向传统的回归,并力求塑造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最终使得国民党失去了知识分子和国际势力的支持。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在知识分子和国际势力间引起的反响,最能说明问题。费正清指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在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311页)而当时的几个支持蒋介石的大国,也被此书所体现出的“狭隘民族主义”(借用胡适语)所震惊。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收于《政治论文》,新月书店,1932年。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收于《政治论文》,新月书店,1932年。
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二卷二期,1929年4月10日。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会议决议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657—659页。
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二卷二期,1929年4月10日。
在《新月》停刊后,胡适由上海到北平,1932年胡适派学人兴办了《独立评论》杂志。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危机的加深,他们关注的焦点也由个体权利转向国家意志。详见第二章。
杨公达:《政治科学概论》,1930年(出版者不详),182—183、184页。
杨公达:《政党概论》序言,神州国光社,1933年。
杨公达:《突如其来的开放政权》,《时代公论》第53、54号,1933年4月7日。
杨公达:《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时代公论》创刊号,1932年4月1日。
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7、11号。
所谓“党政思想化”就是要求树立党的统一信仰,党内各派可以在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不能在根本信仰上存在争议;所谓“党员职业化”,要求党员要有自己的职业,而不能倚靠国家来供养;所谓“党部简单化”,就是要减少党部数量,使得国民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7、11号。
杨公达:《青年的出路问题》,《时代公论》第8号,1932年5月20日。
施存统:《理想中的以党治国》,《革命评论》第十六期,收于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314页。
胡适:《名教》,《新月》第一卷五期,1928年3月10日。
杨公达:《折衷主义与中国政治》,《时代公论》第3号,1932年4月15日。
杨公达:《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时代公论》创刊号,1932年4月1日。
这里的政治能力,主要是指政党动员各个阶层参与政治的能力。对于共产党动员能力的研究,可以参见(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MaryCWright:FromRevolutiontoRestoration:theTransformationofKuomingtangIdeology,TheFarEasternQuarterly,Vol.14.,No.4,(Aug.,1955),pp515-532.
参见(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引自马季廉:《认清自己的失败》,《国闻周报》第九卷四十九期,1932年12月12日。
《中执会“九一八”告国人书》,《申报》,1932年9月18日。
王造时:《国民党怎么办?》(1932年10月25日),收于氏著:《荒谬集》,自由言论社,1935年。
汪、于反对结束“训政”的理由有:人民程度太低,不经过训政,不能运用民主政治;认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否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就是否认中华民国的基础;过去的宪政是失败的,政绩不好;现在主张宪政的人,有些是从前的“官僚政客”,不配谈宪政。同上。
孙科:《抗日救国纲领》,《申报》1932年4月25日。
记者(张君劢):《我们与他们》,《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施存统:《理想中的以党治国》,《革命评论》第十六期,收于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314页。
张君劢:《当代政治思想之混沌》(在北平华北大学讲演),《再生》2卷11、12期合刊,1934年8月1日。
《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103—104页。
张佛泉:《训政与专政》,《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三十六期,1934年9月10日。
同上。
张佛泉说,“我以为民治需要人民有开通的头脑,专政却必定需要人民有热烈的心肠,民智水准如过低,民治容易变为政棍政治(Demagogue),民众如过于驯服,专政则恐容易变为虐政(Tyranny)。今日的斯塔林与希特拉政治与旧日帝制的俄德最主要的分别,我便可以说是,前者有一部分民众热烈地追随,后者只有被动的百姓。”张佛泉:《训政与专政》,《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三十六期,1934年9月10日。
马季廉:《认清自己的失败》,《国闻周报》第九卷四十九期,193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