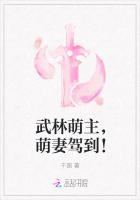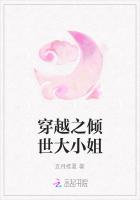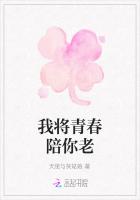参见朱亦松:《中国国家的伦理基础问题》,《再生》1卷6期,1932年10月20日。
张东荪:《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再生》1卷6期,1932年10月20日。
张东荪:《“国民无罪”:评国民党党内的宪政论》,《再生》1卷8期,1932年12月20日。
张东荪:《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再生》1卷6期,1932年10月20日。
季廉:《社会革命之危机》,《国闻周报》9卷6期,1932年2月1日。
短命的孙科内阁因江浙财阀的不合作而迅速倒台,详见(美)小科伯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63—69页。
同上,77—80页。
(日)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译:《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77页。
孙科:《抗日救国纲领》,《申报》1932年4月25日。
参见(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再生》的朱亦松说,“我认为过去革命政治的失败虽有种种原因,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原因,便是国民党误用他们在野时代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手段,作为掌握政权时代的指南针。”朱亦松:《国民党的病源》,《再生》1卷4期,1932年8月20日。
马季廉:《认清自己的失败》,《国闻周报》第九卷四十九期,1932年12月12日。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收于《政治论文》,新月书店,1932年。
记者(张君劢):《我们与他们》,《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记者:《本志第三年之运命与使命》,《再生》3卷1期,1935年3月15日。
《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汪精卫蒋介石书》,引自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19—82页。
《蒋介石汪精卫复张君劢书》,引自方庆秋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82页。
陶其情编:《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序,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
《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1929年10月21日中央44次常会通过),引自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与他的论敌》下册,时事出版社,1999年。
记者:《本志第三年之运命与使命》,《再生》3卷1期,1935年3月15日。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144—145页,岳麓书社,2003年。
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二期,1934年1月1日。
《本报解除停邮处分》,《大公报》社论,1935年12月12日。
邹文海:《请看宪法草案第一条》,《再生》1卷12期,1933年4月20日。
《关于言论自由》,《大公报》社论,1935年1月25日。
本文使用“公共舆论”特指1930年代思想界所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公”在这里代表了“民族利益”,即民族危机下,如何使上下一心共赴“国难”。这个“公共舆论”体现在知识分子兴办的各种刊物和报纸的言论中,也体现在知识分子思考“舆论如何成立”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这里使用的概念,不同于时下讨论热烈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关于“公共领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讨论,参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公共领域”理论的基本内容,参见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译林出版社,1999年。
《本报解除停邮处分》,《大公报》社论,1935年12月12日。
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二期,1934年1月1日。
政之:《作报与看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一期,1934年1月1日。
同上。
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二期,1934年1月1日。
张君劢:《舆论的造成与保障》,《再生》4卷6期,1937年6月1日。
杨公达:《休刊的话》,《时代公论》155、156号合刊,1935年3月22日。
这从《大公报》社论的内容就可以看出。社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向民众宣传政府的政策、要求民众对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一类为向政府介绍民众的意见与动向,要求政府体察民情、改进政治。
《新出版法的再检讨》,《大公报》社论,1935年7月30日。
《论统制新闻》,《大公报》社论,1936年6月9日。
《新出版法的再检讨》,《大公报》社论,1936年7月30日。
《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大公报》社论,1936年4月2日。
张佛泉:《论自由》,《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三期,1934年1月8日。
胡适:《蒋汪通电里提起的自由》,《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6日。
此处诚有林毓生先生所指出的,“以思想文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倾向,这种心理结构自然容易引发对于思想自由的重视。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张佛泉:《论自由》,《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三期,1934年1月8日。
同上。
革命和反抗,以完全改变现存社会秩序为目的;反权威、反政府,则是相信个体具有反抗超越个体之上的组织的道德优越感,都是以共营的社会组织压制个体为基本的判断。这种“个人主义”在外在力量过于强大的时候,可能迫于屈服,或者采取忍耐与“不合作”的对策,而一旦外在力量变得软弱,就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全面反抗。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第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关于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特点,参见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立国常轨》,《再生》4卷1期,1937年3月1日。
张君劢:《舆论的造成与保障》,《再生》4卷6期,1937年6月1日。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立国常轨》,《再生》4卷1期,1937年3月1日。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张君劢:《张东荪著〈思想与社会〉序》,收于《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
张君劢:《思想的自主权》,《再生》2卷1期,1933年10月1日。
“与境性”这里指一种思想、主义或制度,有其赖以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同时,当一种思想、主义或制度被引入到另一些不同的背景和条件时,它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一些改变。
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142—143页。
《独立评论》第一号,引言,1928年3月10日。
张君劢:《舆论的造成与保障》,《再生》4卷6期,1937年6月1日。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3年6月1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通讯(储安平—记者):《现在的问题》,《再生》1卷3期,1932年7月20日。
记者(张君劢):《说自己的话》,《再生》4卷1期,1937年3月1日。
胡适:《容忍与自由》,《胡适文集》卷十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27页。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4年12月16日。
谢泳把胡适的“自由主义”概括为一种“宽容”的精神,参见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立国常轨》,《再生》4卷1期,1937年3月1日。
张东荪:《“国民无罪”》,《再生》1卷8期,193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