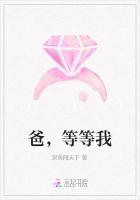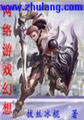本书的正标题是《“国难”之际的思想界》。本书所要处理的是1931年到1937年之间,由知识分子的言论所构成的思想界,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系统讨论。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其一是“国难”;其二,是“思想界”。“国难”指的是“九一八”以后日本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东北首先被日本占领,并且很快由日本人扶植了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复辟”,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东北的沦陷对于知识分子的触动是深切的。东北是中国工业的主要集中地,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后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步伐,策动华北五省的分裂,这进一步加深了知识分子的危机感。华北是国民政府教育的重镇,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设在京津地区。思想界处于“国难”最前线,那种亲临危机的感觉与理性的思考相结合,更能促发他们对于如何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追问。
“思想界”的主体自然是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是大学教授,有正常的收入来源,有的还进入政府,有的虽然身在“朝外”,却为政府提供着政策上的帮助。此外,知识分子还通过报刊和杂志等舆论来表达他们的看法,这些制度性的传媒使得他们的言论具有了公共性。近来史学界已经有人开始重视对于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形成的研究,指出各种“界”的表述的出现表明了一些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形成并且寻求着相互之间的“认同”——比如省界、实业界、政界、学界、教育界、思想界等等。①至于“思想界”的明确意识的出现,大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当时新思潮的倡导者希望通过全面批判儒家伦理思想的斗争,弘扬“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些努力在20年代,逐渐转向了从学术上整理中国文化的思潮,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对于中国上古历史的全面否定。②1920年代的思想界是一个“学术”与“思想”互相推动的进程,通过学术的讨论以推进思想革命,是20年代思想界的主题。③到了1930年代,思想界则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中国政治问题的讨论。这种转向一方面正如上文提到的是“国难”危机的紧迫,促使知识分子们必须思考中国在政治上向何处发展,才能避免亡国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的成立,使得中国的政治秩序得到了基本的稳定,在此前提下,一切民主化和社会改造方案的讨论才成为了可能。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成立,奠定了中国新的统治秩序。然而这个政权从其成立之始,就只是名义上象征着全国的统一,各地军阀仍然维持着他们实质上的割据。在国民党内,汪精卫为首的党政系统、蒋介石为首的军政系统以及老资格的党员胡汉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孙科在1932年宣传民主和宪政,在党内的呼声一度也很高,而改组派、第三党等蒋介石的反对力量也在1933年底的福建事变中,结成了“反蒋”的联盟,再加上日本的入侵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正如易劳逸所指出的,国民党在1934年以前的处境非常困难。④在1934年,国民党安全地度过了党内反对派的攻击,同一年蒋介石的所谓“剿匪”,也导致红军被迫离开江西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前途未卜的长征。蒋介石在南昌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这是新政权试图确立其意识形态的标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混杂了许多复杂的成分:蒋通过“蓝衣社”来推广“新生活运动”,这是一个试图向法西斯主义学习的组织;蒋本人则推崇清朝中兴的重臣——曾国藩;他所主张的“力行”哲学又来自于阳明心学,他努力用阳明心学的东西来解释孙中山的学说;他的姻亲宋氏家族是基督教的信仰者,而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重要人物也在“新生活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⑤蒋在公开的场合从来都不承认有必要向法西斯主义学习,虽然当时法西斯主义被视为是塑造强大国家以应付危难的一个途径。蓝衣社确实企图掀起一股崇拜领袖的风气,不过蒋在它举动过于激化时曾经加以阻止,他有意加强了CC系的权力,以求在两者之间的平衡。在易劳逸看来,把国民党看作法西斯主义的政权是不恰当的。⑥
国民党确立了一种新的统治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党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属于列宁主义的政党,不同于西方国家以政见结合的政党,它们都以一种意识形态来团结党员的效忠和相互之间的认同。⑦两党都受到了苏俄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下,改组并成立了新的国民党,从而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他的党内团结的问题。费约翰研究了国民革命中所体现出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意义。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志士仁人都在试图“唤醒”中国人民的自觉意识,他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一种‘唤醒政治’是如何在一场群众运动中变得体制化的”,结果他发现“从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到中国作为一个民族观念的增长,到一个在中央政权领导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最终到一个党,一种声音”,“民族觉醒的观念从一种不成熟的冲动,最终演变为一种鲜明的、纪律化的大众政治风格,并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督之下。”⑧费约翰的力作,为我们理解国民党的“训政”(即以政党代替民众来统治国家)体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国内史学界大都倾向于抨击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对于国民党的统治方式,邹谠则试图从一种“中性”的分析概念入手,他指出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着全面的社会危机,这一危机呼唤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⑨国民党确实试图通过强大的党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虽然它的能力并不足以保障它那样做。王奇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国民党党的势力在与军队、政府势力的竞争中,并未能真正占据上风,甚至在地方国民政府有意抑制“党权”而强调“政权”,因此它并未像苏俄那样真正达到党对军事和政治的全面控制。⑩正如当时一些思想界的论者指出的,国民党不过是“冒牌党治”的政党。因此,对于国民党“党治”的强度和影响,似乎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但是国民党的“党治”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却是极大的威胁,国民党强调思想的控制和“党化教育”,用严酷的手法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自由”是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最珍视的价值之一。胡适在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初,曾经激烈地批评了国民党侵犯“人权”的政策和所谓的“党化教育”,这使得国民党将胡适列为“反党分子”。余英时曾指出,正是“人权”运动初步确立了胡适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九一八”前后,思想界开始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的“训政”思维,他们要求迅速实现民主化,胡适并且有明确的“宪政救国论”的思想。在“国难”背景下,国民党不得不作出听取民意以共赴国难的姿态,国难会议的召开、宪法草案的拟定和1936年“五五宪草”的通过,都成为思想界讨论“宪政”问题的重要时期。
这里有必要探讨知识分子在民国政治中的地位。当然,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难免会陷入一个概念论争的困境。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无疑是旧式“士大夫”,但是现代知识分子却同传统“士大夫”有了根本的区别,在1905年科举考试正式废除后,那些保障“士大夫”特权地位的制度性机制不复存在了。余英时先生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面临着“边缘化”的处境。在军人、工商等新兴集团势力崛起的同时,知识分子却不再是社会的中心了。罗志田则指出,在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另一些边缘知识分子也在逐渐兴起,比如学生集团。确实,学生在现代中国成为了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以致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通过动员学生来打败他们的政敌。思想界在30年代就非常重视青年学生中间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努力修补他们与学生之间存在的隔阂,他们非常担心学生运动中爆发出来的“左倾”情绪。不过,通过对30年代思想界主体的考察,笔者认为知识分子都在通过发表对于现实政治的种种意见,来寻求重塑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毫无疑问,知识分子还保持了一些他们的前身(“士大夫”)的影响力,或者说政府还不得不顾及到来自“士人议政”传统的压力。以《独立评论》群体而论,胡适等人在30年代都或多或少有“参政”的经历,他们对于国民党政策的抉择或是维护、或是批评,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样,国民党也非常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利用,抗战爆发后不久所成立的“国民参政会”,聚集了大量知识分子,它被视为一个准民意的机构。
如果说,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那么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则用它特殊的方式,在重新塑造一个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知识分子通过思想界的论争,发表他们对于国家、社会各种问题的意见,从而确立了他们的“公共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思想界”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是知识分子的独占领域,其他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力量是无法真正参与到“思想界”的话题中来的。首先,知识分子垄断了“知识”资源,他们是一群“读书人”,而且往往是有留学国外经历的学者成为了思想界的主流人物。其次,知识分子还掌握了现代的传媒手段,借此他们可以不断扩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是办报纸、刊物以及各种其他出版物的主要力量。本文所选择的几个主要的报纸、刊物都是由知识分子主办,从其构成来看,绝大部分都是有留学经历的大学教授,还有一些专业的记者和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报人”。从其影响来看,以《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为例,可以知道当时北方的舆论几乎都被这两个刊物所垄断。其广泛的读者群体中有来自各个阶层和不同行业的支持者,陈仪深对《独立评论》读者群体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大公报》则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而且它很好地保持了与知识分子的合作。至于《再生》和《时代公论》,虽然其影响稍逊,但也很有特色。《再生》是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时代公论》则代表了首都思想界的主要倾向,遗憾的是对于《时代公论》的专门研究似乎还没有看到。
1930年代自由主义的问题集中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对于这场论争该如何看待,学界一直以来似乎都陷入了“后见之明”的误区,因此没能很好地理解当时的历史现实,以及思想界所最关注的问题。一般都把主张“民主”与主张“独裁”者加以明确区分,甚至纠缠于一些政治价值理念的“先入为主”的判断。30年代民主独裁的研究,还同80年代末以来“新启蒙运动”中一系列论战纠缠在一起,在论战中双方都以“历史”为论据,从而使得历史经验成为了政治理念斗争的工具,这自然影响了我们对这段历史“同情之了解”。“胡适是不是始终坚持着自由主义的理念”,“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关键时候往往会倒向独裁政治”,这些疑问和结论,都是心中先有了一个政治价值的选择才产生的。但是,30年代世界范围内“统制”潮流是一种新的政治趋势,即使是那些民主的故乡美国和英国,也无不倾向于“独裁”了(胡适等人称之为“集团主义”),可见“独裁”并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反人性”的恶名,反倒是世界危机中的一条出路。如果说,政治上的“独裁”还有人反对,那么经济上的“独裁”(即“统制经济”)则得到了普遍的拥护,这种将政府权力深入到经济领域的趋向,还被认为可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无疑这和我们今天称之为“极权主义”的体制,已经相去不远了。当然,由于民族的危机、国家统一的需要和提高政府效率的呼声等因素,也推动着思想界实际上认同了“独裁”政治的效力,虽然有很多人“名义”上仍然坚持着“民主”政治,如胡适就是其中之一。
思想界在上世纪30年代还非常关注社会改造的问题,这与2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社会革命风潮迭起,而引发的国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与革命的需要相结合,提供了解释中国社会性质的一把钥匙。社会史论战使得从社会、经济角度观察和认识历史,成为了思想界的一种自觉意识。在社会改造日益紧迫的时期,人们开始考虑改造社会的途径,英美的社会主义新趋向和苏俄共产主义的初步成功,提供了两个可供思想版界选择的路向。实际上,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这从胡适和其他人的身上可以看得清楚。胡适在30年代一直对苏俄道路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同时他也把“罗斯福新政”当作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思想界虽然还无法完全接受苏俄的共产主义模式,但是对苏俄所取得的惊人的建设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纷纷到苏俄实地考察。他们认为苏俄的计划经济、农业集产化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社会改造所借鉴。蒋廷黻和丁文江更是在寻求富强的理想感召下,认同了苏俄的道路,认为中国应该采取“独裁”的政治。总之,30年代思想界面对苏俄这个远东崛起的新贵,态度是十分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