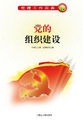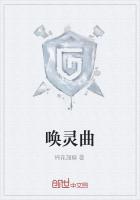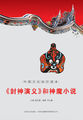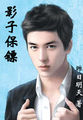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必然是更为猛烈的爆发。1935年,随着日本对华北领土的步步蚕食,处于“国难”最前沿的平津教育界再也无法沉默下去了。“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剧的喷发出来,而当时共产党的北方局积极地参与了动员学生反对国民政府的活动,他们深入到学生中间,不断地把学生的爱国热情推向激进化。这使得罢课和游行持续了很长时间,教育界的正常秩序被严重打乱。作为思想界的主要成员的大学教授们,在学生运动面前显得十分为难,他们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但是又担心学生运动的政治化,而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胡适的态度可以作为代表。他赞赏学生们的政治热情,“所以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可喜的事”,在他看来,一个言论不自由的社会,其干预政治的形式就只有靠青年学生诤臣式的义举了;但是他又不同意以“罢课”方式而耽误学生的学业。罢课的举动是“不幸”的,这已经超出了理智的界限,“凡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假公济私、破坏法律,都不是受教育时代的青年人应该提倡的,所以都不是学生运动的方法”,在他看来,学生的爱国热情被利用做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亨廷顿曾指出,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由于其政治远未制度化,因此学术社会更容易被卷入政治运动。胡适的观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他不同意走上街头的革命举动,“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能力”,无疑地青年只有获取了理性的改造社会的能力,才真正对于国家和民族有所贡献。然而,胡适的理性忠告,却淹没在青年不断激进的“左倾”浪潮中。“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在那个民族情绪激荡的时候,学生哪里能够安下心来学习呢?
这样,青年人开始和思想界的领袖们分离了。胡适曾经在青年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在他1931年重返北大的时候曾经受到了学生们热烈的欢迎,为此他还深受感动。然而,老师们在学生运动中的立场使得学生十分地失望,在他们看来,老师们已经渐趋于保守,而认同并维护着那些现存秩序。老师们所寄望的点滴的社会改良,那种建立在“实验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哲学,也已经失去了有效性。丁文江惊异地发现作为中年人的一员,他已经和青年人有了极大的隔阂,他们一面斥责那些中年人侮蔑青年“不道德”的说法,一面在试图填平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他指出“只有具体的、各个的,而没有抽象的、普遍的道德”,一个团体的道德也许在其他团体看来就是罪恶,因此不是青年人“不道德”,而是中年人还沉迷在旧道德中,无法适应不断进化中的道德标准了。“我们要改造我们的道德和伦理,要打破一切权威的观念,把人的忠信心从家族、帝王、神佛移到社会上来,尤其要有在社会成功的首领以身作则为青年来做领袖,然后才可以建设出近代化的中国。”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德进化论的观点,青年代表了近代化的方向,年轻就意味着“进步”。丁文江满怀激情地对比了现在的青年和30年前的青年,结果他认为现在的青年在体格、知识、能力、道德各个方面都比过去的青年进步了许多,他忠告中年人不要动不动就责怪青年的退步,最后他希望两代人达成和解。在他看来,青年无疑是中国复兴的希望,“这三十年来青年的进步是我个人民族自信心的最大的根据。”但是他也知道青年重情绪而轻理智,容易为一时的激情而贸然牺牲,他也强调青年加强知识能力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在这方面,作为中年的他们应该给予青年有益的指导,“当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中年不能领导青年,青年不肯受中年的领导,是国家一个很大的弱点。”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丁文江试图重塑思想界与青年人的和谐关系。
思想界发现现在必须重新树立青年人对于国家的信心,他们需要引导青年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不是眼看着青年向反政府的方向发展。“一二九”运动风潮刚刚平息,行政院就要求教育部筹议“国难”时期特殊教育的方针。思想界纷纷就“国难”教育发表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应该设立一些特殊的课程,比如军事训练课,并着重发展与军器制造有关的专业,总之实施短期内可以为“备战”服务的举措。但是,更多的人承认教育的目标是长期的。“国难”教育应该更重视塑造学生的国家意识,他们以费希特的教育思想为启发,“从远大处着想,要建设一种新教育制度来发扬祖国的文化,改造国民的品性,树立复兴的基础。”杨振声认为教育应该奠定国家的立国基础,而“科学”这种新文化才是一国强大的基础,中国的科学教育还极需加强。另一些人则要求教育必须体现出民族的精神,一国的精神则积淀在他们的“历史”中。张其昀指出科学文艺历史之教育各有作用,“科学训练示吾人以开发富源建设新邦之途径,文艺修养予吾人以唤醒国魂恢宏民性之工具,史学陶冶则令吾人有排除万难誓兴祖国之决心。”他强调了青年承担国家历史之重任,“明兴亡之大义,知立国之纲维,导民力于正轨,此负荷国史之重任,乃青年自觉之源泉,而当与科学文艺相为羽翼者也。”正因为承担责任之重大,故而青年对于自己之信心也应该更强。古时“士”之教育则既重视理智的培养更看重情感和意志的养成,因此潘光旦主张加强青年的“人才教育”,即教会青年如何“做一个‘人’,做一个‘士’”。加强国家意识的同时,更要使得青年愿意积极参与政治的讨论,“首宜令一切学校于寻常功课外,注意国难时期之政治教育。不论何科何系皆应由学校当局亲切指导使学生于课余得讨论研求现实的国家问题。读书发言,皆畀以最大限之自由,而师长指导之。官厅取缔反动,惟重实际行动,学校以内,则赖讨论之方法,以集中学生之意志。”因为新闻取缔制度的存在,学生无法从正常渠道获知政治的信息,同时政府试图取缔共产主义思想在青年中的流传,在思想界看来也不可取,他们希望通过公开的讨论,纠正学生们在思想上的偏差。
正如国民党这一时期因为“剿匪”而疲于奔命,思想界则面对共产主义思潮在青年中的广泛影响而焦头烂额。在思想战线阻击共产主义的传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明显共产主义有它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对它的批判也需要强大的思想武器作后盾。正如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把共产党视为“匪”极为不满——丁文江说,“我们对于国民党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他们认为这表明了国民党的无知和傲慢。他们警告共产主义是国家强大的“敌手”。景文说,“共产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而且有国际背景的政治集团”,他进一步申论道,“共产党的势力含有五种元素。第一种是主义,第二种是组织,第三种是民众,第四种是武装,第五种是国际背景。”共产主义当然迎合了某些现实的需要,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是大有问题的,因此从思想上“反共”必须正视它所触及的社会矛盾,并提出足以与之抗衡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必须具有“世界性”,能提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并且有确定的群众基础。
丁文江确信共产主义有它的“好处”,“我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包含一部分的真理。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已经变成为普遍的心理。在任何制度之下,完全违反这种原则,是很难维持社会的安宁的。所以我们对于现行的资本制度是不能满意的。”在思想界所珍视的诸价值中,马克思主义无疑与他们在对“平等”的追求上是一致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却戕害了他们同样重视的另一价值——“自由”。马克思的学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它是鼓吹社会革命,鼓动人类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手段罢了,“马克思痛恨社会的不平等,所以要鼓动阶级战争;因为要鼓动阶级战争,所以造出他们的价值论来证明劳动者为失主,资本家是强盗。他的价值论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但是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动员的口号,因而它也最容易鼓动那些缺乏理性思考、重视实际行动的青年学生。马克思为了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还不惜掩盖社会的事实和学术的真理。张东荪批评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我们当然不能反对阶级的存在,不过决不能象马克思派那样只分为‘布尔’与‘普罗’。须知店员是一个阶级,而与工人并不在一个范畴内。经理人是一个阶级,和股东并不是完全在一个立脚地。此外如佃户便与长工(即雇工)大大不同。手工业的学徒与工厂内的工人亦不可一概而论。即如包工制的工头,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劳动者。凡此种种足见社会的阶级是很复杂的。在这样的复杂的社会内,要使其形成对垒的两大势力是不免于太理想了。所以阶级的讨论在社会学上是一种研究性质。但马克思一流的阶级论却不是如此。乃是先立有一个目的,然后再以说明来强勉证明之。他的目的是社会革命。
把马克思说成是社会动员的手段,而不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在思想界是一种趋势,其用意无非是要青年学生识破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不要为马克思的“假科学”而蒙敝。马克思主义是“为革命而学术”,思想界则希望学生们返回到“为学术而学术”的正轨中来,正像他们一直以来所作的那样。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批判,来自于罗素、拉斯基等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张东荪和张君劢在30年代初,曾集中于从哲学上批判唯物辩证法,张东荪还把论战的文章汇集成书出版,这似乎正是承继了罗素从“新唯实主义”的角度批评马克思“粗糙”的“唯物论”的主题和观点。而拉斯基在《共产主义论》一书中,也阐明了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态度,他批判劳动价值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似乎直接影响了丁文江。
这时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开始实施他们的土地革命政策,这使得思想界极为担心,因为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在中国人为地制造了阶级的斗争。中国尚未有产业的发达,更谈不上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对立了。张君劢批评道:
吾国共产革命,已逾十年,时间不为不久,不知他们是否明白中国到底有几个资本家呢?以上海来说,有几百个烟筒,几万间洋房,这就算资本主义么?其次,中国有多少个大地主呢?全国除东三省外,关内各地多为小农、中农。在欧洲时,我曾到一个大地主家里,走了两三点钟的汽车,还没有走完他的土地。他的土地是一两万英亩以上,他们的房子完全是封建时代王侯第宅,牛有几百,马有几十,农夫几百,农具自己制造。这才是真正大地主。我国大地主,假定他有一万亩两万亩地,但有各子平分的习惯,不到两三代大家又变成小地主,怎样能和欧洲的大地主相比呢?共产党的口号,要打倒大地主、大资本家,由于他不考察国内情形,读了几本外国书,就一天到晚高喊着打倒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确实提供了研究和分析社会问题的一把利器。以“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来观察与把握历史的方法,到了30年代通过社会史的论战,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即使那些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不得不专心下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质,他们必须应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国现在究竟处于什么历史阶段、中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究竟如何。所以像罗素、杜威等知名学者到中国来,都在研究、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无产业,更谈不上严重的阶级斗争,正是罗素的论断。在列宁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中,肯定了中国历史和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强调了由中国的历史状况来决定中国革命的策略。因此,要批判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就必须从社会和历史的分析入手。张君劢在这里批评的重点,就在于突出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手段在中国缺乏历史的基础。
对共产党的另一个有力指控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它不过是受第三国际控制的“傀儡”。丁文江批评道:
中国共产党不过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举动不能自由的。莫斯科是共产主义的罗马,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很像教皇。中国共产党就譬如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教会。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当然不能离开第三国际而对于共产党有任何的希望。
表面上看来,列宁当时是号召“世界革命”的,第三国际希望团结各国的共产党人在苏俄的领导之下。但是实际上第三国际的政策是灵活的,在支持中共两党的首次合作上,苏俄是从中国的民族主义出发,而不是要推行“世界革命”。张君劢已经看出,苏俄在不断地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而逐步讲求民族主义的利益。他甚至批评中国共产党可能成为苏俄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牺牲品。在30年代,张君劢的《再生》群体一再声明他们“国家主义”的立场,他反对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行“世界革命”的目标,张君劢指出这从横的和纵的两个方面在切断着“国家”这个共同体。张君劢常常拿斯大林加强国家意识的事实,来规劝共产党放弃他们不合时宜的革命立场,回到“国家主义”的正途。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张的这种立场还使得他强烈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中,他委婉地指责共产党保留自己的军队、占有自己的地盘,并且不肯放弃马克思主义,是对“国家至上”的严重危害。
在另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张君劢还指责共产党对青年的利用,并讽刺它在政策上的摇摆不定。他似乎认为共产党并不具备一些政党的基本要素,比如缺乏对于自己党众的一种责任伦理,没有一个坚强的信念,缺乏自主的理论基础。总之,思想界在力图让青年远离共产主义的影响,他们害怕共产主义对青年的动员,他们又担心失去中国最有前途的这支力量。
五、社会改造一例:农村复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