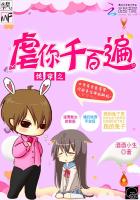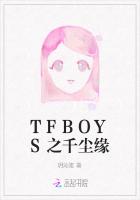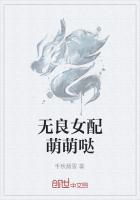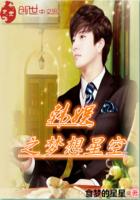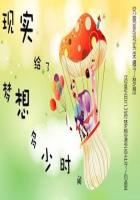如果说,1920年代思想界的主题,在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促进思想解放的话,那么1930年代的主题,则在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而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也就是说,1920年代为新、旧思想之战争,1930年代则为救亡图存之思考。“国难”危机成为促使思想界主题由学术思想转向政治问题的关键。
1920年代的军阀政治,使得许多人都对政治改造失去了兴趣。民国之初造就的共和制度,被军阀的腐败、混乱和争斗破坏了。那时,在一般知识分子眼中,现实政治的黑暗使得他们灰心丧气,许多人由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引发对于民主制度在中国能否实现的怀疑,并生发出一种政治上普遍的“疏离”。鲁迅就因对现实的失望,而以“抄古碑”的方式聊寄人生。更有知识分子在激烈的社会变动中,因为“意义”追求没有着落,诉诸“自杀”的极端方式,以寻求解脱,梁济和王国维的自杀就曾引起思想界极大的震动和关注。当然也有试图在军阀政治中寻求改造的尝试,比如曾经坚持“不谈政治”的胡适,却也不得不在组织《努力周报》时期宣传“好人政府”,为社会的秩序寻求制度上的保障。而老资格的革命者和经学家章太炎,则于军阀势力间纵横捭阖。不过,此种种努力终究毫无结果。胡适很快就放弃了他的主张,寄望于“文学艺术”的改良了,而章太炎更是为个人牟利多,鲜有政治上的追求。总之,1920年代知识分子于政治的失望是普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他们改造思想的决心,也为学术上的努力创造了条件。
然而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节节胜利,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政权更替。对于国民党,思想界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非常反感国民党的“训政”模式,在孙中山的革命阶段论中,认为国民党在结束军事统一之后,应该转入“训政”阶段,在此时期内,国民党代替民众执掌政权,以待民众具备了参政议政的能力,然后转入“宪政”。由此确立的便是国民党的“党治”,也就是一党的独裁,民众的自由在此统治下,必然要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对于思想界自由、民主的理想,无疑是一个严重打击。“党治”的力量首先就在国民党“清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了,在一系列恐怖政策的压制下,国民党征服了资产阶级奠定了它的经济基础,而通过“党”推行的思想统制和“党化教育”,也奠定了它的意识形态。当知识分子迎来一个新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却似乎距离他们民主、自由的理念更远了。胡政之曾经指出,国民党的“党治”的结果,使“报人”可以发表言论的自由度比军阀政治时期更小了。这自然引起思想界的极大不满,胡适和罗隆基发起的“人权”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的出现毕竟使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统一的希望。在长期分裂和地方割据之后,思想界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初步愿望,必然落在了国民党的身上,虽然国民党在1934年之前,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形势。无论胡适还是张君劢等人,都寄望于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胡适“实验主义”哲学的背景使他认为,中国急需解决的仍然是那些老问题,社会的进步必然诉诸于点滴的改良。当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以后,社会似乎自发地会产生某种积极的力量,这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因此那些善于洞察社会变动奥妙的政治家和学者,就应该千方百计地创造一个这样的秩序,而任何试图破坏这个秩序的行为都应该设法避免。胡适称之为“社会的重心”。他指出,中国之所以数十年来没有出路,就在于无法找到一个这样的“重心”,而在国民党的身上他看到了塑造这个“重心”的希望。张君劢则本着他的德国哲学的思想基础,宣传重建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他宣传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从中国文化中提炼出了所谓的“民族精神”,这使得中国可以在承续自己的民族使命的同时,塑造出一种现代国家的意识。(详见第二章)虽然表示支持国民党,思想界的主要人物并没有停止对国民党的批评。胡适很不满国民党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张君劢则更是宣告了国民党“党治”的失败。不过在民族的危难面前,他们似乎只有寄望于国民党自身的改造。“九一八”以后,国民党也迫于压力,开始寻求民众的广泛支持,宣称要缩短“训政”的时限。孙科更是在1932年前后,成为了国民党内主张民主的代言人,他希望能够改变“党治”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间的隔阂。(详见第三章)
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展开了关于中国政治出路的全面思考。当然对于中国政治出路的探讨,首先要弄清楚中国问题的现状是什么。对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和评价,思想界从1920年代以来就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切为1930年代的思考奠定了条件。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所关注就是社会问题。知识分子越来越意识到一切政治进步的障碍在于其社会的根源,于是他们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并且主要地集中于它的社会基础,即家族制度。在此背景下,1920年代人们开始广泛关注“社会问题”,那时的青年学生试图投身到社会改造中来重塑新的自我,他们走出“家庭”、走向广阔的“社会”。在此动力下,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社会调查开始推行。1920年代,到中国来讲学的两位思想界的巨头,罗素和杜威,都在中国发表了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看法,他们的观察和思考无疑奠定了思想界的主调。胡适一直坚持着杜威的教诲,比如他对中国问题的概括(所谓“五鬼乱华”);张东荪则继承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的许多看法。罗素和杜威都把社会的变革视为一项讲求谨慎和尊重经验的事业。这些思想家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思想界对于社会改造的兴趣。
此外,随着国共合作和“北伐”的进行,新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这场革命背后是一种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它有着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系统判断来支撑它对于中国革命策略的指导——正是由于民族主义革命的现实使得国共的合作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马克思主义借着新的革命运动,而逐渐扩充着它的“唯物史观”的地盘,它用历史来说明革命的合理性,用革命来证明历史学说的真理性。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根据“社会—经济”的变迁来解释历史的理论,它对于中国社会的有力解释,推动了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热情。192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史论战,无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解释方面的优势地位,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学者都必须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解释中来寻求问题的答案。即使象张君劢、张东荪等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理论的学者,也必须从中国历史的解释中来说明中国社会的现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研究中国问题的方式、关注的对象甚至是得出的结论,从这一意义上,它无疑是一种新的“典范”(paradigm)。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思想界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也是“他们从过去都继承了些什么?”早在《新月》时期,胡适就汇集了“八九个朋友”对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讨论,编成书出版。文章中提到,“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之间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个人随他的专门研究,提出论文,供大家讨论。去年(1929—1930)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讨论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发去的。……今年(1930—1931)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分为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个人分任。”由“研究现状”到“解决问题”,胡适对于自己的任务非常明确。从这本取名为《中国问题》的书中所收录的文章可以看出,胡适等人在寻求对于中国社会的准确认识。这为他1930年代讨论政治问题作了准备。《再生》群体的冯今白也把“再生社”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汇集成《中国往那里去》一书出版,目的也是为中国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陶希圣是“社会史论战”的主将,亦在1930年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书中他认为思想界关心社会问题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
民国十七年秋到民国十八年现在,是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展望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过去革命高潮已成过去,他方面未来革命战斗尚在未来,有形成理论斗争时期的定命。在其间,有许多刊物,定期不定期或以杂志或以书籍而出现,若对于此其间在理论斗争之名下所发表的论文,加以概略的观察,则可分为两大部门。其一为原理的争辩,若所谓唯物或唯心或心物二元论,又如所谓革命之阶级基础以及阶级转化等说。其二为历史事实的检讨,首在认定中国社会形式为何物。
胡适等人在这一时期的思考,确实是处于一个革命的过去与未来的间歇期(革命推翻了一个旧政权,而一个新政权刚刚建立),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论认识,也成为1930年代大规模政治问题讨论的起点。
1930年代思想界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往往首先关注中国政治现实背后的社会根源。确实,当人们寻求政治改造途径的时候,需要首先对于他们从历史继承下来的那些制约改造的社会条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尚处于“无政治”的状态,换句话说,中国还没能走上现代政治的轨道。人们在中国社会中发现了那些制约中国政治长期处于“前现代”状态的种种不利因素,如果这些社会因袭的毒素还无法清除的话,那么现代政治是无法实现的。《时代公论》的阮毅成有一段关于什么是政治轨道的比喻,“政治轨道的钢铁,是人民政治智识与政治能力,必先有百炼不挠的人民,乃能锤炼出好的法律制度。这好的法律制度能载的了政治车厢的重量,能顺利地助益于车辆的开驶。如其有不合适的车辆,轨道定不予以平安通过,非使其倾覆不可。”这正是在思考制约政治问题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的因素。
张荫麟认为中国文化中有与法律制度根本冲突的地方,即所谓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也是试图从文化因素来探讨政治问题。陈之迈很重视促使宪政运行的那些社会因素,比如国民遵守法律的习惯、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舆论的制裁力以及一国教育的普及。在对西方宪政考察之后,他指出中国现在实行宪政的条件还不具备。“宪政”不仅仅是一套政治制度,而且是与其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相结合的一个体系。总之,现在人们大多把政治问题的考察,首先着眼于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那些“条件”。
当然,思想界的人士也在积极地寻求可以促进中国政治改造的动力,这同样根植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胡适和《时代公论》的几个成员,似乎都在积极寻找中国最能产生现代政治意识的集团力量。萨孟武倾向于把国家政治的基础建立在依靠某一个最有力量的阶级之上,即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张其昀主张“士治”,“教授与技师,博学与专精,好比是车之两轮,前者供给深沉的思考,后者供给纯精的法术。”实际上,这是主张由最有知识和最精通现代社会本质的人组成的“专家政治”。梅思平希望调和“资治”与“士治”,他认为中国转向“有政治”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国民党或非国民党能够与资产阶级相团结以制裁武力的问题”。他设想的是智识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掌握财政权,作为国民党“党治”的补充,以财力和智力的结合来共同制裁武力。无疑,“武力”决定一切正是中国“无政治”的表现,思想界在努力寻找现实社会阶层中可以制约武力的力量。胡适非常高兴看到社会集团力量的兴起,尤其是那些各行业的联合组织(这多少受到“费边社”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上海是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地方,这里从清末以来就形成了许多工商业的组织,他们联合起来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萨孟武和胡适所寄望的社会力量,亦主要是指这些现代经济势力。1932年5月,上海市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钱业工会以及银行业工会掀起了“废止内战同盟运动”,“废战运动”使思想界看到了改变中国政治的希望。胡适“相信这个运动可以造成一种道德的制裁力”;天津《益世报》也评价这次运动的意义,在使人们认识“建设和平方式改换政权之政制”的必要。从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阶层出发,推动中国政治的改造,已经成为1930年代思想界关心的主要问题。
当胡适等人公开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时候,他们也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的。蒋廷黻把中国近代以来混乱的历史,明确地归结为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地方分裂主义,在他看来一切政治的问题都在不能“统一”。傅斯年则说的更明白,即中国现在的唯一出路是要“有政府”。当一个政府甚至无法达到“统一”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引导建立一种现代政治的秩序。丁文江在讨论中国政治出路的一篇文章中,试图向人们展示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这些决定了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权力的“规范化”——即人们对中央政权的尊重以及明确的政权转移的程序——而且采取的方式必须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丁的观点受到了《国闻周报》马季廉的强烈批评(马相信“社会革命”)。在他看来,国民党已经陷入了重重的危机,无法成为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正轨的动力,他强调中国政治改造的动力是一种难以阻挡的“社会革命”。当国民党政府已经陷入中国政治的传统怪圈,而走向腐败与堕落的时候,胡适等人还寄望于他们实现“宪政”无疑是不明智的。中国政治的动力究竟在“社会”的自发还是“政府”的主导?他们对中国政治出路的不同选择,都源于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不同认识。
当然,这些对于政治问题背后的社会因素的考察,只是思想界思考中国政治出路的逻辑起点。在此之上,正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然而,只有在认识了“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之后,一切政治问题的解决才成为可能。如此,思想界的政治关怀才不是“空中楼阁”,才不会陷入单纯的理论论争和价值判断中。
三、思想界的构成
关于1930年代思想界的主体,本文主要选择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兴办的刊物。其中包括胡适等人办的《独立评论》,张君劢等人办的《再生》,以及杨公达等人办的《时代公论》,还有《大公报》和《国闻周报》。其中包括了当时不同取向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以及有影响力的报纸。下面简单作一介绍。
1《独立评论》:“专家政治”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