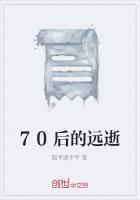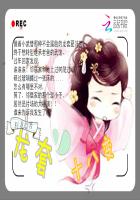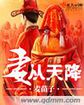1931年“人权运动”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胡适被贯以“反党分子”的头衔,并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于是,胡适北上北平,在北大谋得一席之地后,他也开始了改造新北大的计划。1931年到1937年,在胡适的人生经历中自成一个重要的阶段。“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得“国难”临头的北平学术界,无法再专心于学术。胡适等人不得不站出来,为中国的政治出路而思虑。在1932年5月《独立》正式发刊之前的一段时间,胡适等人经常组织一些聚会,来讨论中日争端,并且形成了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些基本主张,经常参加这个讨论的“八九个朋友”,也就是独立社的核心成员,最终自酬经费促成了刊物的发行。这是胡适继《努力周报》、《新月》之后,主导的另一个刊物,而它也深深带着胡适群体的特色和那个时代的烙印。
定期的讨论、聚会,知识分子自筹经费兴办刊物,以及以几个主要朋友为核心开展刊物的日常工作,确实是胡适办刊的一贯作风。在当时维持刊物的运作是相当困难的,陶孟和就以自己兴办《时代评论》的经验为先例,最后他并未加入独立社。然而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独立》以高效率的工作,赢得了巨大的成功。“独立社”社员仅有十一个人,当时排字费用不算太高,胡适和章希吕则亲自负责校对,而撰稿人一律没有稿费,包括外来稿件。《独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发表政见的舞台——胡适亲切地称这个时期为“小册子的新闻事业(Parmphleteeringjournalism)的黄金时代”。第一期《独立评论》只印发了两千册,而一年内发行量已经达到了八千册,两年之内达到了一万五千册,而随着它的影响力和发行量的增加,最初需要社员捐款维持的局面也得到改观,两年后社员捐款停止。到1937年被迫停办,《独立》一共出了244期。它成为当时著名的刊物,其读者群体包括了学生、职员、军人等,并且散布在全国各地。《独立评论》的作者群体主要来自于大学教授、学生、公务员、研究员、中小学教师、助教、报人等各个职业团体,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北方。
正如刊物的名字所宣示的那样,胡适希望保持一种“独立”的批评立场,“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希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这种态度即胡适说的,一方面“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另一方面,“不依赖任何政党,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独立》群体的言论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诉求。在一些根本的政治意见上,《独立》成员基本保持了一致(比如国家应该寻求一个“社会重心”;实现全国的统一;以渐进的社会改良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内部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分歧——蒋廷黻和丁文江都认为中国应该经过一个“独裁”的阶段,而胡适则坚持中国最适合实现民主政治;傅斯年对于胡适等人解决中日问题依靠“国联”支持的言论极为不满;而胡适的“民主幼稚论”、丁文江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和平的言论也遭到《独立》内部许多人反对。《独立》成员确实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胡适还指出,对于公开的政论必须持一种“无所苟”的谨慎态度,“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或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这种一言一举都关系国家命运的自觉的责任伦理,体现了胡适等新式学人群体的“公共意识”,也是对于传统儒家“天下兴亡”道德责任的承继。
一般都把胡适为首的学人群体,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如果“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本质性的定义的话,那么显然给胡适等人贴上这个标签,是大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指称”,而寻求在历史的考察中来不断地规范它、修正它,那么《独立》时期则是胡适一生中最值得注意的。1930年代是一个国家危机的时期,胡适等人逐渐放弃了他们的“个体主义”的立场,而纷纷寻求塑造一个导向现代化的“权威”基础。不论是提出以“建国”、“独裁”,还是一整套理性化的现代制度(如民主、宪政、专家治国、文官制度等)来团结民心,都是出于对“秩序”的追求,甚至不惜在此前提下牺牲宝贵的个体自由。因此,于“独裁”主张最力的,却恰恰是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胡适虽然表面上主张民主,实际却正是出于对“独裁”政治效能的肯定。他的理由是“独裁”是一种要求高度政治知识的政治,而中国政治知识的缺乏,只适合于行“幼稚”的民主政治(详见第四章)。因此,很难想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胡适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斗士,至少1930年代的胡适表现出更多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这也是《独立》的时代主题。关于1930年代胡适的政治态度,学界带有太多的价值和道德评判的意味,而未能很好地表现出对历史的尊重。
另一种看法是过于纠缠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把胡适当作国民党的“同路人”。胡适同时代的其他反对者,已经持有这种看法了。张君劢等遭受政府打击的知识分子,认为胡适是在为国民党的无能而“痛哭流涕”。而建国后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更是为胡适的这种政治角色定了性。确实,胡适在1930年代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的要人保持了密切的关系。1931年底政府财政委员人选的名单上,作为学界的代表,“胡适”的名字赫然与马寅初、顾孟余等同列,但是胡适事先并不知情,这是国民党主动向胡适示好。1933年,胡适与蒋介石会面,并且就中日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胡适与汪精卫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胡适对汪精卫的外交和内政方针,不乏建议与批评。再加上蒋廷黻、何廉等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人们似乎有理由把《独立》群体当作国民党政权的“同路人”。然而胡适曾经激烈地批评过国民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必须把民族主义放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才能保证它不被滥用。胡适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长期的可靠的“社会重心”,这是一切社会改造得以开展的前提,任何破坏这个“社会重心”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即使是借着民族主义的口号而推行的种种激进行为(比如“反日”情绪),都是对一个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有效“秩序”的破坏,从而毁灭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国民党政权正是由于它可以作为知识分子改造中国、寻求“秩序”的基础,才得到了胡适等人的支持。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独立》对破坏统一的“二等军阀”的谴责、对“闽变”的批评、对共产党的驳斥,以及对激进学生运动的失望等复杂态度的背后,所体现出的政治理念。而这些恐怕无法用国民党的“同路人”,就可以解释得清楚。
在笔者看来,《独立》群体实际上是一批“专家政治”的实践者。他们认识到现代政治必须与知识结合。当然,中国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责任,也要求新式学人群体出来为国家做贡献。不过,学者参与“专家政治”的合理性,已经不在于他们是道德理想的化身,而在于他们拥有现代的专业知识和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在儒家秩序崩溃以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已经日益成为现实,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以“西学”知识——建立在专业分科的科学教育之上——来为现代政治服务,就无疑为知识分子找到了可以承担的新的社会角色。《独立》群体大多都有英美留学的经历,而且从前表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农学、工学、文学、史学、哲学、地质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不同专业。他们不仅是现代研究机构、国内主要大学的核心与骨干,他们更在政府教育部、实业部、行政院、国防军事委员会等部门任职,或者担任驻外大使。他们还是当时一些与国际势力有着广泛联系的社会机构的主角(比如“中基会”),因此依靠他们的西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独立》群体构成了一个“权势网络”。这使得他们可以在国民党政府中拥有一席之地,使得“专家政治”成为可能。
2《再生》:国家社会主义与修正的民主政治
《再生》创办于1932年5月20日,同时它也是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创立的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的前身,即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创立的“保国会”以及“保皇党”。民国以后二张跟随梁启超,是“研究系”和进步党的主要骨干,而“保皇会”残余则一直在海外发展,后更名为“民主宪政会”。1946年“国社党”和“民宪党”合并,成立了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二张仍然是该党领袖。“研究系”在民初政治中曾经非常活跃,梁启超虽然逐渐放弃了“保皇”主张,但是其主张宪政的立场却被二张继承了下来,这成为国社党和民社党的一贯标榜。1932年5月,在张君劢等人的组织下,国社党在北平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11位中央委员。其中有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罗隆基、徐君勉、梁秋水、黄任之、诸青来、陆叙百、胡子笏等。该党在北方保持了一定势力,据称其“主要的基础是在大学教授、学者、‘下野名流’。”国社党办的《再生》杂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陈铭枢1930年在这个出版社倾注了大量精力,该社从1931年开始出版了很多“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还办有《图书杂志》、《文化评论》等刊物。在陈的资助下,这里成为政府反对者的集中营,主要是托派分子和AB团的成员,他们在政治观点上即不同于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的统治。
张君劢从跟随梁启超开始,就一直致力于通过组织政党来改造中国政治。在“组党”这一点上,《再生》群体和胡适等人有着重要的区别,胡适一直坚持他不参加任何政党的立场,实际终其一生也未组织过任何政党。所以有人把张君劢、张东荪归入“党派知识分子”之列。然而在1930年代,“国社党”实际上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集合体,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这同改组后的“民社党”有着明显的区别。《再生》一直存在了很长时间,后来张君劢到台湾以后仍然延续了它的刊行,不过1932年—1937年可以说是《再生》杂志的第一阶段,1938年10月《再生》在重庆复刊以后,则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本文讨论的正是第一阶段,即北平时期的《再生》。这一时期的《再生》广泛关注着中国政治的问题,它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和“修正民主政治”的基本主张,成为后来民社党的纲领。这是《再生》“知识讨论”的阶段,1938年以后《再生》所关注的问题则逐渐变为如何展开政治的实践。
《再生》所宣传的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物。1920年代,二张跟随梁启超旅欧归来以后就开始兴办《解放与改造》(后更名《改造》),宣传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他们主要信仰的是“基尔特(Guilt)社会主义”。当时英国的“费边社”是这种社会改造运动的倡导者,他们认为社会改造的力量在于各种产业组织的联盟,因此把“行会”组织视为推行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罗素在中国的演说和他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观察,更进一步推动了这股思潮的影响力。费边社的理论家,如柯尔、拉斯基的著作被广泛翻译和介绍到中国。1920年代张君劢以“张士林”的笔名翻译了拉斯基的名著《政治典范》,柯尔关于社会改造的许多见解,也经常见诸《再生》发表的各种文章中。从张君劢的言论来看,1920年代,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颇有好感;同时作为德国哲学的推崇者,张君劢尤其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在《再生》上他曾对黑格尔的绝对的国家主义大加宣扬,并且因此和张颖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张东荪也继承了德国哲学中强调“精神”实体的一面,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各种社会价值都表现为人类的“精神力量”,民主、自由、公道、博爱成为了一组没有矛盾冲突的概念群,因此他们根本上都合乎人类的理性。苏俄在1930年代的成功,无疑也影响着《再生》的选择,虽然他们极力抨击苏俄的极权政治和财产公有的社会政策,但是对于苏俄的计划经济却试图加以借鉴,张君劢还认为中国的农业改革可以利用苏俄成功的经验,即“农业集体化”模式。德国的国家主义、英国的社会主义以及苏俄的计划经济等因素的混合,构成了《再生》的基本政治主张。
张君劢曾经自述其立场为理性主义与德性主义的调和,“我之立场,谓之理性主义可也。我所谓理性,虽沿欧洲十八世纪之旧名,然其中含有道德成分,因此亦可迳称为德智主义,即德性的理智主义,或曰德性的唯心主义也。”胡适也宣称自己是“理性主义”者,不过他的理性基础则建立在夸大“工具理性”的范围之上,即使是道德的问题也必须由科学的理智来解决。在1920年代“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张君劢显然为理智划定了界限,“人生观”问题关涉到人的信仰和道德领域,因此张君劢的调和论实际建立在“理智”和“道德”的区分之上。张君劢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充满敬意,他在宋明理学中发现了中国精神的核心,因此他在1930年代一直强调从本民族的经验出发塑造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1930年代,张君劢所主导的国社党的宣言,明确了他的立场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国家本位主义,以对抗所谓的国际主义,要求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其二,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对抗独裁政治,他认为民主政治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而无须效仿“独裁”;其三,主张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既反动资本主义的“放任”原则,又不同于苏俄的公有制度,而主张国有与私有的混合。张君劢说,“吾相信一方面承认私有,一方面承认公有,是一条无可逃的大道。但这不是调停两可之词,以后国有实业是应该一天一天扩大,私人谋利的动机是应该大加限制的,必如是,然后能增加民族资本,开发民族经济。”总之,1930年代国社党通过他们的纲领,向人们宣布了他们对塑造有效率和经济自主的国家实体的信心。
3《时代公论》:大学教授?党派分子?
杨公达于1932年4月1日创办了《时代公论》,担任该社社长,当时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并且短暂担任过中央大学法学院的院长。萨孟武和雷震也在法学院兼职。萨孟武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任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雷震也是兼任法学院教授,当时他已经从政,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这三人是《时代公论》的核心成员。《时代公论》的作者几乎都是中央大学教员,主要来自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