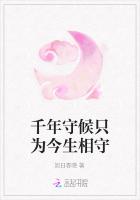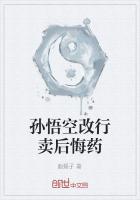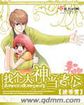姓名教育背景任职政治、社会活动及其他张君劢(又名嘉森,号立齐)留学日本、德国,习政治、哲学大学教授、政治活动家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主要组织者,著《立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张东荪(又名万田,字圣心)留学日本,主修哲学大学教授、哲学家办《改造》,著作《道德哲学》、《思想与社会》胡石青清末旧式教育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1929年组织普产主义协会、著《普产主义大纲》、《中华民族史纲目》邹文海清华大学政治系、35年入伦敦经济学院研究院时任清华大学助教著《自由与权力》、《代议政治》《比较宪法》诸青来(名翔)留学日本,习工商经济大夏大学、持志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公学教授历任“汪伪”交通部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副院长朱亦松专业为社会学上海大同大学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参与创办《新社会》杂志、中国社会学年会蒋匀田〖4〗民主社会党重要活动家孙宝毅〖4〗民主社会党重要活动家武藻池〖4〗民主社会党重要活动家。
资料来源:《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再生》;《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
姓名教育背景任职著作政治、社会活动杨公达法国政治学院、巴黎大学,习国际公法、国际关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时代公论》社长《政党概论》、《政治科学概论》国民党党员,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组织部秘书萨孟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系教授兼主任,中央大学兼任教授《政治学原理》、《政治学新论》国民党党员,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雷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主修行政法学、宪法兼任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舆论与民主政治》、《监察院之将来》国民党党员,1931年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张其昀东南大学毕业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人地学论丛》阮毅成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系主任《政治论丛》、《比较宪法》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叶元龙威斯康辛大学硕士,伦敦大学研究员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梅思平国立北京大学法律科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系教授曾任江宁模范县县长,后在“汪伪”政府任实业、工商、内政部长等要职傅筑夫北师大国文系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史论丛》何浩若斯丹佛大学学士,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博士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楼桐荪法国巴黎大学法科硕士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均权的理论与实际》田炯锦美国伊立诺大学博士,攻读政法国立东北大学教授《联邦制度概论》章渊若复旦大学、留学巴黎大学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其保韩林大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博士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行政学教授《教育法概论》杭立武威斯康辛大学硕士,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政治学博士,师从Laski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教授《政治典范要义》中国政治学会发起人,1932年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
表中“职务”一栏只说明该作者在《时代公论》发表文章期间,曾经担任过中央大学的职务,并未将他同时期担任的所有职务全部列出。“著作”一栏列出的是该作者一生的代表作,“备注”部分也列出他生平值得注意的经历,并不仅限于1930年代。
资料来源:《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时代公论》;《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法学院概况》(中央大学,民国十九年)
《时代公论》是大学教授讨论政治的公共舞台。正如短暂担任该社总干事的张其昀所说,“《时代公论》,公器也,大学教授之公开讲座也。大学既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大学教授所发表之言论,自不受任何政党之拘束。既在同一刊物之中两相反对之论调,苟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暂不妨同时并存,而一任读者之比较选择,此其所以名为公论也。”除了法学院的教授为《时代公论》的主体之外,中央大学其他学院的教授也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张其昀当时是理学院地理系的教授,已经在史地研究方面暂露头角,在中央大学期间,他多次到西北等地进行实地的研究考察,关注祖国的人文地理变迁。张其昀的论作最终汇集成《人地学论丛》一书,1932年由《时代公论》社出版。当时,杨公达任《时代公论》的编辑人,而张其昀任发行者,但是在杂志发行到18期以后,张其昀因为忙于创办钟山书局,而辞去了在该社担任的职务。柳诒徵和缪风林是文学院史学系的教授,程其保是教育学院院长。他们也都在《时代公论》上撰文,讨论中国的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中央大学法学院聚集了当时国内一批非常知名的政治学家、法律学家以及经济学家。1928年法学院成立时,其下设三个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以及经济学系。1930年,政治学系有钱端升、刘师舜、崔宗埙等人;其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的马寅初为经济学系的主任。阮毅成为法律学系的主任,他对宪法和法学的理论都颇有研究,《时代》社先后出版了他的论文集《法治论集》和《政治论丛》,胡长清则是刑法学方面的专家。杭立武于1930年任政治学系的系主任,他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曾师从著名的费边社政治理论家拉斯基。回国后,他大力宣传拉斯基的政治学理论,在《中央大学法学院季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介绍拉斯基的学说。他还于1932年接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并于同年9月促成了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的正式成立,这对于促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和中央大学以及《时代公论》社有着重要的关系。学会在最初15年里,由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扰乱,故而也较多关注实际的问题,比如外交政策、地方行政、宪法草案、非常时期国民教育、政治机构改革、地方自治研究、改进吏治等,这正与《时代》关注中国政治现实的宗旨相合。虽然存在时间比较短,《时代》也曾就上述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楼桐荪的著作《均权的理论与实践》、田炯锦的著作《联邦制度概论》都关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时代》还专门讨论了国民代表大会和宪法草案等问题。
然而正如上表所示,《时代》的核心成员,如杨公达、萨孟武、雷震等人本身又是国民党员,他们发言的立场很明显站在国民党的一边。杨公达后来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党部秘书,萨孟武后来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尤其是雷震在1926年冬回国后,开始从事政治、接近各种政治要人,先后在法制局、南京市党部、教育部、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担任编辑、秘书等职,由于他能纵横捭阖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因此后来被称为“各党各派”之友。阮毅成也在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任上,大展身手。梅思平后来在“汪伪”政府的实业、内政等部任部长。可见,《时代》的核心成员都有在国民党党部和政府供职的经历。从他们的职务来看,阮毅成和梅思平曾担任过一些实际的职务,杨公达、雷震则更多的是充当政府官员的幕僚,以“智囊”的身份为国家政治出谋划策。
《时代》成员大多是国民党党员,他们主要从国民党的立场(而不是国家立场)出发来看待、思考中国的问题。因此,《时代》群体与胡适为首的《独立》群体同样是“参政”,却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杨公达等人大都是国民党的党员,他们一再强调,国民党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并积极地实现“自救”,然后才能挽救国家的危机。但是胡适等人的参政却更多出于国家立场的考虑,是在民族危亡时期出来为国家做一些事情。这些当时颇有影响力的知识精英,大多都不愿加入任何党派,由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考虑,进而认为“中国现在要有政府”(傅斯年语),从而支持国民党。这是两种思考中国政治的不同路向:一种从党的生存利益出发,进而及于国家的改造,因而以党在国家之上;一种以民族存亡为出发点,要求建立国家的秩序,认同党为改造国家的工具。蒋廷黻曾批评这种“党在前而国在后”的“训政”思维,是把中国当作小孩子,而以国民党为保姆,认为应该严格区分党的制度和国家的制度。胡适在汪精卫的一再要求下也不肯进入政府,一方面固然有其为国家考虑的因素,“我细细想过,我终坚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并表示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但更明确的是他始终持一种党外的立场。
与其他几个主要思想界的刊物集中于北方不同,《时代》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体现出南京思想界截然不同的取向和对政治的理解。当然在支持国民党的态度上,《时代》似乎趋向“保守”,但是对于“独裁”政治的公开倡导,却不能视为其“保守”的理由。《时代》群体也不同于主要有着英美留学经历的《独立》群体。他们留学主要在三个国家:萨孟武和雷震都在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攻读过法学;杨公达、阮毅成、楼桐荪、章渊若留学巴黎大学;叶元龙、何浩若、杭立武则属英美派,而且主要学习的是政治学或经济学。《时代》的核心言论大体出自前两派人之笔,他们的专业都是法学。法国和日本的留学经历,以及法学家的背景,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言论。杨公达和阮毅成与萨孟武似乎都受当时“主权多元论者”影响。同时,他们主张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应该采取不同政体,并不存在普世的善政,则明显带有孟德斯鸠的色彩,因此他们认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改造政治,而不是马上实现民主政治。这被信仰民主、宪政的反对者,称为“实际主义”(详见第三章)。这些思想都明显受到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理论的影响。
4《大公报》与《国闻周报》:“社会舆论”的承当
讨论1930年代的思想界,自然不能忽视《大公报》和《国闻周报》的言论。如果说以上讨论到的刊物主要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那么《大公报》则主动承当起了“社会舆论”的角色。《大公报》在1926年9月复刊的《本社同仁志趣》中,吴鼎昌强调了他的办报宗旨,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而1944年吴鼎昌也指出,办报的目的在于“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强调了它“为了人民全体利益”的公共的立场。从《大公报》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基本上保持了这种“独立”、“理性”、“公共”的舆论地位。
这家由私人出资兴办的报纸,在复刊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成为了全国知名的“舆论”汇集所在。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是报纸的创立者,吴氏最初投资了50000元,并且主要负责报纸的经营和管理,张氏和胡氏则专心办报。胡政之曾经主持《国闻周刊》,1926年“大公报新记公司”成立后,原来胡麾下的《国闻周报》和“国闻通讯社”便成为了《大公报》的附属机构。“国闻通讯社”曾经同“安福系”有着密切联系。《国闻周报》存在了13年,出版了14卷,每卷50期,发行最多时每期达到了1.5万份,在当时是出版时间最久、发行量最多的新闻周刊。《大公报》和《国闻周报》实际是一家,它们互相促进、互相依赖,其发表的文章基本来自同一个作者群体。
1930年代是《大公报》最重要的发展时期。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发行满一万号,国内外政界、知识界、新闻界的代表都发来贺词。胡适在文中称赞道,《大公报》虽然起步很晚,“比起那快六十岁的《申报》和那快五十岁的《新闻报》,真是很幼稚的晚辈了”,但是它却无愧“全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这真是“后生可畏”了。他希望大公报再接再厉,在世界最好的报纸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1936年《大公报》复刊十周年的时候,开辟了上海分社,津沪合计日发行量已经由1926年的2000余份达到超过十万份,并行销除东四省以外各省1300余处,《国闻周报》亦由两千份增加到两万余份,该社资产价值已达四十万元,而且在人员削减的情况下由最初的亏本逐渐转为盈利。1941年,《大公报》由于它的卓越贡献,荣获美国米苏里奖章,这使得它可以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世界知名报纸相比肩。正是有了独立经营的实力和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大公报》的言论才能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并且对政府的行为有所监督。
1930年代面对着“国难”的日益紧迫,《大公报》和《国闻周报》充分承担了为国家政治寻求出路的社会良心。之所以选择它们讨论193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状况,而不是其他同样有影响力的报纸(比如《申报》),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系统的关注。它们探索了“国难”之际国民和国家应尽的义务,讨论了国家的宪政问题,参与了民主和独裁的论战,对于统一、地方制度、行政效率、国际形势等问题都有所涉及。这些讨论主要反映在《大公报》的“社论”和它的“星期论文”之中,《国闻周报》也主要以讨论国家的政治问题为核心。《大公报》的“社论”坚持每天一论,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同时又能跳出就事论事的俗套,体现了敏锐的洞察力和主笔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关怀。最初“社论”基本上由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包办,“九一八”以后杨历樵开始写一些国际问题的社评,此后王芸生、曹冰谷、张佛泉等人开始参与到写“社评”的队伍中来,这增加了“社论”的专业含量。王和曹是《大公报》第二代的主要领导者。王对于中日关系颇有研究,曹则在1930年代初到苏联游历,写了关于共产主义的许多报导,张是美国留学归国的政治学专家,他负责国内政治改革的评论。
《大公报》还通过兴办形式多样的副刊,起到了与学术界沟通,并且向社会普及知识的重要作用。《大公报》的专业副刊有先后有20多个,包括了《科学周刊》、《社会研究》、《世界思潮》、《经济周刊》、《军事周刊》、《文艺周刊》、《图书周刊》、《史地周刊》、《乡村建设》等。这些内容丰富、专业性与普及性兼备的副刊大多由学术专家来负责编辑,比如“南开经济研究所”负责《经济周刊》,何廉等人举办的著有成效的中国经济调查和研究成果,在《大公报》上与读者见面;张其昀负责的《史地周刊》于史地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科学周刊》由清华大学的夏坚白等人编辑;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张申府主编了《世界思潮》;梁漱溟则是《乡村建设》的负责者,主要探讨中国乡村的改革。可以说,《大公报》是依靠知识分子的一份报纸,它联合了舆论界和知识界的力量。
1934年1月,张季鸾提出了创立“星期论文”的想法,他希望每周能有一篇社评由外面的专家学者来撰写。1月7日,胡适的第一篇“星期论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发表,此后除非有特殊情况,“星期论文”每周都按期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