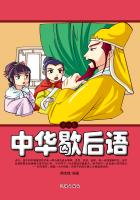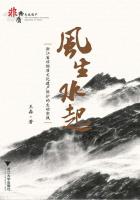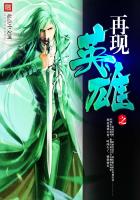斯诺的“施乐”显然根本不同于一般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猎奇态度,他把异质的文化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也把自己放在和中国人对等的地位上。由此,他才会同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息息相通,对中国怀有的感情与日俱增。1932年,他在《中国洪水末记》一文中写道:“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它怀着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它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与苦痛,它们沉重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难过已极,无法控制。在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美好,性格是如此坚强,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来恢复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谁都不会怀疑,那是他的真情表白。
伟大的尝试
斯诺这种深厚的感情绝非通常的悲戚或怜悯。相反,随着他的不断探索和认识的深化,他已经能从黑暗中略约窥见未来的一线光明,从纷乱如麻的社会现象中预感到某种历史的前景,观察到了争取斗争胜利的前程。1936年在英国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本书的编辑问世,表明他已经由中国社会的表层深入到文化思想领域进行探讨。这种探讨使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也表明旧中国黑暗丑恶的现实并没有使他丧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信心。
《活的中国》从编辑到出版,是斯诺与中国五四以来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与运动中涌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积极沟通,也是中美两国文学和文化交流史灿烂的一页,它凝聚着以斯诺为一方、以鲁迅为另一方,所代表的中美文化在新形势下互相加深了解的伟大心愿。
《活的中国》是斯诺编译的一本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作为新闻记者的他为什么要编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呢?原来,斯诺在深入探索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很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现状,了解他们在作品中如何反映现实生活的。但令他困惑的是直至1931年,都未找到这类文学书籍的英译本。他发现,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文学”尤其不为外国人重视,即使被译成英文,也只是一鳞半爪。有鉴于此,加上自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集中在短篇小说的领域,斯诺决定亲自动手编译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
由于鲁迅是公认的“白话大师”,作为小说家深负盛名,当时又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精神领袖,斯诺打算先翻译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及《呐喊》中的其他篇目,然后再选择新文学运动以来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优秀短篇作品。斯诺的这一编译计划,得到了鲁迅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作。为使斯诺深刻了解《阿Q正传》等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创作意图,鲁迅曾与斯诺进行多次的交谈,正因为有了深切的感受并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斯诺才写出了《鲁迅——白话大师》这样评价鲁迅的生平思想与作品的出色的文章,并在文章中对阿Q这个典型作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鲁迅也应斯诺之邀,特意于1932年3月22日为编译中的选集写了《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并怀着喜悦和谦逊的心情说:“自己的短篇小说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鲁迅还为这本“选集”的编译,主动配合做了许多工作。他还对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中涉及到的史实和看法提出了十多条具体的意见,供斯诺修改时参考。
斯诺没有辜负鲁迅付出的精力和心血。为保证译文的质量,请了位合作者姚克,以崇敬的心情、严肃的态度,积极认真地对待作品的编译工作。虽因种种原因,所译鲁迅作品最终未能按原计划出版,但数年以后,却以另一种形式辑入《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一书内,于1936年秋天在英国伦敦由乔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此书除鲁迅小说外(《阿Q正传》可能因翻译有困难未收入),还选录了中国其他现代作家的小说。斯诺撰写了“编者序言”,书末另有两个附录:即《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和“参考书目”。
斯诺为编译中国现代小说选集,前后持续了约五年时间,耗费了许多精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在“编者序言”中坦率地说:“倘若事先能够充分地估计到编译这个集子需要呕这么大的心血,耗费这么大的精力的话,我绝不敢‘贸然’进行的。请读者们相信,我宁愿自己写三本书也绝不愿再煞费苦心搞这么一个集子。”但书最终还是问世了,可见斯诺对五四新文学是如何重视与关心。
无疑,这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英译本的出版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斯诺希望西方世界广大读者通过阅览此书,“至少可以了解到这个居住着五分之一人类的幅员辽阔的国家,经过几千年漫长历史进程而达到一个崭新文化时期的人们,具有怎样簇新而真实的思想感情”,“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而所谓“活的中国”的“灵魂”,也就是“正在改造着中国人民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
《活的中国》除重点介绍鲁迅及他的作品外,还精心选择了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沈从文、丁玲、柔石、萧军等几十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他们大部分属于30年代左翼作家。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以多样的风格,逼真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无论是反映农村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控诉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还是描写城市小市民庸俗麻木的变态心理,揭示现实生活的严酷与不幸,抑或是表现“九一八”后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痛苦遭遇,或者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人民的毒害……都使斯诺不但“看到了一个被鞭笞的民族的伤痕血迹,还看到这个民族倔强高贵的灵魂。”斯诺的序言说,他全神贯注于“传达每一篇作品的精神实质,是诠释而不是影印复制;不但表达原作的感情内容,而且还想烘托出存在于这种感情深处的理智信念”。他特别着力于发掘作品中的“根本观念”和“它们对中国命运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斯诺才觉察到当时中国的文学运动深入发展的意义及前途。他作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预言:
任何人在中国用不着待多久就会体会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再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旧的文化。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的信仰遭到了摒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了出来。到处都沸腾着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
这就是“活的中国”的真谛所在。在表面的动荡不安下,在伟大的文学艺术里,正在萌动和孕育着强有力的新的文化,它是中国赢得对内对外斗争之必需。一个外国人,如此准确地把握住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的命脉,的的确确难能可贵。
奔向红星照耀的国度
从身份特殊的“高等人”的位置上走下来,转而面向中国的真正的实际,在这过程中斯诺也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影响和推动,许多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进步人士都给了他鼓舞和力量。这正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其中因编译《活的中国》而结下交情的鲁迅是给他推动最大的人。据斯诺自己说,恰恰是鲁迅,对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那些将军,再去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永远思考和研究。”后来他对友人再次提起过:“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另一个令他难忘的人是宋庆龄。《活的中国》就是题献给宋庆龄的,献词这样赞美她:“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也肯定说:“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的榜样。”
在左翼进步势力的直接影响和指点之下,斯诺不再局限于城市的狭小范围,开始关注农村广大地区的革命潮流。时隔不久,斯诺便毅然下定决心,于1936年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奔赴红星照耀的另一片国度——陕北革命根据地。
斯诺此行意义重大。一是打破了中外舆论对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长期封锁,正如他在为《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写的序言说的,“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但“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们的经历”。斯诺是西方人中的第一个自告奋勇者,他的采访结晶《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翔实地报道了红色根据地的情况,澄清了各种污蔑不实之词。二是让中国和中国人看见了希望。长期以来西方预言家们便认为中国人注定作为一个“无望的民族”生存下去,30年代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甚至武断地宣布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人民已经无力自救。斯诺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红色的中国,相信它是中国的未来,也让所有关怀中国命运的人树立了同样的信念。三是接触和了解到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建立在农业经济之上的乡村文化及其主力军,即广大农民。中国的现代进程正因农民革命运动的加入而增加了许多新的成分、新的可能和新的问题。
1936年6月,斯诺由北平出发经由西安,冒着生命危险,历经长途跋涉,千辛万苦,进人了陕甘宁边区。他的采访单开列的问题多达70余项:为什么是共产党而不是别的政党,为什么是当时势单力薄的红军而不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承担了在中华民族历史危急关头挽救民族的重任?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的战士为什么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能克服无法想象的困难,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历史性长征?他们的领导人是谁?毛泽东是怎样的人?他那价值25万银洋的东方人的脑袋里究竟有些什么名堂?红军采用什么战术?中国农民是否支持苏维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能成功吗?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中心问题是:1936年,“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这本书1937年10月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7次,销售10万册以上。世界各国的重视和世界读者的欢迎出乎斯诺的预料。世界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杰作,在西方了解中国方面开启了一个时代。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明,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的主要来源,《红星照耀中国》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老百姓,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使西方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难怪赛珍珠认为斯诺的这本杰出记事的每一页都很有意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看过《红星照耀中国》后,曾三次接见过斯诺,还亲自推销过斯诺的著作。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不无自豪地说:斯诺的书一经问世,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无稽之谈统统烟消云散,斯诺的书拥有崇高的声誉。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10年之久。他从大量确凿的事实材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地说,(中国社会)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做希望和自由的象征。”他热情洋溢地称赞“红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最优秀的军队”,“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战士”。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这个远见卓识的预言超出了一般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观察家的眼界,是斯诺独特的发现。
《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魅力,在于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忍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正如斯诺自己说的,这本书“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这些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斯诺曾经申明,《红星照耀中国》“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但是,作为真实的见闻的记录,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一部中国革命的史诗而长垂史册。斯诺公正客观,但绝非无倾向性的出色报道,令中国多少热血青年为之神往而投奔红色苏区;使国际上多少有识之士因而走上了终生与中国人民友好的道路。这些人命运的改变,曾经引发和衍生多少离奇而动人的故事!由于《红星照耀中国》产生的广泛的积极作用,甚至影响到国共两党及其拥护者力量对比的消长,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二战后中国政治力量乃至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