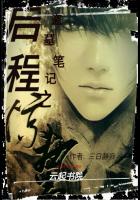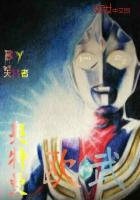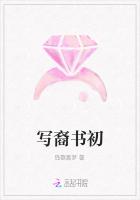说起王正功就不得不追溯广桂一带的文化渊源。桂林地处岭南,层层阻隔,挡住了不少文化溪流的脉动。历代统治者又多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派驻的中原官员并不多,桂林之地的文化启蒙就被耽搁了不少年头。到了唐代之后,派驻或贬迁桂林的官吏数量大增,广桂一带与中原文化就大量地自由流通起来。这些“中州伟人硕士,或迁谪之经从,或宦游之侨寓”,与桂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桂林大量的山水诗精品就出自于这个时期的贬遣名流们。诗人的不幸成了桂林的幸运。许浑留诗曰:“桂州南去与谁同,处处山连水自通”;张籍也曰:“旌旗过湖潭,幽奇得遍探”……诗人们对桂林山水的审美自觉一直延展到了今天,桂林山水魅力不减。
若桂林只纳山而拒水就无从构成完整的桂林印象。看水就要看把广西盘得妩媚且活泼的漓江水了。漓江发源于桂林北面兴安县的猫儿山,流经桂林、阳朔、平乐至梧州,汇入西江,全长437公里。从桂林至阳朔一般漓江被誉为“百里漓江,百里画廊”。
初冬入漓江,水明显清瘦了很多。沿岸水太清浅,大游船靠不了岸,坐着撑杆小船才能至大船。有水的簇拥,漓江的山又风味了很多。游山如游史,观水如观画,唐代的韩愈一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成了漓江山水最响亮的广告词。陈毅老总在桂林山水的“贿赂”下可爱地说了句“不愿做神仙,愿做桂林人”,让桂林老百姓感动至今。
挥毫当得江山助,重庆的雾,北京的秋,上海的夜,桂林的雨,都是风景物什中的经典之作,与桂林之山齐丽的漓江水最值一提的便是水中倒影。漓江山水就揣在了我们口袋中,20元人民币上印着的就是漓江光影大成之作“黄瀑倒影”。喀斯特地形造就的桂林山石坚硬且色泽丰富,黄瀑即涓涓细流千百年来刻印在黄色岩壁上的写意画,写意画映在漓江水中形成黄瀑倒影。山水相交,水影相连,亦幻亦真的漓江影之美在于活水,影入水中,水动影不动,静态的影隔着动态的水看过来,更体现出漓江外山内水、外刚内柔的品质来。
山水间活着的生灵也不尽相同。浅岸边的妇女在青石块上千百年如故地搓洗着衣裳;浸圆了肚皮的大水牛咻咻地拱着牛犊子往水中赶;成群的鸭子在水中自由泳着嬉戏,船过来了,它们很绅士地拍拍翅膀让开水路;扎紧了脖子的鸬鹚站在竹筏子上还在微笑。
以人类的理解,多劳少得的鸬鹚微笑颇费思量。没等你思量明白,心思便被一条条狭长的小竹筏子冲撞得七零八散。六根竹子排成的筏子上站着赤了脚、挽高了裤腿的筏工。筏上会有二三个大筐,里面装着各种廉价的玉石工艺品或柚子、香蕉之类的水果。漓江筏工操着拍卖行的语气与大船上的游客你来我往地交易着。小筏子钩挂在轮船两侧的备轮上,服帖地顺着大船流淌,筏工就能全心全意地观察游客的眼神推销自己的货物。一旦成交,筏工会像猴子一样用赤着的双足攀在船舷上,将货物递出,将钞票收回,精彩如同水上杂技演出。数十分钟后,筏工觉得此船的生意已饱和,解下挂钩,任大船逍遥而去,自己再去捕猎另一条大船。
如此的交易场面,还真成了漓江游中的一幅风土人情画。这风土人情也该是世风已久的。桂林山水在以旅游胜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之前,城市特征带有浓重的政治、军事、经济色彩。桂林是岭南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水路与陆路交汇,枕山带水,地势险要。在统治者眼中桂林是一座“地压坤方重”的军事重镇。另外,当时的桂林“所处延海,多犀象珠玑、奇珍异玮”,魏文帝“谴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由此可见桂林曾有的经济意义。筏工们的“竹筏商旅”也许就是桂林曾有过的贸易辉煌的烛光杯影般的现代写意。筏工的艰辛与适者生存之道让人看清楚了鸬鹚还能微笑的深意。
现在桂林城中最大的一家商厦叫“微笑堂”,是中日合资的。两个微笑,一个是意会,另一个音译,外在的解释应该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但通用的感觉却体现出桂林人内在的性情。桂林人自古至今就懂得微笑的内涵。他们浪漫得很,地名景名上不时就蹦出了七星岩,象山水月、月亮山、花轿虹影等星啊月啊的名字,这是山水滋养出来的怡情怡性。
桂林城中的商业步行街上有店铺、书店、小商品。在天下城市大同之余这里比别处多的是笔墨纸砚的叫卖,以及为数不少的画廊。画廊作品内容多是就地取景地框住了桂林山水。一幅以中国工笔画就的漓江山水图上署了这么句名言:我到过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城市,没有一个像桂林这么美丽的——尼克松。
我哑然失笑这中西合璧的幽默。
桂林山水间也存在着种种冲突,像是潜伏在许多人心间的《我想去桂林》那首歌词中表达的那样,金钱与时间并着诙谐与无奈。她的城市建设、她的环境保护、她的发展定位都在不定性的冲突中摇摆着。桂林奇特的山水促进了文化名城的形成,悠久的文化又充实了山水的人文内涵。桂林站在很高的起点上,承受着更多的瞩目和压力。这也许是桂林在美丽的冲突间需要重新去想象的理由,这也许就是攒出了时间和金钱后必游桂林的理由。
池莉笔下的汉正街、吉庆街
未到武汉之前对武汉的了解基本上限于从读池莉、方方等武汉籍作家以武汉人为背景的小说中得到的印象。
一旦有了印象,人的本性都好于去印证一番。虽然知道小说本是高于生活的物什,但那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冲动是压制不住的。到了武汉必经长江大桥,必不放过黄鹤楼,必要去汉正街、吉庆街徜徉一番。精雕细琢地挤出了“瞻仰”汉正街、吉庆街的日子,正赶上武汉雨季中的艳阳天。四月底的这一天,温度已达32摄氏度。经过咨询,筛选掉了借汉正街名头兴起的经营家装、饰品市场的汉正西街,直奔现名为汉正东街的正宗汉正街。
骄阳下的汉正街赤裸裸的,虽是店铺连店铺,摊位靠摊位,但内容不复杂,像是能一眼望穿。经营的无非是些毛巾、袜子、内衣、箱包之类琐碎之物。失望之余左顾右盼,发现其街的外延早胜于主街。像是一棵并不粗壮的树干却发出了过于繁茂的枝桠,随意盘根错节,任性四方发射。于是着意往一条小巷子深入,倒是店铺鳞栉有了些像样的品牌店或仿品牌店。
汉正街占尽了服装集贸市场的名气,支持了它好酒不怕巷子深的“脾气”。它的品牌、精品店铺躲在巷子中,碎货、杂货小铺子倒是称霸主街,显现出了它独有的特色。所有的巷子宽不过两米,曲曲折折的因为巷巷相通,巷巷相套,让人理不清它的始终。
汉正街最初本就是自发而成的集市,“自发”二字在这里发挥得很是尽兴。童装、女装、男装、绸缎铺任意组合,高价、低价、跳楼价处处搭配。若拿购物眼光来看,庞乱杂芜的风格并不讨人欢欣,但若拿领悟、察风的心情品读,这的确是个让人可晃晃悠悠走着,随性抻抻拈拈布料,随心挑挑试试的好去处。
汉正街的服装经营者大多数是从经营沙滩裤、大汗衫起步的。经过了时间的积累、艰辛的积累、金钱的积累,个个练就了见过大世面,得之不喜、失之不惊的气质。所以你去到哪家店中都不会出现拉着你不放,夸得你脸红,过于热情的场面让人松松垮垮着舒心得很。
千万别拿品味、档次来品评汉正街,它不在这个范畴内。于是想起了若干年前拍成电视剧的《汉正街》中的镜头,那挤挤拥拥的人群依旧,但声嘶力竭地叫卖、喧哗却少了很多。这也许是汉正街走向成熟的一个侧面特写吧。
汉正街也有些很“武汉”的小吃,但提到“名头”二字,咫尺的吉庆街小吃更有名头,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原汁原味。有人说来武汉不进吉庆街不算来武汉,这大概是武汉市文联主席池莉在小说大肆宣扬的结果。她的笔下太热恋于这条长不过百米的巷子,太熟识这里的一颦一笑。看多了,没来过也觉得几百年前已相识过。
“天下名街,容陶汉韵楚风;江上闻楼,春醉市声门调”吉庆街街坊的对子既大气又抒情,我很是喜欢。“春醉”二字的确点出了些许心情。
本意是用眼睛和肠胃来消化吉庆街的,却意外而有幸地遇到了吉庆老街发展的见证人之一——江运生老先生。由央视张鹏编导的荣获中国纪录片金奖的《吉庆老街》中,江运生便是片头中的解说人。江运生经营着一个有二十余张桌面的大排档,是吉庆街的一个老字号。坐在他的大排档中,“来双扬的辣鸭颈”“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臭干子”“玉芳斋的糊米酒”一一上来(这些仅是武汉十二名吃中的一部分)。吉庆街的大排档多以酒菜为主,你钦点来的小吃若本排档中没有,老板会从临近排档中将最正宗的小吃端来。他们这种客源上竞争激烈,经营中互通有无、融江贯通的方式是吉庆街每一个摊位都得以高朋满座的原因之一。
江运生很善谈,吉庆街的音容笑貌便在眼前一一展现开来。
追溯起来号称百年的吉庆老街,街的历史早跨越了百年。追随詹天佑修筑铁路的众多随从、工役到了武汉被滚滚长江水滞留下来,这些“见过世面”的工人们多成为武汉早期的小商家。为了应付武汉火炉样的气候,住在吉庆街的人家习惯在各自家门口泼水降温,然后再把家中最好吃的食品端出来吃着“卖杠”(意为显示自己家境好)。暂时的凉意与“卖杠”的虚荣让吉庆街的先民们很惬意。可外地客人却吃不消武汉的暑气,饭菜不香。到了晚上十一二点,外地客人终于饥肠辘辘了,看到了“卖杠”的先民们的美味吃食,都想掏钱买些“杠”吃。外地客人想吃的念头刺激了吉庆街先民们的经营意识,于是“卖杠”出让成了现吉庆街“大排档”的前身。之后,大排档又经历了“挖地脑壳”阶段,(这种称呼是武汉的方音,也是吃夜宵的意思)再往后叫夜市。在这一阶段,那些“卖杠”人把武汉地方口味,修铁路人的智慧和外来人东南西北的风味东西合璧,左右逢源,逐渐形成了吉庆街的“武汉味”,形成了今天一气呵成的“大排档”。
吉庆街是一个惊叹号。在热热闹闹中简短,在红红火火中创造感叹。池莉笔下“来双扬”住过的破旧二层楼,十四年前也被市政府拆迁,取而代之的是“吉庆家园”。不宽的街市上矗立着六七层的楼房并不碍眼。房价均价为每平方米2180元,楼下门面房每平方米1万元。住户是吉庆街上的老经营户,卖艺的、唱歌的、卖花的、擦皮鞋的。倒别小看了他们,他们个个腰包都很殷实,他们是吉庆街流动着的风景,是吉庆街的文化。但听说“吉庆家园”入住率并不是太高,恐怕是吉庆街的主人们不想工作、生活都囿于同一寸土地上吧。
吉庆街三十多位老板,四百余名伙计,再加上应有尽有“流动着的风景”,百余米的街滋养着四千多人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吉庆街真正的生命是从午夜时分开始的。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地人一下飞机、火车,先扎在宾馆中大睡,到了午夜才驱车前来吉庆街吃村味。所以吉庆老街在没有夜色中尽显夜色。上半夜外地人喧哗,下半夜武汉人享受,吉庆街老板们深谙这个规律。所以上半夜使出浑身解数招徕八方来客,越是独特、怪味的小吃越上座。到了后半夜熬不过的外乡人带着“春醉”走了。需要打麻将的,需要找刺激的,夜不成寝的武汉当地人就三三两两地延续着这种热闹,直到东方泛白。据说武汉市的商贸洽谈多是在这条嘈乱的吉庆街上谈成的。武汉的大老板们用吉庆街不上桌面的小吃,用吉庆街的吹拉弹唱套牢了一宗宗的大生意,奠定了吉庆街不凡的社会经济地位。
在你品食各种小食品时,卖花姑娘会悄悄地走来,介绍你买束鲜花,买点心情;吹萨克斯、拉二胡、拉手风琴的会殷勤地为你递上曲目单;唱京剧、唱豫剧、唱越剧的会用剧中的动作给你唱个诺,道个安。这样,常常是左耳萨克斯曲,右耳京剧调,演奏者有收入不亦乐乎,听者长见识不亦乐乎。
江运生很有人缘地为我们邀请来了吉庆街的腕级明星四大大王中的三位:乡土派麻雀、专业派老通城、偶像派吕文礼(另类派潇洒已离开吉庆街)。这些人可不仅仅是吉庆街的品牌。乡土派麻雀的资料在音乐网上可随意点击,现场填曲、即兴改歌词演唱的风格胜过香港红星脱口秀张帝几分。央视、武汉市春节晚会上他曾是座上嘉宾。演艺界的雪村、杨钰莹、毛宁都曾经要拜师其门。老通城是从湖南省歌舞团出来的萨克斯手,红遍老街,曲价听说也是包中殷实者才能享受得起。偶像派吕文礼是老通城的黄金搭档,帅帅的长相在莞芜的街灯中一样的耐看。实在的麻雀拉着二胡即兴唱道:“你们是时代的楷模,不远万里来到武汉,收获可否多;你们的兢业让我钦佩,知书貌美让人舒心很多……”
吉庆街的卖艺人早已提前跨入了小康行列,他们的许多东西像我们眼中所见到的那样都与吉庆街融为了一体。这种丝丝相扣、不舍不弃的意味延绵着吉庆街的风情。
江运生大排档对面的白毛大排档听说是池莉小说《生活秀》中来双扬原型李琼经营过的摊位,所以排档外立的是电影版《生活秀》中演来双扬的演员陶红和李琼的合影。我也追星一样留下了照片。
夜已很深,必须打道回府。与江运生道别后,迎面又来了招揽客人入席的小姑娘。她甜甜笑着说:“请进来尝尝我们的小吃吧,我给你找张清静些的桌子。”
“吃过了。”我好心情地表示歉意。
“那下回来吃吧!”小姑娘依旧笑意盈盈。
像是百年老街的笑意!
胭脂峡的孩子
亏了这群孩子,胭脂峡才能在我记忆中活泛起来。
入峡口不足百米,一个黑黑瘦瘦穿着件灰蓝小褂的十多岁女孩有些怯怯地迎了上来。走近了,小女孩双双的眼睛很大,鼻梁也挺挺的,灰蓝小褂还是件牛仔上衣,脑后扎了个小辫辫。城市、农村的孩子的外貌特征上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城里十多岁的小姑娘也是牛仔衣,马尾辫,但洋气十足的,眼前的这个孩子憷憷而言,找不到城市孩子常见的那种飞扬跋扈。
一时不知女孩的真实目的,打量着小女孩被晒得黑黑肤色中滋着汗的亮。
“阿姨,我给你们当小导游吧!”小女孩终于开口了,一开口就让我们的队伍又惊又喜。
“你会导吗,要多少钱?”
“我会,我天天跟着大人导游听,就学会了。外面一个大人导游要50元……”小女孩话语间羞怯中透着老道。
大家主要是新奇,没人见识过这么年轻的毛遂自荐者:“给你十元钱给我们导一趟吧,有个领路的还是好”。小女孩迭声地应着,眼睛中闪着欢呼雀跃。儿子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闯进队伍的小姐姐,并很快与其熟络起来,他还不懂得我们之间大概只是一种经济往来。
快到第一个景点,在一山弯处我看见一个更小的农村女孩子正在用野花编花环。她臂腕上套了两个编好的,一双小手飞快地编着第三个花环。多美的花环,白茉莉花一样的花头攒动在黄绿黄绿毛桠桠的枝条、叶片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