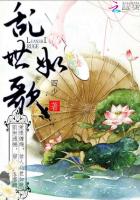用系统论的观点讲,社会是一部大机器,一个单位、一个人只是部件。也可以说,宇宙是一部大机器,太阳系是它的部件。我们肉眼观察,心灵记忆,太阳这个部件比人还听话,自觉性很高,主动发光,时时不息,不怕辛苦。人就不行了,难免想跳出规律,以此惊天动地。不受规律约束,不做自觉配合,作用就会抵消,效果就会削弱。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一致公认的最高奖项。其中有一篇获奖作品是《尼克松访华》。这当然是写一个重大事件,是一个重大题材。文章的主题是尼克松当时说的一句话:“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现在重读,回首当年往事,会感到历史有沉重的一面,也有令人振奋的一面。然而,这些“重大”,在我脑子里几乎隐退得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印象最深的却是两个小小的细节:一是尼克松为周总理脱大衣;二是当尼克松总统的专机起飞后,周总理仍然在停机坪上同美国的特派记者们开着玩笑,又聊了10分钟,这使他们很惊讶。
以事论理,以理论事,这两个细节,不是文章的主题,只是配角。人事也一样,很多时候,配角同样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或者尤其深刻的印象。当好主角固然不易,当好配角更为难能可贵。既当好主角,又当好配角,使一部机器正常运转,才是正确选择。
主角和配角不是固定不变的。就拿我们农委来说,此项工作甲科室是主角,彼项工作乙科室就是主角,甲科室转化为配角。我讲这些,也应该适合于县委办公室,适合于乡镇的同志。我在办公厅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当科长只管一个科,当副主任、副秘书长就有意识让分管的几个科室协同作战,效果很好。当了农业局长,管三十多个科站,能较充分地贯彻通力作战的思想。一个主要材料任务下来,先在小范围讨论,再在较大范围讨论,有时还把各县农业局长调回来讨论。邀请部分副县长、副书记回来贡献智慧也有多次。当然是几位经验丰富,又喜爱琢磨问题的老朋友。动笔写文件,总是由一人牵头,几个科室各写一部分,然后汇总、总装,呈交“讨论”或上报“审阅”。主持的,可能是副局长,也可能是科长。这样,既有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也有利于强化团体意识、全局意识,更有利于提高效率。最近,为了扭转各科站因职能等原因造成忙闲差距较大的状况,使整部机器运转更加正常,更加没有“杂音”,我们采取合并同类项的办法,一个支部统管几个科站,以支部统一协调作战。这样做的前提是“提干评先”看三动:主动、劳动、行动。主动看先后,劳动看态度,行动看效果,完全是公开公平竞争。
可以试想一下,就农委承担的任务来说,正常办会一年已经很多,仅现场会,全省的、全市的一年总是好多次,多的时候八、九次,加上专业现场会竟有十几次,汇报、总结、调研、外出考察的材料也很多,如果不是通力作战,一些科室累死也完不成任务。有领导表扬说,农委的工作忙而不乱,任务再多,也是井井有条。原因就是已形成习惯,谁牵头谁就是一把手,各组听从统一指挥。我们还建立了领导值周制度。过去值周领导主要是管机关秩序,现在又加了一项任务,每周搞一个主题鲜明的学习主题活动。值周领导统一行使设计权和指挥权。我仅承担了一项技术活:总结点评。每有一项重要工作,重大活动,也都是一位分管领导总抓,统一指挥。有的科长向我请示,我除了不予回答,还严厉批评。
工作就是集体行为,就是协同作战。各个科室自觉地通力协作,任务再多,也较轻松,而且就像发动机,越是正常运转,越不会有杂音。我甚至对大家说,什么时候我们的运转像太阳月亮的运转那样自如了,那才叫水平。原来,有的科长养成一种不好的习惯,既不善于和别的科室协作,又不善于调动全科人员合力作战,只管车头跑,不管车皮动不动。为了解决科室之间互相隔离情况、封锁材料、封锁消息、封锁信息等问题,形成经常性地融洽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的风气和习惯,采取过一系列措施。其中一件事,就是创办《内参》。一段时间以来,我几乎每周都在《内参》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协调配合不够,互通信息不够的问题。配合这件事,我最佩服的还是太阳和月亮。在人类社会里,这看似简单的一件小事,改变起来也需有持之以恒的决心。配合自如的局面来之不易啊!
关于讨论,也有几件印象较深的事,其中或许也有可供借鉴的地方,或者影子。
一件是用讨论的方法理顺干部和确立工作思路。我来农业局,接的是原来农委、农业局、开发局、扶贫办合并的新摊子。当时,主要面临两个问题:其一,人员怎么调配;其二,思路怎样创新。关于人员调配,先在领导层面讨论,又在科长层面讨论,发动各科室讨论。目标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经过讨论,大多是“自报公议”安排上岗。副科以下干部,基本是自选岗位。我在会上讲,为了工作起来舒心,岗位可以自选。选岗位,实际是选领导。作为一个科站长,如果没有人选你,就意味着不受人尊重,或者不称职。这对科站长也是个压力,等于逼着科站长提高威信。这样做,并没有乱套。正因为满足了心愿,利于发挥个人专长,加之班子内部团结,争取到的科级职数比较多,较好地调动了内在的工作热情不说,而且很快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祥和局面。
关于思路确定,当时面临的情势是:市委明确提出要把长治建成全国一流全省最大的绿色农业经济区。方向虽然明确,究竟怎么办?并没有具体的工作思路和行动方案。就我本人而言,过去的岁月尽管对农业接触也不少,但并不是内行和专家。在此情况下,我毫不犹豫选择了“集思广益”的讨论。用讨论的办法解决问题,达到目的。就“讨论”而言,我虽然不是专家,更不敢以“导演”自居,但毕竟不生疏。套用别人一句话:“咱们的老秘书长,还不会组织组织讨论?”讨论中,自觉将自己置于三种角色:学生、记者、组长。不怕人说这个局长什么都不懂,虚心当小学生;不怕人说言行不够稳当,像记者采访一样,大胆提出问题;不怕辛苦繁忙,上下穿梭,场场当组长不误。班子内部的讨论是组长,参加一些组的讨论也是组长,集中起来上大会讨论还是组长。在外国的名词中,我不知道对“组长”这个名词怎么理解,在中国,能当好“组长”很不容易。其实,像我所处的这么个小单位,把自己说成组长还是说大了,当好组长谈何容易?
经过反复讨论,确立了“打绿色旗,走特色路”的总体思路,提出了“强龙头,扩基地,抓品牌,促营销”的工作战略。从而使工作方向更加明确,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工作手段也更加切实。当时分管农业的王进卯副书记提出,“要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这样一来,王书记的思想也有了落实的载体和途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做法之所以不落后,原因就在于通过讨论甚至争论凝聚了大家的智慧。正是这样的讨论,使工作重点揭示、抓住并落实到了农业发展的本质上,并且明确了任务,凝聚了人心,调动了力量,工作起来十分顺畅。
一件是用讨论的方法创建第一个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市。市领导提出,长治可不可以创建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市?这又是一个大课题。回答的办法依然是讨论。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标准化是现代农业与国际接轨的一个方面,农业部已经有明确要求,但长治能不能创建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市?尚有许多有待弄清楚的问题。为此,还是坚持以讨论的办法开路,开展了向上和向下两大调研讨论活动。向上,把讨论的触角伸到了农业部。由此明白,当时已经创建的只限于县一级,地市一级还没有先例,并在讨论中找到了申报的途径;向下,把调研讨论会开到了最基层。从而进一步认识到,长治条件得天独厚,用吕日周书记的话说,连长治的牛羊,都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但是,条件具备不等于可以吃现成饭。能不能将大山深处的绿色优势转化为创建优势?怎样创建?从何抓起?仍然是用讨论的办法解决其中的一系列问题。组成了由一名副局长牵头的创建组织,把几个科站集中起来讨论攻关,把技术监督局的领导和专家也请过来共同讨论。经过讨论,确定了申报目标,制定了标准,采取了申报、制标、推动创建同时进行的工作方案。由于方法得当,特别是广泛吸收了正确意见,有效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便使长治的自然优势转变为工作优势,成功地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由此,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第一”就意味着开创,开创就意味着新问题层出不穷,而要有效地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讨论。
一件是用讨论的方法开好全国农业现场会。大家知道,农业部在长治召开一次全国农业现场会,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农业部召开如此规模的现场会,十几年来是唯一的一次。此会之后,最近几年,也没有再召开过这样大规模的现场会。此次现场会,用农业部领导的话说,效果之好,组织之条理精密,可以称为是一次样板会。就整个现场会的准备工作而言,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但从现场准备,材料准备,以至环境准备,各项工作都是由农业局独立完成的。后来,有人让谈谈体会,我说,就是采取了讨论的方法。开始的方案设定和分工,是讨论确定的;现场准备,材料准备,会务准备,是讨论确定的;现场行不行,材料行不行,各方面行不行,也以讨论得出结果;会务准备万无一失,是集思广益的结果;会后总结点评,也是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可能有人会说,这不势必要天天开会,形成“文山会海”吗?开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决不开目的不明确的会。每次讨论,时间都很简短,畅所欲言,决不漫无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