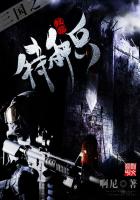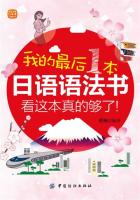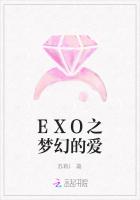“宁兄何必如此?这般倒显得苏某沽名钓誉了,实在惭愧。”苏轼停住脚步,转身如是说。而宁中直从他眼神中却看出的是不以为然的意味。宁中直伸手悄悄捏住苏轼衣袖,赶忙道,“苏兄,你看,追得我好辛苦。我久闻苏兄的大名,嘉佑元年苏兄以弱冠之年与弟辙一门两登科,着实是一段佳话啊。”宁中直见苏轼脸色转和,继续夸道,“当年苏兄一篇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着实让人激赏,区区六百言,读之却有青铜之音,‘仁可过,义不可过’旨意跃然纸上,难怪欧阳公也曾言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宁中直乘胜追击,出口就是苏轼当年应礼部试的得意之作,苏轼不禁开怀大笑,“哈哈,宁兄,如此推崇在下一篇拙作,苏某实幸甚!”言语间,前嫌尽弃,苏轼不由心中一动,略带玩味地微笑对宁中直说道,“不知宁兄可还记得苏某拙作中可有一典故?”
宁中直此时见苏轼已与自己起了逗耍之心,放下心来,苏偶像今天是跑不掉了。见他还要考较自己一番,不禁莞尔,神秘道,“莫非是‘尧与皋陶对答’,依宁某所忆此实乃周公与皋陶对答,不过既是立论何必言必有出处,若前人未有出处便自我而出又何妨!”
“哈哈,宁兄甚合我意,当初欧阳公问典故出自何处,苏某便答欧阳公何须出处,而宁兄的意境又远高于我,好一句‘前人未有出处便自我而出又何妨!’,宁兄脱出禁锢,立意洒脱自然,苏某与宁兄着实投缘。来,宁兄,随我来,苏某待你去一处我常去的酒楼咱们再边吃边谈。”此时韩毅和莫大叔也赶了过来,正站在不远处望着他们,宁中直眼角余光早看见他们,便手中暗暗示意他们先回客栈不必等他。
待到了那酒楼,宁中直见酒楼便叫“眉州酒楼”。入席后,店小二如流般很快便将苏轼所点的菜式一一端来,苏轼喜好美食,便为宁中直如数家珍般将桌上菜式评点一番,宁中直心中一动,问道,“苏兄,不知故里眉州菜式是否以辣为主?”苏轼望着满桌地美食,心思早飞到美食上,随口回答道,“宁兄莫非口味重,天下菜式皆以味美色鲜为佳,并无以辣为主的菜式。”宁中直并不罢休,又追问道,“那以何物调辣味?”苏轼已经开动筷子,待咽下口中美食才说道,“茱萸啊,宁兄莫非没吃过?”
“啊?!茱萸?!”宁中直的声音一下高了不少,茱萸这东西在宁中直的脑海中虽然不熟悉,但是“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名句他还是知道的,茱萸在他印象中作为观赏类植物的印象让他不禁对茱萸当作调料非常惊奇。苏轼正专心对付一盘红烧鸡块,被宁中直突然声音爆发吓了一跳,夹起的鸡肉落在桌上非常有弹性地一个小跳,“噗”地飞进宁中直面前的汤碗,等苏轼回过神来,看着宁中直那沾满菜汁的古怪表情,苏轼不禁大笑起来。这二人在雅间内又叫又笑,热闹非常,虽然他们是在一个雅间内,但是还是引得旁边雅间很是不满。“哗”雅间的帘布被掀了起来,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气势汹汹地进来便劈头道,”不要喧哗!搅得我家公子不得清闲……“
“昭选,快回来,不要惊了旁人!”不等这大汉说完,旁边雅间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这大汉不得不回头悻悻恭声回话道,“是,少爷,我这就回来。”走之前还回头瞪了苏轼和宁中直一眼,以示警示,只是一看到宁中直的怪模样,顿时怒脸摆不下去了,想笑又想板起面孔的矛盾样子着实滑稽。
沉默片刻,“噗哧”一声宁中直和苏轼同时大笑,笑声又再次飘进旁边的雅间。“昭选,市井多豪客,且融让些,来吃菜。”那络腮胡子的大汉望着这不过十余岁的少主人,不情愿地点点头,将怨气撒在面前的猪蹄上。
二人一边享用美食一边饮酒谈天,苏轼不觉把话题转到时政上来,“宁兄,如今你返宋,名声正是如日中天,不知宁兄对时政有何独到见解?”宁中直放下筷子,望着苏轼,一字一顿地说:“我观大宋今日,评价只需四字,内忧外患。”苏轼此时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已经两年多,听了宁中直这四字不由也放下碗筷,注视着宁中直道,“还请宁兄详解这四字。”
见苏轼那认真的样子,宁中直露出灿烂的微笑,缓缓地说:“既是苏兄想听,我便谈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内忧前人已有卓见,故龙图阁学士宋祁所提‘三冗’我稍改之,冗兵,冗官,冗费。太祖时,天下兵马不过三十余万,而后经过历次天灾,灾民尽数编入厢军,父子相替,历朝编入厢军已过百万,朝廷平日耗费了大量钱粮供养厢军而只是让他们当杂役使用,一遇战事,缺乏训练的厢军几乎一触既溃,毫无作用。我在辽国时便听说当今我大宋足有百万厢军,可见冗兵之多。其二,我朝优待士子,但每年数百士子通过科举大考,皆需授官,而历年各地所派官员都有定数,能出京为官者不过十之一二,新进士子往往数年不得派遣而在京师闲住,而每年仍然通过科举考试再进数百新人,积累下来,官多职少,而官员待遇优渥,所以朝廷发放的俸禄因而节节上升。而这两者的费用加之每年拨给辽、西夏两国的岁币,结果便是产生大量的冗费,想来,历经数朝,如今朝廷财政已是难以负担。苏兄在外任职数年,应当深有体会。”
苏轼叹了口气,说道,“苏某凤翔三年也是深有体会,宁兄你所说的三冗几乎天下共知,但无人能解此困局啊。”宁中直正要回话,帘布又一次被掀开,一个衣饰华丽的少年走进来,看了一眼宁中直,转头对苏轼说道,“苏先生,在下冒昧问一句,这位可是前几日返宋的宁中直宁先生。”听这清脆声音便是刚才旁边雅间那大汉口中的“少爷”。宁中直见这少年气质雍容,英气勃勃,想来应是王公贵族子弟,赶忙起身作揖道,“在下确是宁中直,不知这位……”一时宁中直也不知该如何称呼,便含糊带过,“……有何见教”。
苏轼此时已经认出这位少年便是淮阳郡王赵顼,轻声道:“王爷,这位便是宁中直。”赵顼一听便转身好奇地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俊秀的士子,好半天才说道,“谣传宁中直面目俊秀异常,气质独特,我还当是以讹传讹,不想今日一见,比我想像中还要谦和俊秀。”宁中直听着比自己小七八岁的赵顼在那故作老成地对自己一番点评,心中暗自好笑,“哼哼,瞧我这运气,今天一天又是见偶像又是见了以后老板,哎,怎么光关心我的长相了?这小子不会有断袖之癖吧?”一想到这,宁中直不由打了个寒颤。
刚才赵顼由属下结帐,正要离开,从宁中直他们这间经过时正好听见宁中直在谈论时政,不由停住脚步,在帘布处侧耳聆听宁中直的论述,听苏轼称这位谈论时政的士子为“宁兄”,不由想起前些日子传得举国皆知的宁中直大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便冒冒失失冲进来看看这位声名鹊起的人物。
两人垂手站在自己面前,赵顼见气氛有些尴尬,于是便随手拉过一把椅子,边坐就问道,“两位请坐,宁先生,刚才听你谈及内忧,不知外患可否也讲解一番。”此时赵顼不过年过十五,正是年轻气盛之时,相对于“内忧”,喜好兵器的他更关心“外患”。宁中直见以后的老板要“面试”了,抖擞精神,略一沉吟,微笑望着赵顼,口气轻松地说,“在下以为外患虽然看似严峻,但实际却并无内忧那般难解。”赵家王朝从建立伊始便感受北面契丹的威胁,而数十年前西夏又叛宋自立,仁宗朝三战西夏皆败,赵顼和他的前人一样对外患比内忧更为担心,这时听宁中直说外患并不难解,不由聚精会神等待宁中直的下文。
宁中直心中得意,“嘿嘿,吊起胃口来了吧。”他侃侃道来,“以在下刚离开的辽国为例,历经数世,其国势已经大不如前,国内汉民与夷族矛盾重重,而且其国内如今刚刚经历大乱,朝中主少国疑,虽然萧太后是个精明人,但是朝中耶律乙辛是个野心极大的权臣,其党羽也不可忽视,他们二人若未分出胜负,则辽国无南下之意,即便他们分出胜负,辽国也是元气大伤,无力南侵。此北面之敌实不用担心。何况我大宋还可其中作梗,让他们两派争斗不休,待大宋国势恢复,收复幽燕也大有可能。”
宁中直的话让年轻的赵顼不由眼前一亮,尤其是提到的那幽燕十六州一直是大宋历朝的夙愿,听了宁中直一番解说,赵顼迫不及待地问:“不知西面之贼宁先生以为如何?”宁中直早知道他会这么问,微笑着说,“王爷,在下只是市井之民,议论朝政已是逾礼,妄言军情之罪可担当不起。”
赵顼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不过还是说:“即使如此,小王也不便勉强,改日小王邀请宁先生和苏先生到鄙府做客,还请两位不要推辞。”说着便起身告辞,这顿饭被赵顼一搅,宁苏二人也不便再留,便就此各自告辞。
待宁中直回到客栈,已是月上梢头,刚迈进客房,便劈头听韩毅道,“公子,韩相公今天送来请柬,请您明日过府一叙。”宁中直打着哈欠随口说道,“哦,知道了,应元早点歇息吧。”韩毅赶忙叫住宁中直,“公子,这还有欧阳相公、淮阳郡王、……曾相公五份请柬。”一个个显赫的名字飘进宁中直的耳朵,心中哀叹,“这回麻烦大了……”
------------------------------------------------
这一节涉及的“尧与皋陶对答”是苏轼诸多趣事中的一件,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查资料,看看这个宋代美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