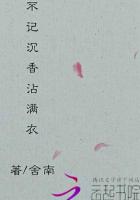净慈寺建在南屏山慧日峰下,高挑的飞梁重檐,黄色的琉璃瓦脊,显得庄严宏大。大雄宝殿后头,还挂着一口重达一百多公斤的铜钟,每日黄昏,悠扬的钟声在暮色苍茫的西湖上空飘荡,激起人们的无限遐思。
可此时的南屏山已被耍杂耍的、变戏法的,卖胭脂、卖零嘴、卖笔墨、占了大半个山头。
“小姐、小姐,今日人真多呢!”
那些个丫环一出了门,哪里还想得起什么永明禅师,什么佛法精妙,各个俱是半掩着帕子,伸长了脖子,两个眼珠子咕噜噜的四顾不暇。
永明禅师果然名动天下,他此番游历回来,头次公开坛讲佛,惹得阖郡的男男女女俱是跑来凑热闹。
那有钱的富贵人家既是见不得永明禅师,也要在寺边的茶社中租个雅座,引上几位朋友,吹吹风,看看湖,听上几声悠扬的钟声,粘粘高僧的祥瑞
那些个小老百姓们,也要在路边的茶棚里花上几个铜钱买杯茶,吃几口点心,听听和尚们唱经,倒像是踏青交游一般
怎奈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太多,简直把僧人修行的僻静场所变成了集市。
好在舒大人面子大,舒管家报上名帖,就有一个知客僧引着他们进去。
绕过几间大殿,就见一处专为香客准备的厢房,外头闹热的不行,这厢房处却极为清净。她们一行又是女眷,特意挑选了一间极幽静的厢房于她们。
那几个丫环婆子伺候了茶水,一个个的哪里坐得住,想要清净,家里才清净呢,何必巴巴的跑来这儿呢?
好不容易出了来,谁不想出去瞧瞧热闹?无奈舒小姐平日管教丫头们规矩多,众人也不好开口,晓得英奴也是个爱闹热的,只去走她的路子。
“萧小姐,永明禅师还未时辰讲法,咱们不若先出去走走罢。”
英奴点头道:“好啊,咱们先逛逛寺庙,我还想去求个签呢。”
殊不知这些丫环年近及笄,正有此意,此时听得英奴一讲,以为笑话她们,俱是扭捏起来。
“奇怪了,你们这是怎么了?”
“萧小姐惯会捉弄人,姑娘需得好好说道说道!”
舒小姐瞧着英奴一脸茫然的样子,暗自好笑,眼看丫环们一个个臊得不行了,只得出来打圆场。
“咱们去大殿里拜拜菩萨吧。”
丫环们见小姐发话,这才扭扭捏捏的出来。
净慧寺香火鼎盛且不消说今日更胜往常,下头的善男信女皆是香油钱添个不停。
英奴捐过香油钱,跪在菩萨面前,诚心诚意的祷告。
“菩萨,都说好人有好报,大哥一生孤苦,恳求菩萨保佑,愿他此后无病无灾,一生安康,快快乐乐的过活”
说罢,结结实实的磕了头,便取来签筒,心中默念。
“菩萨保佑我快些想起以前的事情,愿我爹爹妈妈早日找到我,好叫我们一家骨肉团聚。”
又念了一声“菩萨保佑”,这才摇起签筒,拾起一支签文,拿起一看,写着“庄周梦蝶”。
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众人也都求得了一支,那舒小姐正对着签文沉吟,见英奴望向她,抬头笑道:“英奴可是求得了?”
“嗯,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说着就把签文递于舒小姐。
“庄周梦蝶?”
这只怕不是什么好签。正不知如何宽慰,就听得丫环们嚷着要去寻解签的。
众人走出大殿一看,那寺边解签的摊档早就叫人挤满了,哪里挤得进去。
还是采苹眼尖,指着一处道“小姐你看!”
却见一个档口冷冷清清,竟然一人也无。
再看那解签之人自顾自的喝着小酒,摇头晃脑,没有生意也不着急,好不自得。
英奴心急,道:“就他吧。”
一行人走进一瞧,只见这人方脸大耳,阔鼻薄唇,衣服上头还粘了好大一块酒渍。
她们却不晓得此人可是大大的有名。
这人名叫胡太冲,原是个旧家子弟,无奈家道中落,凭着读过几年书,便做起了神棍,奈何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凡赚够了酒钱再也不肯出来摆摊做生意的。
这人嘴巴又极臭,十个签文里头到有九个是差的,一个是极差的,偏偏找他解签的又是极倒霉的人,自叫他句句说中,他的臭名自然远播,日子久了人人都喊他胡晦气,哪里还有人愿意找他解签来处自己的霉头。
故今日这等大好日子,人家生意做得忙不过来,他却是极清闲,偶有两个外地人不明就里的撞上去,没叫他说上几句,无不拂袖而去的。
偏偏舒小姐她们虽是本地人,平日不出门,这才撞倒了胡晦气手上。
“先生,我们解个签。”
那胡晦气点点头,接了英奴的签文,尽然眼皮子也不抬一下,只捏着英奴的签文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翘着个下巴,摇头晃脑的问道:“小娘子,求何事?”
“求骨肉亲情份的。”
“哦,那便是个下签。”
英奴恼道:“先生连看都不曾看,怎么就说是下签?”
“嘿嘿,我胡太冲解了十几年的签,鼻子底下一闻就晓得了,小娘子求的可是“庄周梦蝶”?”
众人大吃一惊。
“所谓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又有人云,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不晓得这位小娘子是庄周还是蝴蝶呢?”
英奴只听得云里雾里,瞧瞧舒小姐,却是锁眉不语。
英奴心下更是焦急,恳切道:“先生,您这话我实是不解,可否说得再白些?”
“哎呦!”胡晦气抿了口酒,指着英奴笑嘻嘻道:“这意思就是说呀,做了一场白日梦,醒了以后不晓得自己是谁了。你说,那梦里的事情能作数呀,一觉醒过来,哪里管得了啥庄子蝴蝶的,该怎地还是怎地。”
做了一场白日梦!
莫非真是此生无望?难道我一辈子就再也见不到爹娘的面,一个人孤零零的举目无亲了吗?
英奴只觉浑身似灌了铅似的沉重,木木的靠着舒小姐身上,话都讲不出来。
舒小姐瞧着英奴脸色发白,连忙安慰道:“俗话说,山不转水转,英奴莫要太过认真了,将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若遇到贵人有转机也未可知啊。”
胡晦气嗤笑道“俗人啊俗人啊!正所谓:城外土馒头,陷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万事归根到底,也就一个奔头,看开些、看开些。”
说罢,对着几个丫头把手一伸,道:我说,还有几位?统统拿来便是。”
丫环们哪里还敢找他解签,俱是搂紧了签文,拼命摇头。
那胡晦气仰天长叹,正俗人啊俗人的说个不停,却听得有人朗声说道:“先生,不若你瞧瞧我的罢。”
只见几个公子们簇拥着一个头戴紫金帽的年轻公子兴步而来。
这些青年俱是衣着华贵,面容俊朗,惹得几个丫环俱是脸红了起来。
其中一人把签文交给了胡晦气,道:“先生请看。”
那胡晦气照例捏着签文,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抿了一口酒,懒洋洋的问道:“求什么?”
“求前程。”
“嗯……”
只瞧他张半睁着一双醉醺醺的眼睛,叽里咕噜了一会儿,笑道:“嘿嘿,恭喜恭喜,是个下签。”
另一位公子恼道:“好个泼皮,既是下签,还说什么恭喜?分明拿我们作消遣,看我不砸了你的摊子!”
唬得胡晦气赶紧伸手抱住档头,笑嘻嘻的道:“嘿嘿,这下签也有讲究,好比刚才这位小娘子,便是个下签中的下下签,如今这位公子得了下签中的上上签,自然要道声恭喜。”
此言一出,气得英奴也想砸了他的摊子。
那头戴紫金帽的年轻公子却笑道:“请先生释疑。”
胡晦气搓了搓胡子,道:“公子的签文可是庄周话鲋?”
几位公子面面相觑,只道:“正是!涸彻之中鲋困之,躬身自可卜当时,若能引得西江水,他日成龙也为之。先生,这签文再不济也是中签,如何下签之说?”
那胡晦气只嘿嘿的笑了两声,有人机灵,便在他的盘子上头放上几颗碎银子。
胡晦听得“咚、咚、咚”几声,小眼发亮,拍着大腿道:“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诸位公子都是读书人,即是命最大,运老二。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如何把这命中注定的因果,枉费寄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转机上?”
说着又抖了抖身上的衣服,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好比小生我,匆匆数十载前,也是粉雕玉琢,人人都说小生将来必定貌若潘安,如何现在这般长得同家父一模一样?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可见都是注定的!”
那公子听得胡晦气一通胡邹,却不在意,只笑道:“好个胡晦气,尽能自圆其说,倒是名不虚传。”
“承让、承让,今日多谢两位惠顾,生意做得差不多了,小生我这就收摊了,下次还请多多照顾,多多照顾。”
又对着英奴道:“多谢小娘子,解签十文钱,童叟无欺,本人下月还在此地作生意,还请小娘子同几位再来啊,多多捧场、多多捧场!”
直到英奴她们走得老远,还听得胡晦气的高声道谢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