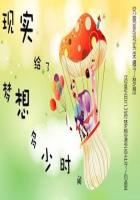镇南王府的苹果树又到了开花的时候了吧,恍然中那些幼时的记忆都蒙了尘埃,不再鲜明敞亮的刺目,多了岁月洗涤之后的柔和,虽然这柔和,只是明了再激烈的抗争也是徒劳的无奈。
沐阳有时候会想,也许人的命真的早就注定,容不得半分更改。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命,就是命。
大哥就是个好人,也许这世上都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假如不曾生于王府,不曾有你争我夺的利欲熏心,大哥的世界必定还是明亮善良的,假如,他和母亲不曾存在,假如,一切都还可以重来……
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可以相处的亲密和谐吗?他是不信的,面对着王妃的鄙薄严厉,面对全府上下的冷眼刁难,他真的不信,可是大哥信,也这么努力的做了。
他还记得那棵在幼小的他看来巨大无比高不可攀的苹果树,真的好馋,大大的诱人的苹果挂在枝头,摇曳的熠熠生辉,和母亲住在冷寂空荒的后院,前院只意味着禁忌和逾越,可是,那棵苹果树,他已经从春日守到了秋天。
他不知所措的站在树下,面对可望而不可即的苹果,委屈的哭出声,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大哥,原来,大哥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那一天,他从清若静水笑的和善的大哥手里接过苹果,便是此生最甜美的滋味,因为,那眉目温软的大哥哥告诉他,这棵苹果树,归他了。
第一次的礼物,他收的无比快乐。
竟然还有别的?有的,自那以后,大哥便时常到后院去看他和母亲,带一些他们短缺的食物衣服,指望正在沙场点兵作战遥不可及的父亲偶尔写来的几句关心之词,果然是不够的,还好,有大哥。
纸包不住火的道理他那时懂了,大哥被王妃禁足,“别有用心”的他和母亲招致更多欺辱,最最受不住那凌厉女子的谩骂毒打,小小的他过早体会到了大人的争斗,母亲,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忍耐中,渐渐变了,变得歇斯底里,变得不再柔婉清高。有时,被母亲当做敌人般撕咬辱骂,他也习惯了承受,只孩子气的怀疑,母亲疯了。
母亲没有疯,却比疯了更可怕。
没有人知道母亲在筹划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母亲是怎么打通这府上的各种关系,利用到厨房总管的,那最后的几日光景,他模糊的记忆里,只剩下母亲偶尔充满快意和期待的咬牙切齿冰寒阴暗的呢喃声“去死吧……去死吧……”
后来他就见到了误喝了母亲给王妃准备的毒茶的大哥,嘴里好多好多血,一直流个不停,那向来白净柔软的衣衫沾着鲜红刺目无比,大哥,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清楚,王妃早就晕过去了,母亲在一旁愣住,满府的人慌乱无措的找什么大夫绕来绕去,只有他,一步步靠近大哥,靠近那个即使痛到身体痉挛目光依旧温和的大哥,听他说话,仔细的听一字一句。
“好好活着……不要争斗了……不值得……娘……放过他们……阿阳……阿阳……好好活着……”大哥说了好多,他努力的听,却只抓住只言片语,够了,够了。
他胡乱的给大哥擦掉嘴角不断溢出的血,怎么擦不完,他第一次知道,人身体里的血,有这么多这么多,空气里都是腥甜的味道,那血,红艳的决绝。
他一个劲的点头,大哥,我知道,我知道,大哥,求你不要说话了,不要再说了,大夫,有大胡子的神仙老爷爷,为什么还不来……还不来……
大哥死了。
母亲疯了。
王妃削发为尼出家了。
空寂荒凉的王府,除了那些带着怜悯之色服侍他们的下人,只剩下他和两岁幼弱的沐雪相依为命。
后来,爹收到消息,抗旨不遵回来了。
再后来,他开始厌恶源源不断的封赏,赐诏嘉奖的功业,都是这些可以继承的东西,让所有人盲目,这些所谓的声名荫庇,不就是害死大哥的凶手吗?
所以,他不会安稳的做什么世子,不会去享用继承那已经用大哥的命证明了虚妄可笑的世子名望,他记得,大哥说,不要争斗了。
那些,不值得。
大哥,我知道。
功业名利,就算需要,我也只会去自己打拼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染着你的血的世子之名,我从来都不喜欢。
大哥,要是你还在,该有多好……那棵苹果树,又开花了……
那些苹果又大又圆,只是,除了你摘的,我再也没吃过……
“……大哥真的是个好人,真的。”沐阳说到后来,微微哽咽,掩饰一般大口灌着酒,眸中都是遥远的无奈悲凉,他定定的凝视着夜空的星星,也许有一颗,是语声柔和目光温软的大哥。
顾青何默默的给他倒酒,这一场酒,到头来,不知要喝伤几人的心。
静寂的夜,静默的两人。
沐阳的情绪渐渐平稳,他缓缓摇头,把杯子移过去躲了顾青何要给他继续倒的酒,苦笑,“我要醉了,青何,我不能再喝了。”
“难得醉一场,顾府的地方容得下你。”顾青何的手堪堪停在半空,他注目面前的人,轻声道。
沐阳稍稍犹豫,叹息着把杯子移回。“好,就醉一场何妨。”
一旬酒过。
“该我说了。”顾青何清冷出声,“今天遇到的那个人,我想你已经猜到了他是谁……”
在顾青何幼年的记忆里,父亲这个词,只是伴着母亲柔软声音谈起过去时的一个称谓。
他不懂父亲是什么,他只知道,母亲是不同的。
在这样破落的小村庄里,到处是粗衣陋妇,母亲却总是文雅清新的,即使在三餐不继的情况下,他的衣物也总比别的孩子干净的多,他的话也比那些孩子识礼的多,因为母亲会责怪他学来的粗言鄙语。
没有人欺负他们,即使他们是外来的,且格格不入。
因为母亲是这小山村里唯一识字的人,开头只是帮忙写信,后来,母亲干脆开办了一个小私塾,成了这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夫子。
所有人都知道母亲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所有人也都知道,母亲,一直在等一个人。
一个多年前带着妻子过来安家落户的落魄书生,那个叫做父亲的人。
一场早不新鲜的戏,落魄书生和富家小姐情投意合却被门当户对的世俗阻挡,终于,母亲决绝的和父母断了关系,一心一意跟着即使穷困的如意郎君翻山越岭逃离了重重追逐。然后,书生决意上京赶考衣锦还乡,然后,便是母亲带着腹中孩子日复一日的等待,煎熬……
如果,不是一个同乡从京城回来,如果他没有沾沾自喜于曾经和一个状元大人见过面因而到处宣扬,如果他没有记得那让母亲日夜思念梦中都在呢喃的那个状元的名字,那么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另一个方向……
然而,上天从不给第二个选择。
母亲终于决心带着年幼的他上京寻夫了。
又一场并不新鲜的戏,俊秀书生上京赶考,及第会上遇到达官贵女,一见钟情,再见倾心,也许有挣扎有矛盾,但终于,抵不过状元加身的名望诱惑,抵不过那些夫凭妻贵的刻意提拔,书生,妥协了。
和母亲的再相见,都充满戏剧性,马前失蹄,他差点被亲父的座骑踩死,幸亏,被救,然后,母亲慌张无措的跑过来搂住他,然后,遇见……
母亲和他的安置是一个大问题。
书生好歹有着或旧情或愧疚的心思,把他和母亲置于家中别院,也算一番照料,可是,瞒不过家中从小浸淫了权术争斗因而心思缜密的顾夫人,这别院,很快被“光明正大”了,母亲也被三番两次羞辱鄙薄,吵闹的时候,母亲总是捂紧了他的耳朵,只是,那颤抖的合不住的手,怎么阻挡得了四处夹击的谩骂攻讦,他在那时才明白,原来,他和母亲,并不被欢迎。
母亲渐渐憔悴消瘦了,眸中早没了往日因期待而聚起的清亮明晰,变得黯然无光,书生偶尔会来,便是一场悔过盟誓,只让母亲等,再等等,等他羽翼丰盛,等他可以脱离桎梏……
母亲真的信,真的等。
假如能平静的等,也好,可是,事不能尽如人意。
流言纷飞,母亲在小村庄的事情突然“精彩”起来,不是日复一日的平淡等待,母亲“不甘寂寞”的房中,有陌生的男子出入,甚至他,都可能并非亲生。
一向温和的母亲听到这流言,第一次发了怒,第一次,委屈的哭。
书生信誓旦旦说着相信,母亲这才渐渐平静。
可是这书生软弱的耳根,敌不过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外出买菜的母亲忘了带钱早早回来,就看见一心一意说着相信她的良人正拿着刀子要割儿子的手,准备神不知鬼不觉的滴血认亲……母亲发了狂,上前要夺下刀子,这一向懦弱的书生那时却定心挣开了母亲……
终于,滴了血。
终于,认了亲。
母亲僵着身子瘫软在地,那本以为母亲不愿是因为心虚的书生愣住了。
此后无论书生怎样的痛骂自己,怎样的悔不当初,母亲,骄傲的不容如此侮辱的母亲,再不曾回应。
母亲生病了,很重很重的病,躺在床上都起不来。可是,当那顾夫人带着家丁过来要把他们驱赶出别院的时候,母亲却奇迹般撑着站起来,她说,让我见一见顾言微,只要是他的意思,我就走。
那个软弱书生来了,也许是被强悍的顾夫人强拖了来的。
他此生此世都不会忘记,那个懦弱只会讨好别人的书生对母亲说的话,他说,让母亲先搬出去,等他安顿好这边就会把他们接回来,甚至,他说,让他们回小村庄,他说,那里比较安稳……
安稳?
连他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母亲如何听不出,顾言微是说,让他们安稳的等,等一辈子,也许到下辈子。
母亲笑了,她静静的看着书生,不言不语。
她为了他负了父母的期望,此生再无脸回家,结果,只换回来一个字,等。
母亲果真就带着他走了。
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他们没钱,顾青何使尽了方法,可是他只是个文弱书生,做粗活的地方不要他。
他开始造假,模仿名家画作,急迫的时候,他甚至偷过书院的东西拿出去变卖,他感激江少曦的装不知情,那一段时光,江少曦给了他不知多少帮助,他此生不会忘记。
母亲打了他,第一次打了他,因为有一味药,实在太贵,他不管不顾了,说要去找顾言微帮忙,母亲第一次对他抬起了手。
母亲说,不准去,你去,就别回来。
他没留住母亲。
他没了母亲,从此,也不会有父亲。
“……你看,我娘多傻。”顾青何再次端起了杯,他甚至笑着在说话,有一滴泪顺着清俊的面颊不知不觉的滑落,他不知情,还是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