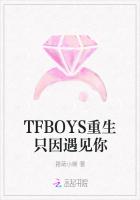得到州牧大人的青眼,教习坊中的管事对我的态度立刻就柔和了三分,但这三分做出来的恭敬中,又夹杂着不屑与怜悯。
教习坊管事不但准了我的假,还殷勤周到地将原来服侍我们的的两个老妈妈又打发了过来,让我们的生活方便了不少。采薇和阿奴她们的的忧虑是显而易见的,连一向总慢人半拍的馨兰都提醒我以后不要再去扎州牧大人的眼了。
我只能苦笑,心里暗暗怨恨诸葛公子,若不是前番送药和这次见尸首,我又怎么会被大人记住,又怎么会变成这么个不尴不尬的角色。想冲他发脾气,可奇怪的是,一连两日,诸葛公子连长公子的院门都不出,仿佛他不是回来报喜,只来打秋风的过客一般。州牧大人也是如常起座,也没有召集在江陵城的大人们进府听诸葛公子的战报,一个胜仗回来遭这样的冷遇,是在让人费解。
在屋里闷闷地躺了两日,这一日终于好些了,走出院子,想着松散松散。才出门,就遇见了诸葛公子。他的样子却着实骇人,才两日的功夫,两鬓的青须竟然扎出老长,看上去青餐餐的一片,眼眶也有些凹陷。我俩走了个对头,我吃惊地愣了愣,他瞧见我倒是不吃惊,笑了笑,可是笑容里尽是勉强:“正要去找你,遣了人去教习坊打听,说你病了?”
“还不是拜公子所赐,若不是那天在河边见了尸首,被州牧大人传去问话,何至被吓病了。”想到这事儿,我实在有些生气那****把我卖给州牧大人。
诸葛公子愣了愣,旋即释然:“哪里是我卖了你,这府里,州牧大人的耳报神灵,那日,我可是一字都没有提起你。”
我也一愣,“你是说,咱们那日说话,都有人瞧见?”
“谁知道哪,”诸葛公子无限疲惫,“横竖都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什么都在人家掌握中也是必然。”
我忽然想到了王夫人的药,忧虑地望了望诸葛公子,他似乎和我想到了一起,“你也不用担心太过了,若是州牧大人什么都知道,那给夫人进药这事儿,也只在他许与不许之间,此刻,州牧大人还是需要王夫人活着的吧。”
我眼前一阵晕眩,如果这刺史府处处都是州牧大人的眼线耳报,那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小计谋,又有多少能瞒过他的眼睛?
“你今天不去教习坊吧?”诸葛公子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摇摇头,回答了他。
他朝我灿然一笑,“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个地方?”我狐疑地看着他。他笑容更灿烂了,“保证是个好地儿,去了你下回还想去。”
也不容我迟疑,他牵着我的衣袖就把我拉去了侧门,仆役早在侧门等候了,一骑双乘,离了府门。我想挣脱,可是诸葛公子用手臂紧紧地箍住了我,“可别乱动了,万一摔下去,跌成个瘸子,以后我可不去讨你。”
“你”我有些真生气了,“你是打算彻底害死我么?刚才还说这府里都是州牧大人的耳目,如今你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带着我出来,你安得什么心?”
“安的什么心?”他的气息喷在我脖子后面,痒痒的,热热的,让人浑身难受。
“我安的什么心,州牧大人传了你,非但不责罚,还赏了你,你倒要问问他安的什么心。有我如此为你出头,给你当现成的挡箭牌,你还不好好谢我,怎么,真筹谋着要留在刺史府当如夫人么?”
只这两句话,就说到了我心底的最深处。州牧大人对我的抬举,让我深深恐惧,诸葛公子愿意给我当这个挡箭牌我自然求之不得,可是他这么公然下州牧大人的脸面,谁知道大人不会报复在我的身上,把我随便又赏给别人哪?
“挡箭牌?你真惹恼了州牧大人,还不是我受连累?”我恨恨未消。
“你放心,大人欠着我的人情哪。”
我转过头去,因为距离近,他一张脸在我面前放得很大,眼下的两个黑眼圈,是触目惊心的清晰,“州牧大人欠你什么啊,尽胡说。”
“呵呵。。。。。。这次长沙之战的封赏下来了,这奇谋之功归了张怿兄,老大人向朝廷请封长公子为广武将军,张兄为和戎校尉。”
我看了一眼身后的人,他的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失望,我在心底里暗暗叹了口气,忽然想到那日诸葛大人从刺史书房出来,看来纵然是亲叔叔,也不曾替侄儿争取什么,又想到叔侄俩河边的对话,只一条计策,八千兵士尽丧,实在是有些太过了。虽是胜仗,也算得上惨胜如败了,这些年,连年战乱,人口日益稀少,八千降兵,不算是个小数目了。
我忽然也很想知道诸葛公子是如何看待这次大胜的,小心翼翼地问:“八千人,这么多尸体很怕人吧?”
诸葛公子眉毛一挑,声音也高了两分,“你是责备我心狠手辣?”
我赶忙摇摇头,“我只是那日见到一个尸首就吓病了,怕你经过了战阵,也有什么不适。”
“傻瓜”他说话的热气喷到了我的脖子后面,“毕竟我也是男儿,和你们女儿家又怎么相同。”
两人同乘一骑,本来就惹眼,这会儿诸葛公子又带着我离开了刺史府的地界,往南城去了,这儿是普通民房的聚集地,路上的老百姓,都提篮担担地步行,我们这高头大马的一来,惹来了不少注目。连年的征战,百姓多贫弱,马匹更是成了稀罕的东西,除了官宦之家,普通人家连牛车也少有了。
马拐了个弯,进了一个小巷子,巷子不深,只十来户人家的样子,一眼就能望见尽头,诸葛公子带着我在一家门前停了下来,院子里有棵槐树,长的很高,枝丫都伸出了院门,正是结果子的时候,树上的槐米挂了一树,
我笑着指着那一树槐米:“好一树的好果子,这家人倒也大方,也不收拾收拾。”
诸葛公子笑着扶了我下马,“可见这家人日子过得不错咯。”
他上前扣门,门吱呀一响,里面出来一个半大小伙子。
虽然有时日没有见了,但阿弟的摸样在我的脑中太深刻了,我“啊”地惊呼了一声。阿弟也一眼望见了我,竟是一声惊呼之后回头高呼着飞奔回了屋子,“阿娘,阿娘,阿姊,是阿姊。”
也不等诸葛公子让,我一马当先就进了院子。三年不见,阿娘竟似老了十岁,母女相见免不得抱头哭了一场。哭得狠了,阿娘开始咳嗽地不停,我给阿娘摩挲着后背,阿妹怯生生地端着一碗水送了过来,阿娘喝了半碗,方才略缓了些,一手拉着我,仔细地瞧了半晌,叹了口气,“日子苦不苦?刺史府里人多,你过得难不难?”
我摇摇头,“还好,早两年府里夫人身子不好,并不曾十分地约束了我们,也不朝打昔骂的,也过来了。”
阿娘听我这话,却也止不住悲声,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早两年不曾?这两年,可是受了委屈了。”
没想到,阿娘如此敏锐,连我这话语后的无奈,都被她洞察地一清二楚,我想把话找补回来:“哪里,如今渐渐大了,更没有人给我气受了,一起的姐妹们也很和睦。现在常常在堂前表演,进项也多了。阿娘你这咳嗽也要好药来医一医,女儿如今在府里得的赏赐不少哪。”
阿娘摇摇头,“如今家里也得过了,你阿哥在府库里也有了差事,你有了钱自己也好攒着,阿娘如今啊,就是愁着你怎么能从刺史府出来。”说着,压低了声音,看了院子里一眼,“那位公子,很是肯拉拔咱们家,你们。。。。。。”
我一窘,“阿娘,别胡说,这屋窄房浅的,被公子听去,那是诸葛公子,府里的座上客,因怜惜着我命苦,才关照咱们家的。”
阿娘额脸上挂着明显的失望:“唉,娘还说若是这位公子,也算我们阿宁有福气。”
不但我大窘,一旁的阿妹也想要出屋去,阿娘却一把拉住了她,“你阿姊回来,你也不说问个好,脸皮这样薄,透着小家子气。”
阿妹才挨近了,给我施了个礼,“阿姊”。我仔细打量眼前这个小姑娘,我离家的时候,她是个走路还跌跌撞撞的娃娃,如今也已经是个小姑娘了。细看了几眼,阿妹、阿娘和我都很像,清秀的面容,只是阿妹的面容更姣好些,深邃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连睫毛都忽闪忽闪,透着底下如小鹿一般的不安分。这和我当日离家时那个挂着鼻涕,在家门口像邻居孩子讨吃食的孩子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欣喜地对阿娘说:“阿妹以后是个美人胚子哪,如今才几岁就出落得这样好,很像阿娘当年。”
阿妹身上穿着我前两年送回家的以上,虽然还大些,但也改地很体面。“这衣裳虽然时旧的,阿妹穿了,也不觉得寒酸。”
阿娘拉着我的手,“你妹妹手也算巧,才几岁的年纪,如今已是能帮我干许多活了,这衣裳也是她自己改了,倒也不用我操心了,唉,我还算是个有福的,你们一个一个都不曾让我操心哪。”
我把阿妹拉到身边坐了,问她“日常在家可做些什么,阿娘可教了你弹琴么?”
这话才一出口,阿妹的神色一暗,摇摇头:“没有,平日就是帮着阿娘做活,阿哥不让学琴。”
我不解,转头看看阿娘,阿娘一阵苦笑:“自你走后,你阿哥在家,连曲子都不让唱了,更不要说弹琴了。。。。。。他也是,也是心里苦。”
我心头一紧,想到了离家的那天,出屋后听到的那声像野兽般的吼声,忍不住,眼眶就湿了。正在伤心,阿弟捧了个钱袋子进来了,为难地看着我,“阿姊,诸葛公子非要留下这袋钱,我推了,实在是推脱不过。”
没想到,他连为我打点家里的钱都准备好了。我笑了笑:“你收着吧,回府我自然还他,家里人多,日常开销也要留一些。”
阿娘摇摇头,“家里托你的福,把最艰难的日子也熬过去了,你在刺史府里,欠着这情分也难还,还是。。。。。。”
我有些无奈,“阿娘,这情份一份也是欠,十分也是欠,横竖是要还的,还差这一袋钱么?”
阿娘也读出了我的无奈,对阿弟吩咐,“你且收了吧,你去街上割些肉,沽些酒来,留你阿姊和诸葛公子吃个饭。”
“艾”阿弟答应了一声,欢快地取了钱,往外头走了。
才出门,又折了回来,一脸无奈,“阿姊,公子请你出去?”
诸葛公子始终没有进屋子,只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下站着,见我出来,直接就把在我家用饭的想法给否了,撺掇着带家里人到外头酒肆里去用饭。我略一犹豫,看一旁的阿弟和阿妹有兴兴然有欣喜之色,不免叹了口气,答应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