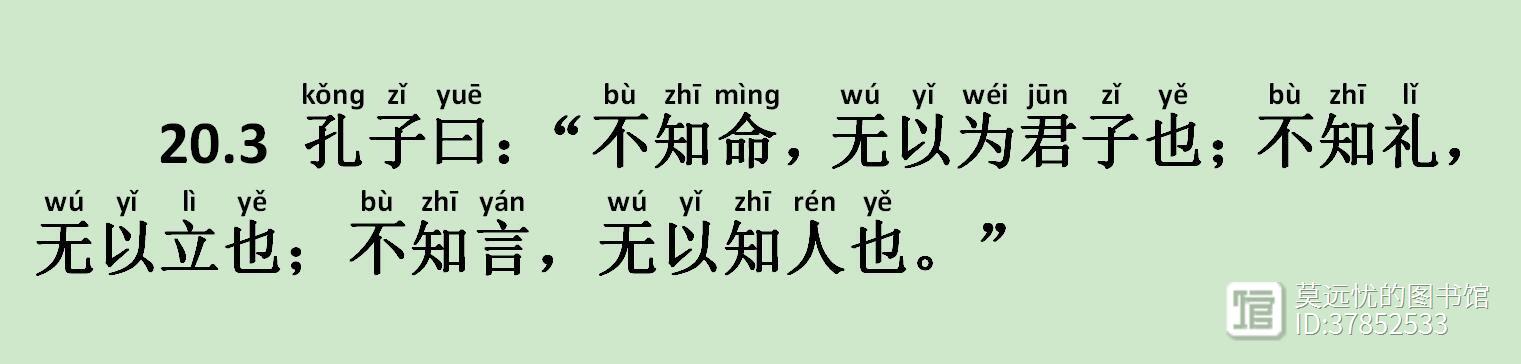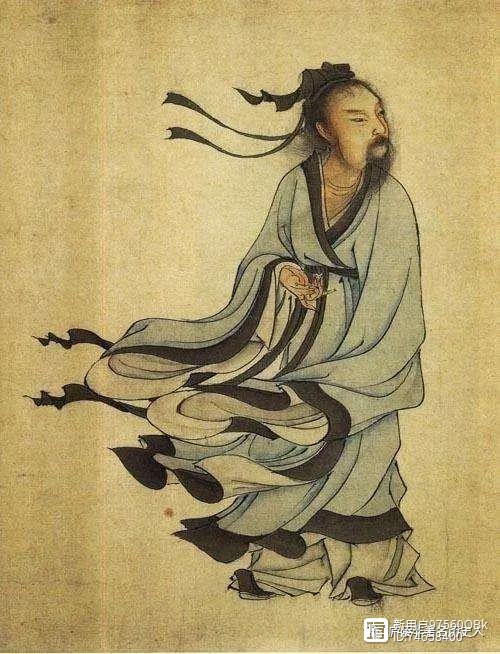子居:清华简十二《参不韦》解析(七) | 中国先秦史
清华简十二《参不韦》解析(七)
子居
【宽式释文】
参不韦曰:启,唯昔方有洪,溢戏,高其有水,灌其有中,漫泆,乃乱纪纲。莫信德,乃作德之五观、九观之参,以效天之不祥。
参不韦曰:启,靡滥天则,毋懈弗敬,春秋冬夏寒暑不懈。启,不违天之德。启,日月、星辰、雷霆、妖祥、风雨,不失其时。启,不违天之臬。启,天则物各有当、各有利。刚柔反易,缓急异章。作柔而利诸刚,作刚而利诸柔。启,唯天之宜,乃不观;启,其溢泆,乃观。
参不韦曰:启,毋用妖观以自阻。德之五观,百神弗享。九观之参:淫、湎、康,则毁;掘谷、壅土、大居,则丘;媱娥、无省、朋尤,则内忧;迫、疾、变,则乖;虐、不由、不刑,则灭光;寇盗、残贼、杀伐,则绝行;刚、虎、猛,则栉;诈、巧、柔,则惑;妖诵、迂言、妖讙,则乱。
参不韦曰:启,毋不极天之命以从乃德,唯天之不祥。启,乃自则乃身,弗可复庚。帝之命逆违,命用不长。百神之凶见,后嗣之殃。
参不韦曰:启,乃毋既康淫湎,观有懈德,乃曰弗可追悔,以须天之殃,天之明德。唯悎天之命,追悔前过,胥受天殃。钦明不懈,天弗作祥。
【释文解析】
參不韋曰:𢻻(啟),隹(唯)昔方有【一一〇】

(洪),溢

(戲),高亓(其)有水,權亓(其)有中,曼(漫)

(泆),乃𡄹(亂)紀䋁(綱),莫

(申)悳(德)〔一〕。
整理者注〔一〕:“有水、有中,与「有洪」结构相同。权,清华简《五纪》作「雚」。《战国策·韩策三》「何意寡人如是之权也」,鲍彪注:「权,犹变也。」

,读为「申」。《诗·假乐》「自天申之」,毛传:「申,重也。」参看《五纪》简一至二一:「唯昔方有洪,奋溢于上,权其有中,戏其有德,以乘乱天纪。后帝、四干、四辅,乃耸乃惧,称让以图。后帝情己,修历五纪,自日始,乃旬简五纪。五纪旣敷,五算聿度,大参建常,天地、神祇、万貌同德,有昭明明,有洪乃弥,五纪有常。」”[1]训为“变”的“权”是权变义,也即权宜、变通,虽然这个解释在《战国策·韩策三》是成立的,但代入到清华简《参不韦》此段则明显不通,整理者注已言“有水、有中,与「有洪」结构相同。”那么作为名词的“有中”自然当是指尚未被洪水覆盖的中央高地,显然无从言及权宜变通,因此整理者引《战国策》训“权”为“变”当非是。笔者在《清华简十一《五纪》解析(之一)》中曾言:“'中’即中原,故'雚’当读为'灌’。”[2]因此清华简《参不韦》此处的“权”盖也当读为“灌”,指洪水泛溢,灌注中央。清华简此前各篇中,“中”、“仲”二字字形有着严格区别,“中”字皆有饰笔,“仲”则书作“中”形。但在清华简《参不韦》中,则存在三种情况,简03、简08、简24、简86的“中”字皆上端右侧有两横笔,简30、简48、简59、简61、简62、简63、简88则皆书作“中”形,简108、简111的“中”字则上端右侧有两横笔,下端右侧有一横笔,如果认为简86只是受之前的影响而写法偶然同于简30之前的各简,则清华简《参不韦》篇的“中”字写法分布可以划分为简30之前、简30至简88,简88之后三种写法,由此可将清华简《参不韦》划分为首、尾与中段三部分,且中段部分的书写者在用字方面更习惯用“仲”为“中”,这方面与清华简此前各篇截然不同。网友鱼在藻指出:“简111:漫泆,乃乱纪纲,莫[言千]德,整理者将其读为“申”,并引用《诗·假乐》'自天申之’毛传'申,重也’。实际上,此'重’作重复解。我们认为[言千]在此不用破读为'申’。'信德’,见于《越绝书》'故曰众者传目,多者信德’,《广雅·释诂一》'信,敬也’,信可训为敬信。如《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莫,代词。此处的'莫信德’指洪水漫溢,扰乱纲纪,没有谁敬信德。正可与简2—3'不虞唯信,以定帝之德’呼应。”[3]所说当是。
乃乍(作)悳(德)之五雚(權),【一一一】九雚(權)之參,以交天之不羊(祥)〔二〕。
整理者注〔二〕:“德,即前文之「五刑则」,简四有「五刑则唯天之明德」。雚,读为「权」。德之五权,权变天之五刑则,即简一至二之「不用五则,不行五行,不听五音,不章五色,〔不食五味」。九权之参,详见简一一六至一一九。”[4]权变本来就是临时性的,如果会固定为可以计数的类型,就不叫权变了,由下文的“九雚之参:淫、湎、康,则毁;掘谷、用土、大居,则丘;媱娥、无省、朋友,则内忧;迫、息、变,则乖;虐、不由、不刑,则灭光;寇盗、残贼、杀伐,则绝行;刚、虐、猛,则㯃;祖、考、柔,则惑;妖诵、迂言、妖雚,则乱。”也看不出任何权变内容,因此整理者读“雚”为“权”且训为权变,应该是不成立的。从“九雚之参”是九种现象来看,“雚”更适合读为“观”,“观”有占示非常之义,《吕氏春秋·博志》:“上二士者可谓能学矣,可谓无害之矣,此其所以观后世已。”高诱注:“观,示也。”《尔雅·释言》:“观,示也。”《淮南子·修务》:“筹策得失,以观祸福。”高诱注:“非常曰观。”《谷梁传·隐公五年》:“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传》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汉书·天文志》:“故德成衡,观成潢,伤成戊,祸成井,诛成质。”颜师古注引晋灼曰:“观,占也。”王念孙《读书杂志·逸周书·以其隐观其显》:“此本'作以其显观其隐’,人之声显而易见,其心气则隐而不可见,故曰'以其显观其隐’,即上文所云'听其声,处其气’也。今本'显’、'隐’二字互易,则义不可通。《大戴记》作'以其见占其隐’,'见’亦'显’也。”是《逸周书·官人》的“观”,《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作“占”。由此,“德之五观”可以理解为德行导致的五种非常现象,“九观之参”则是九大类每类共三种德行所导至的非常现象。“交”可读为“效”训为见,《淮南子·天文》:“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以五月下,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高诱注:“效,见也。”
參不韋曰:𢻻(啟),£監(濫)天𢝔(則)〔一〕,毋

(懈)弗敬,旾(春)

(秋)【一一二】𣅈(冬)

(夏)寒

(暑)不

(懈)。
整理者注〔一〕:“「监」前之字左从水,右部不清晰,疑似「眉」,读为「靡」,无。监,读为「滥」,僭乱。一说「湄」或为「演」字之讹,读为「寅」,敬。”[5]如按整理者读“□监天𢝔”为“靡滥天则”,则此句可对比于清华简十一《五纪》的“凡事群神,无滥有奠”。“毋懈不敬”也见于前文的“使万民毋懈弗敬”,虽然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不懈”、“无懈”习见,称“毋懈”则可对照于银雀山汉简《守令守法十三篇》之九“示民萌毋懈怠”,银雀山汉简有着明确的齐文化背景,因此清华简《参不韦》称“毋懈”当也是反映的齐文化影响,这整段文字则是针对前文的“乃自营自放,烝祀不章,乱天之纪纲,使春秋冬夏寒暑懈,不以其时行。”
𢻻(啟),不(丕)隹(唯)天之悳(德)。𢻻(啟),日月星㫳(辰)

(雷)霆、夭(妖)羊(祥)、風雨,不

(失)【一一三】亓(其)寺(時)。𢻻(啟),不(丕)隹(唯)天之

(表)〔二〕。
整理者注〔二〕:“戢,从爻声,读为「表」,表率。丕唯天之德、丕唯天之表,「丕唯」乃强调「天之德」、「天之表」。”[6]清华简《参不韦》全文皆并没有读“不”为“丕”的情况,此段中的“不”当也不是读为“丕”而仍当读为“不”,“隹”可以考虑读为“违”[7],或是读为“摧”[8],银雀山汉简《将失》:“十九曰军淮,众不能其将吏,可败也。”其中的“淮”与清华简《参不韦》此处的“隹”相类,盖也是读为“违”。《诗经·邶风·北门》:“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毛传:“摧,沮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摧折:上徂隈反,《考声》云:断也,损也,败也。”网友ee提出:“简114:'启,丕唯天之[爻戈]。’'[爻戈]’整理者释为'暴’读为'表’。按'[爻戈]’在楚简中不论是从对读还是押韵看,都与'卫’音相近,没有一例可以确定与'暴’有关者。上博四《昭王与龚之Snap1》简9 10:楚邦之良臣所[爻戈曰]【9】骨,陈剑先生释读'[爻戈曰]’为'曝’,与'[爻戈曰]’在楚简中基本与'卫’音有关显然不合,金俊秀先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疑难字研究》)把'[爻戈曰]’读为'熭’,'熭’与'曝’同义,且'熭’,邪纽月部,与'卫’古音极近。如银雀山汉简《六韬》简664:'日中必卫’,此即今本《六韬·守土》的'日中必彗’,《汉书·贾谊传》作'日中必熭’(参《楚文字两考》)。《三不韦》中的'[爻戈]’大概也可读为'卫’。”不过“天之卫”不知何意,由语境来看,“天之

”当与“天之则”、“天之德”义近,以月部字推测,则“天之

”或可读为“天之制”或“天之臬”,《鹖冠子·天则》:“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即“天之制”辞例。《小尔雅·广诂》:“臬,法也。”故若读为“天之臬”可理解为“天之法”。
啟,天則勿(物)各有尚(當),各有利〔三〕。

(剛)矛(柔)反易〔四〕,緩亟(急)異章,乍(作)𢘅(柔)【一一四】而利者(諸)

(剛),乍(作)

(剛)而利者(諸)𢘅(柔)。𢻻(啟),隹(唯)天之宜乃不雚(權)。𢻻(啟),亓(其)溢

(泆),乃雚(權)。【一一五】
整理者注〔三〕:“启,字从口,与本篇他处作「𢼄」写法不同。「天则」二字为后补。”[9]从口的“启”与不从口的“启”的差别,笔者《清华简参不韦解析(一)》[10]已言。“物各有当,各有利”可比较于《韩非子·观行》:“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可见此段内容成文时间盖与《韩非子》相近。
整理者注〔四〕:“易,更改、变易。”[11]“反易”于先秦文献见于《国语·晋语七》:“若欲暴虐以离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左传·哀公二年》:“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荀子·成相》:“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恶正直。”“异章”于先秦文献可见于《管子·地员》:“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杂英,各有异章。”刚、柔、缓、急并称于先秦文献可见于《韩非子·亡征》和《文子》的《上仁》、《微明》,综合这些词汇的使用情况来看,也可推测清华简《参不韦》此段内容盖成文于战国末期。读为“诸”的“者”字,写法接近于《陈纯釜》(《集成》10371),陈纯釜为齐国量器,非考古发掘出土,《集成》定为战国中期,这盖也反映出清华简《参不韦》此段接近战国中期而有着战国后期、末期齐文化特征。“雚”字相对于整理者所读的“权”更适合读为“观”,笔者前文解析内容已言。“天之宜”可比较于《鬼谷子·忤合》:“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此清华简《参不韦》此段内容的成文时间盖即在《鬼谷子》与《韩非子》之间。
參不韋曰:𢻻(啟),毋甬(用)夭(妖)雚(權),以自

(沮)悳(德)之五雚(權),百神弗亯(享)〔一〕。
整理者注〔一〕:“

,「樝」字异体,疑读为「沮」。《诗·小旻》「何日斯沮」,毛传:「沮,坏也。」《国语·晋语一》「众孰沮之」,韦注:「沮,败也。」百神弗享,《左传》僖公五年:「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12]“樝”又作“柤”,《尔雅·释木》:“樝梨曰钻之。”郭璞注:“樝似梨而酢涩,见《礼记》。”邢昺疏:“《内则》云:枣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胆之,柤梨曰钻之。”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六:“樝掣:古文作柤,同側加反。”而《说文·木部》:“柤,木闲。”徐锴《系传》:“柤之言阻也。”《广雅·释宫》:“柤,隁也。”王念孙《疏证》:“柤之言阻,遏也。”因此“自

”读为“自阻”要较整理者读为“自沮”更直接一些,《诗经·邶风·谷风》:“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毛传:“阻,难。”“五雚”读为“五观”,在先秦文献中有另一种“启”与“五观”的关系,《国语·楚语上》:“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又《韩非子·说疑》:“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韩非子》所称的《记》显然很可能就是《国语》,但在《国语》之前,则只称启之“五子”而不称“五观”,如《逸周书·尝麦》:“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至《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索隐》:“皇甫谧云号五观也。”这并不能解释“五子”何以又称“五观”。至后世,又以“五观”即“武观”,《墨子·非乐上》:“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孙怡让《间诂》:“《国语·楚语》云『启有五观。』韦注云『观,洛汭之地。』《水经·巨洋水》,郦注云『《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为观。』《左传》昭元年杜注云:『观国,今顿丘卫县。』毕云:『《汲郡古文》云「帝启十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注「武观,五观也。」《楚语》士娓曰:「夏有五观」。韦昭云:「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春秋传》曰:夏有观扈。』惠栋云:『此《逸书》,叙武观之事,即《书叙》之五子也。《周书·尝麦》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观也。彭寿者,彭伯也。《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遗文,《周书》载其逸事,与内外传所称无殊。且孔氏《逸书》本有是篇。汉儒习闻其事,故韦昭注《国语》,王符撰《潜夫论》,皆依以为说。』『启乃淫溢康乐』惠云:『「启乃」当作「启子」,溢与泆同。』江声说同。江又云:『启子,五观也。启是贤王,何至淫溢。据《楚语》士亹比五观于朱、均、管、蔡,则五观是淫乱之人,故知此文当为「启子」,「乃」字误也。』案:此即指启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误也。《竹书纪年》及《山海经》皆盛言启作乐,《楚辞·离骚》亦云「启《九辩》与《九歌》,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并古书言启淫溢康乐之事。淫溢康乐,即《离骚》所谓康娱自纵也。”武、五相通,清华简三《祝辞》书“武夷”为“五夷”可证,但“武观”若即“五观”复等同于“五子”,则其究竟为一人还是五人,从先秦文献中明显无从判断,若以《史记》所言为“昆弟五人”,则明显不会同封于观地,甚至由于《武观》篇已佚,《墨子》的引文内容根本不足以说明《武观》篇名就是对应于“五子”。实际上,由《墨子》所引的《武观》内容可以直接对应于“九观之参”的“淫、湎、康,则毁”很值得考虑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启有五观”是来源于被《墨子》称为《武观》的《五观》篇的一种误读,该篇很可能是与《墨子》所引《参不韦》和被整理者命名为《参不韦》的清华简此篇密切相关,其主要内容或即论述在清华简《参不韦》中所提到的“五观”并据以指责夏后启的“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且很可能与《墨子》所提到的《参不韦》篇并传,因此才皆被《墨子》引用,而由于传播过程中的讹误才衍生出《国语·楚语上》的“启有五观”,也即《墨子》所引的《武观》与《史记》提到的《五子之歌》应是各有传承的异说,并非同篇,内容上也非同指。“百神弗享”可比较于《孟子·万章上》:“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孟子为战国后期邹人,而《孟子》编成于战国末期,因此与“百神享之”相反的“百神弗享”句很可能反映的是战国后期、末期的齐鲁文化区特征。
九雚(權)之參,淫【一一六】緬(湎)康(荒)則毀,

(掘)浴(谷)甬(用)土大凥(居)則丘(咎)〔二〕,

(媱)嬟(娥)亡(無)眚(省)朋

(友)則內𢝊(憂)〔三〕,
整理者注〔二〕:“九权,指下文所列九种变乱常则的行为。

,见于清华简《子仪》简一一,以「叕」为基本声符,读为「掘」。《易·系
辞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马王堆帛书本「掘」作「掇」。《诗·驺虞》「彼茁者葭」、「彼茁者蓬」之「茁」字,安大简《诗经》作「盖」。掘,穿也。丘,读为「咎」,凶咎。”[13]被整理者读为“咎”训为凶咎的“丘”如何能是一种“行为”,很难让人理解,“内忧”、“灭光”同样无从让人理解何以会是“行为”,因此整理者注所言“九权,指下文所列九种变乱常则的行为”当不确,“九观之参”当即分别每三种不当德行导致同一类现象结果,共九类现象,导致这九类现象的内容多与前文“建后总五刑则”以下各职司内容存在对应关系。网友质量复位指出:“简116-117'淫湎康(荒)则毁’。按,'康’如字读即可。'康’有逸乐、淫乐的意思。《淮南子·泰族》:'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顾政治,至于灭亡。’二者可以合观。”[14]所说是。淫即淫佚,湎即流湎,康即逸乐,“淫、湎、康,則毀”与《左传·成公二年》的“淫湎毀常”明显直接相关,且对应于清华简《参不韦》前文的“师申则定后之德,典常音故律毋淫”。整理者读“甬”为“用”,然而“用土”当是习见的行为,很难认为有什么不当,故“甬”盖当读为“壅”,“壅土”可见于《文选·张华情诗二首》:“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李善注:“韩诗曰:'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薛君曰:'鹳,水鸟。巢处知风,穴处知雨。天将雨而蚁出壅土,鹳鸟见之,长鸣而喜。’”《观象玩占》卷四十九“土石井邑冢墓杂占”:“邑无故壅土如山,是阳反阴,人君好滛,为女子所谋,不出一年有易君。”“大居”可对应于《晏子春秋集释·内篇杂下·景公毁晏子邻以益其宅晏子因陈桓子以辞第二十二》引孙星衍云:“沈启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晏子使鲁,比其反,景公为毁其邻以益其宅。晏子反,闻之,待于郊,使人复于公曰:『臣之贫顽而好大室也,乃通于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乡恶而居小,故为夫子为之,欲夫子居之以慊寡人也。』晏子对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邻舍。」今得意于君者慊其居,则毋卜已,没氏之先人卜与臣邻、吉。臣可以废没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邻归之心,臣不愿也。请辞。』」』案:今本皆与《左传》文同,删去此文,疑后人妄以《左传》改此书也。”《晏子春秋》是标准的齐地文献,故“大居”之说当也是出自齐文化的影响。“丘”当指成为废墟,《楚辞·九章·哀郢》:“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王逸注:“丘,墟也。”马王堆帛书《十六经·三禁》:“人道刚柔,刚不足以,柔不足恃。刚强而虎质者丘,康沉而流湎者亡,宪古章物不实者死,专利及削谷以大居者虚。”“丘”与“亡”、“死”、“虚”并举,显然就是废为丘墟义,“专利及削谷以大居者虚”句也颇类似于“掘谷、壅土、大居,则丘”,马王堆帛书《十六经》出自齐人之手,与出自秦人之手的《经法》等篇区别明显,故这也可以反映出此段清华简《参不韦》有着齐文化背景。“掘谷、壅土、大居,则丘”对应于前文“司空正万民,乃修邦内之经纬城郭,浚洿行水,及四郊之赴稼事。……工比五色以为文,安宅及戎事。”中的“经纬城郭,浚洿行水”和“安宅”。
整理者注〔三〕:“

,「媱」字异体。嬟,「娥」字异体,其形稍讹;一说释为「媄」。媱娥无省朋友则内忧,意谓沉溺美色、忽视朋友则有内忧。”[15]媱、娥皆为美貌义,“媱娥”指为君者自己也是没什么意外的,如《荀子·非相》:“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然而中君羞以为臣,中父羞以为子,中兄羞以为弟,中人羞以为友。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伤其今,而后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议论之卑尔。”整理者读“朋

”为“朋友”,但先秦文献中“朋党”可以说有贬义,“朋友”则并无贬义用法,因此“

”当读为“尤”训为责怪,《左传·襄公十五年》:“春,宋向戍来聘,且寻盟。见孟献子,尤其室。”杜预注:“尤,责过也。”《淮南子·齐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索隐》:“尤谓怨咎也。”“无省”即不反省自己,“朋尤”即怨责朋友,故二者并举。“媱娥、无省、朋尤,则内忧”对应前文“宰典后之家配”。
敀(迫)息(疾)辡(變)【一一七】則乖,

(虐)不由不刑則烕(滅)光〔四〕,
整理者注〔四〕:“灭光,灭减光宠。”[16]网友tuonan提出:“《参不韦》简117'敀(迫)息(疾)辡’的'辡’,以及《语丛二》简19'急生于欲,[亻 辡]生于急’的'[亻 辡]’,更可能读为'㦚’、'弁’、'卞’等,是躁急的意思。《礼记·玉藻》'弁行’,《释文》:'弁,急也。’《说文》心部:'㦚,忧也。从心、辡声。一曰急也。’《左传》定公三年'庄公卞急而好洁’,杜预注:'卞,躁急也。’”[17]所说是,不过整理者括读为“变”也并无不可,《韩非子·亡征》:“变褊而心急,轻疾而易动发,心悁忿而不訾前后者,可亡也。”俞樾《诸子平议》卷二十一:“'变’当读为'㦚’。《说文·心部》:'㦚,一曰急也’,是与'褊’同义。作'变’者,声近假借也。《易·文言传》:'由辩之不早辩也’,《释文》:'辩,荀作变’。《孟子·告子篇》:'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音义》引丁音云:'辨,本作变。’皆其例矣。”可见括读为“变”与括读为“弁”、“卞”并无差别,皆是“㦚”的通假。《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暴,顾我则笑。”毛传:“暴,疾也。”《韩非子·八说》:“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又“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人主轻下曰暴。”《说文·夲部》:“曓,疾有所趣也。”段注:“趣当作趋,引申为凡疾之偁。”故有“迫、疾、㦚,则乖”。“乖”是指的臣民,因此“迫、疾、㦚,则乖”可对应于前文的“征徒正四郊之闭及徒戎。”“虐、不由、不刑”的前提条件是身为君主,因此可对应于前文的“建后总五刑则,秉中不荧,唯固不迟。”

(寇)佻(盜)俴(殘)賊殺伐則㡭(絕)行,

(剛)虎

(虐)

(猛)【一一八】則㯃(恣)〔五〕,
整理者注〔五〕:“

,疑「虐」字之省讹,同「虐」。

,读为「猛」。㯃,所从「桼」旁与本篇「桼」字略有差异,读为「恣」。《说文》:「恣,纵也。」”[18]“寇盗”见前文士之所司,“残贼、杀伐”见前文司寇所司,因此“寇盗、残贼、杀伐,则绝行”可对应于前文的“士修邦之寇盗……司寇修残贼杀伐”。“绝行”于先秦传世文献可见于《尉缭子·兵教上》:“前军绝行乱陈,破坚如溃者,有以也。”因此可推知清华简《参不韦》此段“九观之参”的具体内容很可能成文于战国末期。网友无痕指出:“简118'{丙丙口攴}’原读'猛’,实应释'更’,读'梗’训猛。'{弓口二}虎{丙丙口攴}’可读'强虐梗’。《迺命二》简10-11'{弓口二}{木丙口}’之'{木丙口}’也是'丙丙’省声,与上博简《三德》'{木丙丙口}(更)旦’(程少轩先生释)之'{木丙丙}’是一字,应释'梗’,原读'刚猛’,今改读为'强梗’。该字与可读为'猛’的'{丙口犬}’(郭店《老甲》33)、'{丙口心}’(上博《从政》8)、'{丙口皿}’(清华《治邦之道》1)等非省声字不同。”[19]所说“

”读“梗”训猛当是,“刚”即前引马王堆《十六经·三禁》的“刚强”,“虎”即前引马王堆《十六经·三禁》的“虎质”,“虎质”也是指的猛,《逸周书·周祝》:“故虎之猛也而陷于攫,人之智也而陷于诈。”《管子·形势解》:“虎豹,兽之猛者也。”《方言》卷二:“撊、梗、爽,猛也。晋魏之间曰撊,韩赵之间曰梗,齐晋曰爽。”钱绎《笺疏》:“梗之言刚也。”漆树之漆古文只作“桼”,因此“㯃”盖是“栉”字异体,《管子·弟子职》:“栉之远近,乃承厥火。”《集校》引王筠曰:“栉,烬也。”“栉”作余烬义时字又作“㸅”,《集韵·屑韵》:“㸅,烬谓之㸅。”先秦有以火势之烈比喻为政之猛的情况,如《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可见为政若猛则难免民残如烬,《诗经·大雅·桑柔》:“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因此清华简《参不韦》此处言“刚、虎、猛,则栉”。“刚、虎、猛”皆为武德,《逸周书·谥法》:“刚强理直曰武,威强叡德曰武。”《吕氏春秋·季秋纪》:“天子乃厉服厉饬,执弓操矢以射。”高诱注:“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厉其所佩之饬以射禽也。”《吕氏春秋·顺民》:“越,猛虎也。”高诱注:“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故“刚、虎、猛,则栉”对应前文“司马展甲兵戎事”。
組(詐)考(巧)柔則惑,夭(妖)甬(用)

(誣)言夭(妖)雚(權)則𡄹(亂)〔六〕。
整理者注〔六〕:“组,读为「诈」。考,读为「巧」。诈巧,欺诈虚伪。《庄子·盗跖》:「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柔,面色和柔奉承。《论语·季氏》:「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邢疏:「善柔,谓面柔,和颜悦色以诱人者也。」”[20]“诈”往往被视为是与商贾相关的属性,如《周礼·地官·司市》:“以贾民禁伪而除诈。”郑玄注:“贾民,胥师、贾师之属。必以贾民为之者,
知物之情伪与实诈。”《荀子·王霸》:“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贾人以诈取人,亦阴也。”“巧”则有巧于言辞、巧于制作、巧于谋思等区别,巧于言辞可对应“祝”、“史”,巧于制作可对应于“工”,如《管子·五辅》:“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管子·七主七臣》:“主好宫室,则工匠巧。”《庄子·渔父》:“国家昏乱,工技不巧,贡职不美,春秋后伦,不顺天子,诸侯之忧也。”《吕氏春秋·季春纪》:“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左传·桓公六年》:“祝史正辞,信也。”《论语·雍也》:“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说文·女部》:“佞,巧讇高材也。”故“诈、巧、柔,则惑”可对应于前文工、贾所司。“妖诵、迂言、妖讙,则乱。”则显然即对应于前文的“士……妖诵迂言,妖乱之禁。”
參不韋曰:𢻻(啟),【一一九】毋不𠄨(極)天之命,以從乃悳(德),隹(唯)天之不羊(祥)。𢻻(啟),乃自則【一二〇】乃身,弗可

(愎)庚(荒)〔一〕。帝之命逆韋(違)〔二〕,命用不長。百神之兇

(顯),𨒥(後)

(嗣)之【一二一】央(殃)〔三〕。
整理者注〔一〕:“𠄨,「𠄨」之讹形。《广雅·释诂上》:「亟,敬也。」

庚,读「愎荒」,刚愎荒怠。”[21]“毋不”为双重否定,表强化肯定义,此句所言“毋不”内容,就是指后面的“极天之命以从德”。“从德”辞例,可见于《国语·晋语四》:“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如果不“极天之命以从德”,天帝就会降以妖祥,故言“唯天之不祥”。“

庚”犹言“复更”,《广雅·释诂三》:“庚,更也。”王念孙《疏证》:“庚者,《汉书·律历志》云:'敛更于庚。’《白虎通义》云:'庚者,物更也。’郑注《月令》云:'庚之言更也,秋时万物皆肃然改更。’”《论衡·无形》:“形已成定,何可复更也?”
整理者注〔二〕:“逆违,即「违逆」,不遵从。帝之命逆违,即「逆违帝之命」之倒装。”[22]夏后启如果以后的身份违背天帝之命,可以类比于《国语·鲁语上》:“臣违君命者,亦不可不杀也。”因此言“命用不长”,前文“而不闻而先祖伯鲧不待帝命而不葬”与《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所言即违逆帝命的情况。
整理者注〔三〕:“此节羊(祥)、庚(荒)、长、央(殃)为韵,阳部。”[23]这段内容的用韵,很可能是上接“乃乱纪纲”、“以效天之不祥”、“百神弗享”,且延续至下文的“殃”、“祥”。现在的隔绝情况,值得考虑是因战国末期的改写者插入自己补入的内容所导致的。
參不韋曰:𢻻(啟),乃毋既□□緬(湎),雚(權)有

(懈)悳(德),乃曰弗可

(渝)

(悔),以【一二二】須天之央(殃)〔四〕。天之

(明)悳(德),隹(唯)

(造)天之命,

(渝)

(悔)前化(過),三气受天央(殃)〔五〕。

(𣎆)

(明)不【一二三】

(懈),天弗乍(作)恙(祥)〔六〕。【一二四】
整理者注〔四〕:“「既」字后残二字。


,简一二三作「

𠰔」,读为「渝悔」,变改反悔。须,待。”[24]前文已见淫湎并言,先秦传世文献也习见淫湎并称,如《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饮酒不恤天灾》:“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吕氏春秋·当务》:“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及前引《左传·成公二年》:“不式王命,淫湎毁常。”因此“湎”字前可以考虑补“淫”字,更据前文内容,“淫”字前也可以考虑补“康”字,由此全句可以为“乃毋既康淫湎,观有懈德,乃曰无可渝悔,以须天之殃。”
整理者注〔五〕:“

,读为「造」,就。三,疑当释「气」,本篇「叁」皆从晶、从三。气,甲骨文、西周金文字形与「三」相近,东周后才逐步加大区分。简文「气」讹与「三」同,当为字形存古所致。简文「气受天殃」之「气」,读为「讫」,终止。此句意谓终止受天之殃,与上句「以须天之殃」相对(参看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二〇〇九年,第一〇一至一〇五页)。𣎆明不懈,谓敬慎黾勉而不懈怠。”[25]“

”盖即“悎”字异体,“悎”有惊惧义,《集韵·皓韵》:“悎,惧也。”《集韵·效韵》:“悎,惊也。”因此“

天之命”可以理解为畏惧于天命,所以有下文的“三受天殃”。清华简九《成人》中有“疋”读为“三”的通假例,故清华简《参不韦》此处的“三”可以考虑读为“胥”,《庄子·山木》:“虽飢渴隐约,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释文》引司马云:“胥,须也。”因此“胥受天殃”即对应于前文的“须天之殃”。
整理者注〔六〕:“此节央(殃)、央(殃)、恙(祥)为韵,阳部。”[26]前文已列举清华简《参不韦》篇中有若干字形早于目前可见的战国文字,这是字形方面的证据;其对五则、五行、五音、五味、五色的列举与《洪范》相似,而《洪范》约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这思想观念方面的证据;清华简《参不韦》中“士”是仅次于“后”的要职,这种情况最早可追溯到清华简八《摄命》的“士疌右伯摄”,“伯摄”是周王之子,能够为伯摄右者的“士疌”其身份之高可想而知,笔者在《清华简八摄命末简解析》中已指出:“《摄命》篇笔者认为很可能是成文于周平王即位之年,属春秋初期初段……《摄命》此处的'士’当即是'大士’”,因此“士”作为能够做周王之子的右者这样的要职,目前可知最早可追溯至春秋初期,由此自然可知清华简《参不韦》中的职官系统盖去春秋初期不远,这是官制方面的证据。三方面的情况都说明,清华简《参不韦》篇的主体盖是成文于春秋时期。前文解析内容也已言,清华简《参不韦》篇中对各官职所司的介绍内容盖是后人补入,祭告文辞部分盖也是后人补入。为了衔接自然,这些补入完全可能对之前、之后的文字做一些修改润色,以保证文风相近,过渡顺畅。而这种修改补充,最晚则很可能会晚到战国末期。例如,“于”和“於”在先秦时期存在着明确的此消彼长关系,何乐士先生在《论左传前八公与后四公的语法差异》文中曾统计部分先秦古籍的“于”、“於”百分比[27],由其统计结果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於”的占比达到和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只有《庄子》、《韩非子》、《战国策》三书,由此不难判断,“於”的占比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的时段当是最可能在战国末期。笔者在《清华简十二参不韦解析(一)》中亦已提到:“由篇中只出现了'於’而未出现'于’则可以判断,此篇在传抄过程中'于’字已全部被改写为'於’,因此这个只出现'於’未出现'于’的版本盖是抄于战国末期。”推而广之,可将目前已见的清华简各篇中虚词“于”、“於”使用情况进行列表分析,首先列出清华简二《系年》的虚词“于”、“於”使用情况表:
系年
于
於
于/於
第01章
6
0
—
第02章
12
0
—
第03章
4
0
—
第04章
6
1
6
第05章
3
8
0.375
第06章
6
1
6
第07章
1
2
0.5
第08章
1
2
0.5
第09章
3
0
—
第10章
2
0
—
第11章
2
1
2
第12章
2
0
—
第13章
2
0
—
第14章
7
2
3.5
第16章
1
5
0.2
第15章
4
4
1
第17章
2
5
0.4
第18章
5
2
2.5
第19章
1
1
1
第20章
4
1
4
第21章
1
2
0.5
第22章
3
5
0.6
第23章
1
12
0.083
如果以清华简《系年》内容来观察,则虚词“於”出现于《系年》第四章“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峁虎起师伐卫,大败卫师於睘”句,因此可推测虚词“於”盖即出现于春秋前期后段,这也就对应了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28]中所推测的虚词“於”出现于春秋前期。
再看清华简七《越公其事》中的虚词“于”、“於”使用情况表:
越公其事
于
於
于於比
第01章
6
5
1.2
第02章
3
3
1
第03章
1
9
0.111
第04章
2
0
—
第05章
2
0
—
第06章
3
1
3
第07章
4
0
—
第08章
2
0
—
第09章
7
0
—
第10章
0
5
—
第11章
4
4
1
在《越公其事》第04章中引出五政内容,从第05章至第09章是五政农、商、人、兵、刑的分述,这在虚词“于”、“於”使用比上反映为这六章中虚词“于”的使用量皆高于“於”,而由此可推知,至战国前期总体上虚词“于”的使用量仍是高于“於”的。
在清华简中,只出现虚词“於”而未出现“于”的篇章还有清华简四《筮法》、清华简五《汤处于汤丘》、清华简五《汤在啻门》、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清华简六《管仲》、清华简七《赵简子》、清华简八《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清华简八《心是谓中》、清华简八《邦家之政》、清华简八《邦家处位》、清华简十《行称》、清华简十一《五纪》等篇。很明显,若认为这十几篇都是早于战国末期的,这个可能性无疑是很小的。反之,对应于何乐士先生的研究,更适合判断这些篇章多是在战国末期成文的可能性非常大。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
虚词篇(补一)“乎”》[29]曾论及,不与“於”结合为语气词“於乎”的虚词“乎”出现时间盖就在战国后期前段至战国后期后段之间,清华简中出现这样的虚词“乎”的篇章有《命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管仲》、《子犯子余》、《赵简子》、《心是谓中》、《邦家之政》、《治政之道》,对比前文只出现虚词“於”而未出现“于”的篇章,很明显重合度相当高,因此足以判断重合的篇章很可能不仅不早于战国后期,且相当可能成文于战国末期。笔者在《清华简七赵简子解析》[30]已言:“包括《赵简子》篇在内的清华简中不少篇章成文时间都很可能要晚到战国末期,对无字残篇所做的碳十四测定,并不足以确定全部清华简材质的形成时间。”[31]以对无字残简进行的碳十四测定结果来推测全部清华简各篇的竹简所属时段,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式的逻辑谬误,因此笔者在《清华简七子犯子余韵读》[32]言:“由于清华简中已有多篇内容笔者根据篇中所用词汇推测属于战国末期成文,因此清华简测年所存在的局限值得重新考量。笔者认为,对于出土简帛所进行的技术测年,即便不能精确到各支简或各片帛,至少也应精确到各个篇章。”另外,清华简《命训》篇八之前皆是用“于”,简八起皆是用“於”,此种差别在今《逸周书·命训》篇中情况相同,因此很可能说明《命训》篇盖原是由“天生民而成大命……则度至于极”和“夫天道三……始以知终”两部分拼合而成的。
推而广之,以虚词“于”、“於”的使用情况分析郭店简和上博简的话,郭店简仅《五行》和《性自命出》两篇各有一个虚词“于”的用例,郭店简《缁衣》中虚词“于”用例皆为引用《诗》《书》,其它部分和郭店简其它各篇也皆只使用虚词“於”,由此可见郭店简绝没有学界流行说法所称的战国前期或中期那么早,而更可能多数为战国后期、战国末期文献。上博简中也是多数篇章只使用虚词“於”,用到虚词“于”的篇章仅十余篇,由此可见上博简整体上盖只是略早于郭店简,绝大多数篇章仍然不会出于战国后期、末期的时间范围。
[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4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2] 中国先秦史网站:,2022年1月9日。
[3] 简帛论坛:/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766&pid=30538,2022年12月1日。
[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7]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497页“帷与帏”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8]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492页“隹与崔”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9]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0] 中国先秦史网站:,2022年12月18日。
[1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5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4] 简帛论坛:/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766&pid=30540,2022年12月2日。
[1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7] 简帛论坛:/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766&pid=30633,2022年12月6日。
[1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19] 简帛论坛:/foru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766&pid=30607,2022年12月6日。
[20]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6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2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2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2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2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25]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26]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第137页,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10月。
[27] 《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第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
[28] 中国先秦史网站:,2011年1月1日。
[29] 中国先秦史网站:,2020年10月13日。
[30] 中国先秦史网站:,2017年5月29日。
[31]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s://,2017年5月29日。
[32] 中国先秦史网站:,2017年10月28日。
《尧曰篇》20.3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20.3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注释】▲不知命:命是命运,天命。“命”可以理解为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不可控的外在力量。也可理解为时代的变化,社会的现状,国情。▲不知礼:“礼”是国家法度,社会秩序。▲不知言:不能明辨是非,分析善恶。【译文】紫网2023-10-14 12:03:140000轻轻松松读《老子》(77)
《老子》第77章天道与人道原文: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xiàn)贤。译文: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是不是很像拉弓射箭呢?举得高了,就压低一点,压得低了,就抬高一些;弦拉得过紧了就放松一些,用力不足了就加点力气。 秋雨堂2023-07-30 12:42:260000
秋雨堂2023-07-30 12:42:260000《道德经今析》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者,知者,明也。美,妙也,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世人皆以目所见色之美,耳所听声之美,口尝味之美,鼻所闻香之美,身所触感之美,法(意)所受境之美。故天下人皆知之美为外之美,圣人不知其美为美为真美。斯恶已,六识转为六贼,即六欲也。六识者眼耳鼻舌身意也。因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而生喜怒爱思欲忧六欲。故六欲,皆从人心而出。 管中和2024-02-04 09:06:130000
管中和2024-02-04 09:06:130000与庄共舞——大大小小贵在道【《逍遥游》4】
让自己舒服的,便是人间最好之道。【原文】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紫网2023-10-14 13:31:2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