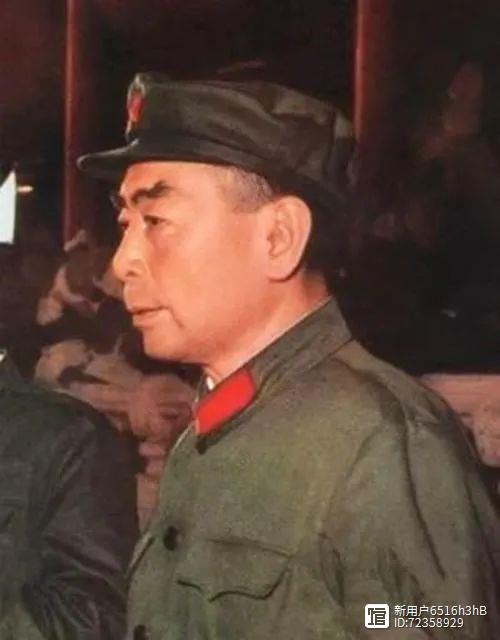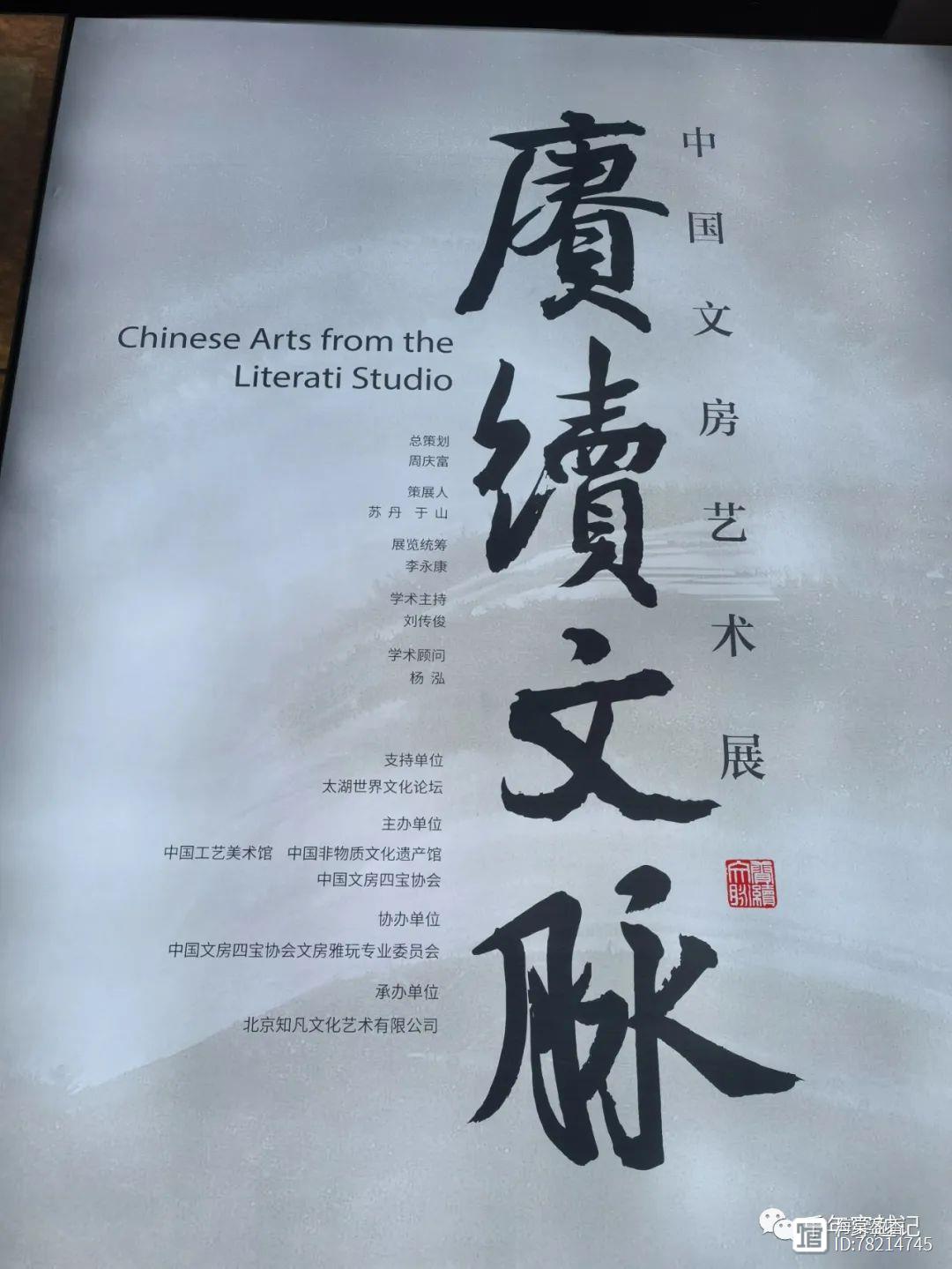“山东兄弟”,是王维这一生情感上最大的牵绊
唐朝诗人王维,一生寄情山水,参禅信道,诗风处处见禅机,人称“诗佛”。
王维少年得志,21岁及第,顺利进入官场。其后数年宦海,从善如流,并没有像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那么强烈的政治抱负。
感情生活上,王维虽有过一个妻子,可不论是她生前还是身后,他都不着一字,连那个时代文人圈流行的“悼亡诗”也不曾写给妻子。而且,妻子去世时他不过30岁,膝下无子,却无意续弦、传宗接代……
综观王维一生,性情冲淡平和,境遇随遇而安,还真有些佛系。
与李白至死不渝的天真狂浪,与杜甫那种对人间世掏心掏肺、呕心沥血的热爱,形成鲜明对比。他似乎过滤掉了某种激烈的情绪,不论写诗绘画,还是人情世故,都只剩下清丽悠远,宁静自持。
但,也有例外。
王维为数不多的亲情诗显示,他的“山东兄弟”是他这一生情感上最大的牵绊。与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机不同,他在亲情诗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兄长,有血有肉的兄长。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便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这一首几乎每个小学生都会背的诗,写于王维17岁时。“山东”指华山以东,那是王维的故乡蒲州。王维是家中长子,底下还有四弟一妹。9岁时,父亲去世,年幼的王维协助母亲打理家业,照顾弟妹。15岁,王维拜别亲人,远游长安,博取功名。17岁那年,孤身旅京的少年,在重阳节这天登高望远,思念远在家乡的弟弟妹妹。此诗中,颔联“遥知”有视角上的转换,少年想象弟妹们登高采茱萸因为哥哥不在而黯然神伤,而他们的伤心又让远在京都的哥哥更为思乡,《岘斋说诗》形容这种写法“不说我想他,却说他想我,加一倍的凄凉”。
父亲早逝,王维与弟弟妹妹间这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成了他恬淡性情中少有的热切,也是他一生的牵挂。
王维21岁及第,被任命为太乐丞,其后几年,宦海沉浮,官职变迁,在排挤和冷遇中艰难求生,他渐生对官场的厌倦,时有归隐的想法。
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孙登长啸台,松竹有遗处。相去讵几许,故人在中路。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忽夫吾将行,宁俟岁云暮。——王维《偶然作》之三
开元十五年,二十七岁的王维官居淇水之滨,被太行山的风景所吸引,归隐之念再现,可这个想法旋即就被现实击碎。小妹未嫁,兄弟未娶,家中经济捉襟见肘,全靠他支撑,他若真归隐了,一家子该怎么办?这首诗言语简约,明白易懂,所呈现的又岂止是王维的困境?再往前,陶渊明曾为此烦恼过,往后,许多21世纪的现代人每天也再做类似的挣扎。一边向往自由,一边为家庭责任所牵绊。
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王维《山中寄诸弟妹》
这是王维小隐嵩山时写的一首五言。
颔联的“遥相望”与《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遥知”异曲同工,明明自己很思念家人,却通过家人想念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或者说一想到弟弟妹妹想念自己、需要自己,他的思念就更为热切而且忧伤了。
对尘世这么大的眷念,还怎么隐得下去,这一次,王维在嵩山静修半年便下山了。
往后十余年,王维生活的主线依旧在官场,十分厌倦了就找个清净地住几天、回回血,这个模式一直持续到开元二十九年。这个时候,王维大弟王缙早已进入官场,其他几个弟妹均成家自立。年过四旬的王维辞去官职,隐居终南,过足了一把隐士的瘾。其后数年,王维一直都在这种半仕半隐的状态,寄情山水,热衷佛道,卸下家庭责任的担子,他这个长兄终于能喘口气了。
755年岁末,安史之乱爆发,官场上一向低调谨慎的王维遇到了人生第一个真正的劫。叛乱刚起,唐玄宗便携贵妃、部分宗室、随从逃离长安,王维不及脱身,为安禄山所擒。安禄山久仰王维大名,将其押解洛阳,软禁菩提寺。就这样,王维被迫做了“贰臣”。
待唐军收复两京,回到长安,唐肃宗磨刀霍霍,针对“附逆者”秋后算账,王维也在被罚之列。此时大弟王缙因辅佐将领李光弼镇守太原有功,升为刑部侍郎。闻兄之难,他跪求皇帝“削己官位以赎兄罪”,愿意用自己的前程换取兄长的平安。当时又有大臣针对唐肃宗对“附逆者”的惩罚提出异议,言“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第一个出逃的是皇帝自己,他抛弃了长安、抛弃了百姓,首先违背君臣契约的他,现在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罚“附逆者”,难服众人心。
唐肃宗权衡再三,最终宽大处理,只将王维官降一级,做了太子中允,后来又任王维做了尚书右丞,这是王维宦海生涯的巅峰了。但此劫之后,“贰臣”耻辱成为王维余生的隐痛,他越发遁世,隐居辋川,与山水草木为伍,用佛经禅理抚平内心痛苦。但他仍做不到远遁尘世,因为尘世中还有他的骨肉兄弟。
758年秋,王缙出任蜀州刺史,王维登高目送:
陌上新离别,苍茫四郊晦。登高不见君,故山复云外。远树蔽行人,长天隐秋塞。心悲宦游子,何处飞征盖。——王维《别弟缙后登青龙寺望蓝田山》
此时王维快60岁了,孑然一身,残躯一副,老病相煎,与弟这一别,今生都不知能否再有相见的机会。立于山岗,茫然四顾,兄弟俩带着对彼此的牵挂消失在树涛山海之间。天地无情,所以能千年万载的生生不息,人之有情,每每苦于生离死别,困于自伤。但世间万情,总有些东西是佛经禅理不能抵达的。
761年春,王维预料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上书皇帝《责躬荐弟表》:
……顾臣谬官华省,而弟远守方州,外愧妨贤,内惭比义,痛心疾首,以日为年。臣又逼近悬车,朝暮入地,阒然孤独,迥无子孙。弟之与臣,更相为命,两人又俱白首,一别恐隔黄泉。傥得同居,相视而没,泯灭之际,魂魄有依。伏乞尽削臣官,放归田里,赐弟散职,令在朝廷。
王维说自己年迈孤独,又无子孙,与弟缙相依为命。如今缙远在蜀州,两人俱是白首,遥隔两地,惟恐不能见最后一面,黄泉永隔。几年前,王维遇劫,王缙愿舍前程保兄长平安,此时王维也做了同样的事。他恳请皇帝削去自己官职,换王缙回朝,兄弟俩朝夕晤对,这样即使哪一日大限将至,也能“魂魄有依”,了无遗憾。
不久,皇帝准了王维的奏请,在《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中,王维再次写道:
臣之兄弟,皆迫桑榆,每至一别,恐难再见,匪躬之节,诚不顾家,临老之年,实悲远道……
这些奏疏中,王维不是后世人印象中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的样子,只是一个牵挂自己兄弟的还有些絮叨的兄长。这里没有诗佛,只有兄弟间的依依深情。
761年夏,王缙获准回长安。但王维依旧没能等到与弟弟的最后一面,王缙行至凤翔时,噩耗传来,长兄与世长辞。
时光倒流,多年前那个带着全家的希望闯荡长安的17岁少年,在重阳节这天忍不住对家人的思念,写下了传世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凝聚了人心底最纯粹最痛切的感情,穿越历史烟尘,叩在每一个游子的心头。
数载过去,对王维而言,这份亲人间的牵挂依旧沉甸甸的,鲜活纯粹,只是这一次他终不能如愿,不能“魂魄有依”,他带着那份牵挂,走了。
作者:寇研
本文为菊斋原创首发。公号转载请联系我们开白授权。
中元节将至,牢记“做3事、忌3事”,压住“霉运”,为家人祈福
中元节,又称“鬼节”、“七月半”,是一个融合了多种信仰和传统文化的传统节日。它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古代农耕社会,最初是对祖先的崇拜和缅怀,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节日。紫网2023-10-15 08:39:530000周总理在军中地位有多高,能被授予元帅吗?看他的军职就知道了
艺述史官方原创元帅中的元帅1955年,57岁的周总理亲自主持了军队大授衔仪式,自己却果断拒绝了元帅题名,把这份殊荣让了出去。这项仪式不仅在新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所有军人更是一项最高殊荣。1授衔仪式结束后,周总理向几位元帅道贺,他们连忙起身对周总理说:“您也是元帅!”紫网2023-10-14 12:24:500000小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人生就像一场雪,聚散终有时
 脑洞趣味历史2024-02-19 16:05:580000
脑洞趣味历史2024-02-19 16:05:580000山东方言里的“蹀躞”,咋读又是啥意思?可别嫌俺土气了!
艺述史官方原创万里蹀躞,以此为归北方尤其是山东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方言叫做“diexie”,说一个人不高兴,垮着脸,就叫“diexie个脸”,在有些地方这两个字还表示瞎积极,穷显摆,不稳重。这俩字怎么写,您知道吗?1其实啊,别看方言说起来土里土气,这两个字写起来可是相当文雅,摆在许多山东人面前,我们都不一定认识:蹀躞,你认得吗?紫网2023-10-16 17:07:040001我离喜欢建盏,只差一个它!
上周六,8月26日我去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看展“赓续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这个展以文房为题展品来自全国收藏界藏品和当代文房企业产品及大师作品共600多件/套文玩到了清尤其是清中后期就几乎成了附庸风雅的代名词用料讲究、穷工极巧、精雕细琢但文的作用越来越少,主打就是个玩儿什么葫芦、核桃、手串儿……充满了糜烂的八旗子弟瞎讲究之风现在,还能赓续什么呢?还有多少人用文房四宝?平常用笔的机会都极少极少紫网2023-10-15 13:32:130000